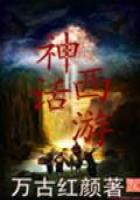《古诗十九首》是飘零他乡、悒郁不得志的汉末下层文士的真诚的人生感怀,充满浓郁的生命悲情格调。以《古诗十九首》作为山水诗前史的起点,是基于以下认识:其一,中国美学史视野中的山水诗前史,就是体现强烈个体意识的《古诗十九首》以来的个人诗歌创作及其审美意识的变迁史。其二,《古诗十九首》为了表达人生如寄的漂泊感,将季候变化与旅途物象写进诗中,这是五言诗的最早时空印象和审美经验。其三,由秦入汉,《诗》奉为经,《骚》变为赋,诗骚艺术抒展个人情性的传统转变为政治教化道统,东汉末《古诗十九首》的出现透露出某种诗性气质与审美精神回归的积极信息,故以此作为我们考察山水诗诞生的前导。在诗歌与艺术文类(genre)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作为文本的《古诗十九首》不仅承担了早期文人个性化创作五言诗的历史使命,而且构成三国两晋行旅诗的近源。《古诗十九首》的基本主题是游子之思和思妇之怨。正如马茂元先生所指出的,这其实就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二者只是作为代言人的抒情主体形象的文化身份的砝码表象有所差别,从不同维度表达主体的羁怀愁思和漂泊情怀而已。尽管这样,对本论题具有理论阐发意义的部分仅限于前者即游子之思,因为它与后起的行旅诗前后承续共同构成一组较明晰的发展脉络。而随着天下三分、诸侯割据局面的形成,汉末政治军事利益集团认识到拥有文人谋士的重要性,纷纷蓄士自重,文人地位得到根本的、体制性的改善。于是,文士们心怀济国安邦之志奔走各方。行旅诗大体就是魏晋文士这种人生历练的写照。
在《古诗十九首》中,以羁旅客外的游子之思为基本抒情主题的作品大体有《青青陵上柏》、《涉江采芙蓉》、《明月皎夜光》、《回车驾言迈》、《东城高且长》、《驱车上东门》、《去者日以疏》和《凛凛岁云暮》等八首。这些诗作共同抒写的是一种人在旅途的孤寂、落魄与无所皈依的悲愁,我们称之为羁旅诗。用谶纬神学武装起来的大一统的两汉政权,军事上历经东汉末黄巾大起义和随之而来的豪强割据的一再打击;统治阶级内部则连续爆发了牵连甚广的“党锢之祸”;意识形态上,不断遭到进步思想家王充、桓谭、扬雄等人的质疑、挑战与解构,已经显示出它荒谬而岌岌可危的颓势。加上汉末社会陷入空前的由人祸和天灾所导致的战乱与动荡之中,人民迁徙流离,维系精神的价值体系濒于崩溃。动荡不安的现实极大地破坏了社会的良性运行机制,作为知识拥有者的文人的晋升之阶不可避免地被阻断了,大量士人被无情地抛人社会的下降性流动通道。但是这些体力劳作能力退化的文人并不甘心屈居陋室里巷,兼济之志并未因此消磨殆尽,于是他们不得不背井离乡奔波于求仕之途。此期文人的人生求索、精神挣扎的心路历程就集中体现在《古诗十九首》这一组早期文人五言诗中。
一、生命悲情主义
这些游子羁留客外或是宦游以博取功名,或是为生计而漂泊,心怀愁苦,局促难安:“《晨风》怀苦心,《蟋蟀》伤局促”,“思还故里闾,欲归道无因”,他们有家不能回,而这种境况远非暂时:
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
(《涉江采芙蓉》)
羁旅在外的游子采摘到表达爱意的芙蓉花、兰草一类新鲜美丽的花草想送给思念的人,却因为“她”在漫漫长路的另一头——“旧乡”而无从达至,这种因空间阻隔而产生的“同心而离居”的错失怎不令人心生忧伤?此处采摘芙蓉、芳草送给恋人或亲友是中国古人的一个传统,如送别时折柳相送或别后寄赠衣物、信物,我们可以解读为主体表达思念之情的一种象征手法。从末尾两句“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来看,此类因天各一方而产生的思念“忧伤”并不是偶然的一时一地的短暂别离,而是终其一生无由团聚的现实人生悲剧。也就是说,这种因爱结合、因羁旅导致离居而产生的愁苦甚至折磨毕生。羁旅的游子不仅承受着情感失落之痛,而且生活经常陷入困顿,身体承受饥寒煎熬。“凉风率已厉,游子寒无衣”,在情感空置与物质匮乏的双重痛苦体验下,游子们的旅途生活怎能不蒙上厚重的悲愁与凄苦氛围呢?透过这类诗歌文本所表达的情感向度,也许读者更能读懂中国成语“生离死别”,“生离”为什么同“死别”作为并列词组组成一个成语!深陷此中的抒情主体可以切肤体会到,二者所包蕴的人生的悲苦与惨切同样沉重。甚至“生离”更甚于“死别”,因为“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的“生离”是一辈子长久的痛苦牵系与煎熬,而“死别”是“一恸之悲”而后止的短痛。
浸透心脾的悲凉、愁苦之情,在包括以羁旅为主题的诗歌在内的整个《古诗十九首》中居于主导地位,铸成《古诗十九首》浓重的悲情主义抒情格调。人生无奈,命运多舛,悲情之链牢牢地嵌套在这些羁旅在外的下层文人身上。因此,他们往往直抒愁怀。但这些诗歌“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形成直朴而不肤浅、外物迁逝却心恒悲切的古诗抒情传统。正是出于对个我生计困顿的感喟,对暗淡前途的失望,对挣扎轨迹的回顾、反思与抒发,《古诗十九首》对有限“人生”的生命感受格外敏感: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
(《青青陵上柏》)
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
(《今日良宴会》)
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
(《回车驾言迈》)
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
(《驱车上东门》)
人生,就是一段或长或短的生命活动时段的延续历程,对人生的感受实际上就是对当下流逝着的时间之流的感悟、反思和展望。《古诗十九首》伤人生虚度、感生命凋零的悲情意识,是建立在对作为具体感性有限存在的时间——生命脉搏跳动的同情体验与真切把握之上的,有一种特别震撼人心的感染力、穿透力,千载之下益愈动人!在此种灰暗心境的支配下,即使在百草逢春向荣的春日也体会不到丝毫时令给生命赋予的生机与愉悦:
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
(《回车驾言迈》)
在这里,这位羁旅他乡因求“荣名”而未果的游子欲“回车”——尝试穿过长长的时空隧道回到另一头的过去与故乡。但时光无情演逝,给他带来美好而温馨回忆的过去与故乡已物是人非,眼前的故土对抒情主体而言如同陌生的他乡一样冰冷。面对作为心灵家园和情感寄托而盛满温情的故乡的沧桑陌生景象,轰然坍塌的是抒情主体的人生精神寄托。生命绵延中的过去与未来都是不可追索的沉重与虚无,现在的“他”那无根飘零的人生因此变得无所皈依而深陷冰冷的现实困顿。无论是时间维度还是空间维度,现实人生对这类士人而言都意味着自我否定和双重失落。抒情主体置身叶绿草长的春天原野却在系念“故物”——别离故乡时的生活场景,由此联想到生命的转瞬盛衰,悲叹身名未立、功业未建。他的思维逻辑如是:由于人生如花草苗木“奄忽随物化”般转瞬即逝,只有建金石之功,身名才能永垂不朽,才能安顿失重的心态。由此,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不绝如缕的、流淌在游子们血脉中的儒家兼济之志,以及“兼济”这个人生十字架给他们带来的生命不能承受之重的挤压感和压迫感。
二、延绵时间对空间物象的重构
《回车驾言迈》中另一个可堪玩味的地方是,这首羁旅诗以空间切题,并且前四句一直通过空间视野的描述铺开,但是经过五六句过渡后迅速转折进入到对时间之维的感受与抒发之中去。其他此类游子羁旅诗如《行行重行行》、《青青陵上柏》、《涉江采芙蓉》、《庭中有奇树》等似乎都有此种抒情的结构取向: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
(《行行重行行》)
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
(《涉江采芙蓉》)
庭中有奇树,绿叶发华滋。攀条折其荣,将以遗所思。馨香盈怀袖,路远莫致之。此物何足贵,但感别经时。
(《庭中有奇树》)
在这些诗歌中,时空并没有复合交叉错乱,空间和时间被明显整饬地切分到诗歌的前后两节中。写空间的诗句以广延铺陈叙述为主,写时间的则多为抒发生命悲情意识。总体而言,在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早期文人五言诗中,空间的出场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作为时间表现的铺垫或者说引子而已,有时充当比兴之起兴的功能。如《行行重行行》中“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从空间展开的开篇八句诗整体作为比体兴起下文中的“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抒发由岁月空淹引发的悲切。再如,《青青陵上柏》的“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托物起兴,兴起“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这一对生命过程短暂的感触。也就是说,此期诗歌中作为空间存在的物象的审美意义并不在于其作为景物或景致被寓目与被观赏,而在于作为比体兴起具有时间提示意义的情绪变化。因而,这些诗歌的表述方式自然以叙述为主,因为其客观功用在叙事、提示方面的使命颇重。
与《古诗十九首》中的羁旅诗具有比较意义的是《诗经》中的征役诗。征役诗是抒情主体离家在外,或在征战或徭役过程中所见、所闻、所感经历的写照,如《豳风·东山》、《小雅·采薇》: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鹳鸣于垤,妇叹于室。洒扫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见,于今三年。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仓庚于飞,熠耀其羽。之子于归,皇驳其马。亲结其缡,九十其仪。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
(《诗经·豳风·东山》)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日归日归,岁亦莫止。靡室靡家,狁之故。不遑启居,狁之故。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日归日归,心亦忧止。忧心烈烈,载饥载渴。我戍未定,靡使归聘。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诗经·小雅·采薇》)
这两组征役诗的共同抒情特色是都从眼前的现实处境(“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或社会活动(“采薇采薇,薇亦作止”)落笔,起始二句在各节中重复充当起兴句,后面部分则是抒情主体的内心活动的叙述。《东山》共有四节,此处引用的是该诗的后两节,记录的是抒情主体——一位长期戍边的战士即将回归故乡时悲喜交加的心理活动,而且主要部分都是回忆和想象。由于抒情主体还在回乡行进的途中,因此主体的想象是对家乡温馨缠绵生活的展望,回忆则充满离别时的难舍和分离后的凄苦,以及对时光流逝所带来的不确定性的悬疑。《采薇》“采薇采薇”的抒情主体是一位尚在边地戍守的军人,他早已归心似箭,但为了抵御狁(战国后称匈奴)侵略而一再推迟归期。而到“杨柳依依”,抒情主体显然已在归途,重在表现物候和心情的巨大反差。由此可见,《诗经》中的征役诗,对现实空间的描述基本上没有展开甚至未曾观照或经历过,更多的是通过想象或回忆来展现时间之维的过去和现在的沧海桑田、物是人非的巨大反差而形成悲喜交集的体验,强调场景和视阈的巨大反差和未来的不可知性。也就是抒情主体已经通过对照的方式找到以时光的变迁、时令的变化来表现内心感怀的抒情程式,但是时光之流中的空间物象与画面却并不一定与某种倾向性的情感产生固定的关联。季节与某种固定情感取向(通常表现为悲或喜)的固定联系则要到《楚辞》,集中表现在《楚辞》发明的悲秋主题上。
而在两汉的“一代之文学”——汉赋中,凸显的是抒情主体对恢宏阔大的空间审美经验的极致追求:在数量的极度排比中追求阔大,在空间的延续中企慕恢宏,在物类的汇聚中去把握和表现“博物”之繁富。司马长卿(相如)《子虚赋》中子虚对楚泽——云梦之浩渺空阔的记叙,就是以空间方位为坐标一气排比楚地富饶的动植物类:“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则盘纡岪郁,隆崇嵂崒;岑岩参差,日月蔽亏。交错纠纷,上干青云。罢池陂陀,下属江河。其土则丹青赭垩,雌黄白坿,锡碧金银。众色炫耀,照烂龙鳞。其石则赤玉玫瑰,琳珉昆吾,瑊玏玄厉,碝石碔砆。其东则有蕙圃,衡兰芷若,穹菖蒲,茳蓠蘼芜,诸柘巴苴。其南则有平原广泽,登降陁靡,案衍坛曼。缘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则生苋菥苞荔,薛莎青苹。其埤湿则生藏茛蒹葭,东蔷雕胡,莲藕菰芦,庵闾轩芋。众物居之,不可胜图。其西则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外发芙蓉菱华,内隐钜石白沙。其中则有神龟蛟鼍,玳瑁鳖鼋。其北则有阴林,其树楩楠豫章,桂椒木兰,檗离朱杨。楂梨橙栗,橘柚芬芳。其上则有鹓雏孔鸾,腾远射干。其下则有白虎玄豹,……”无尽空间的延展是以品类繁多的物类(动植物)充实其间,品类的变化是空间方位转移的标志。汉赋中的空间是具有实物质感的方位延展,《汉书·艺文志》所谓,汉赋“感物造端,材知深美”,赋成为表现和装盛抒情主体才智与学识的容器。由此,汉赋中这种宏阔的空间审美经验形成两大特点:其一表现为空间中有着人与物的充实与纷繁,其二表现为空间在广袤、周延、平直中展开。而在包括羁旅诗在内的《古诗十九首》中,抒情主体对外在自然的观照与体验,由以汉赋的空间广延为主转向了以时光变迁而产生的强烈的生命迁逝体验为抒情脉络。这是一个由外在显象的空间转移至内在驿动的体验迁移,表现为一个由外入内的移入过程,即由对外物毫无体验的无限铺陈与辞藻堆垛,到基于生命同情的流光迁逝的感性体验,这是审美时空转换的一个重要表征和成果。
虽然《古诗十九首》时期所体验到的还是如长江之水一样延绵不绝的持续的时间感受,但抒情主体已经能够将延绵的时令感受与所接触和想象中的外物变化结合,产生即时的情境式生命体验,这便是《古诗十九首》奉献给中国诗歌最新的审美经验。在叙述方式上,《古诗十九首》审美经验的时令意识是以情感为尺度,按照情感起伏的节奏剪裁诗思,通过不同时间背景下的空间界面的物事叙述来兴起主体的情思:
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下有陈死人,杳杳即长暮。潜寐黄泉下,千载永不寤。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送,贤圣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
(《驱车上东门》)
去者日以疏,来者日以亲。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思还故里闾,欲归道无因。
(《去者日以疏》)
这两首诗虽然不乏空间方位的转换,但是,不管是《驱车上东门》还是《去者日以疏》,两诗中的抒情主体都不约而同地走到埋葬逝者的坟墓场,由是激起人生无常、沧海桑田的生命悲情意识。而生命意识往往具化为一种本能的、真切的时间感受,可见主体还是以时间为纵深经线展开水平纬度的空间物事叙述与组合。值得注意的是,《古诗十九首》中由人生、生命而感发的时间意识还是一种粗放型的、大单元的时间概念。也就是诗中的时间单元较大,最常见的是以自然时令的春夏秋冬节候的变化为基本的节令时间单位,甚至以更长的时间段为单元激发生命感受。“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是这种时间意识的典型表达。比一年四季更小的时间单元,如黑夜与白天,或将一天中的其他更小时间单位对举而产生的时间流逝感,在《古诗十九首》中是看不到的。“明月皎夜光,促织鸣东壁。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和“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等诗句中虽然出现了用来指示夜的时间意识的明月和星座(玉衡、牵牛星、织女星),但是没有产生星夜与白昼相对照的时间迁逝感。
由生命无常所刺激与催化下的时间意识,在《古诗十九首》中是一种普遍的、难以捉摸的、不可化解的迁逝悲情意识。因此,《古诗十九首》的抒情方式整体上是在这种悲情时间意识的直接作用下形成的。时间本不是一种可以直接把握的现象界实体,在《古诗十九首》中抒情主体把它对应于有限的生命历程,时间由此落实为具象的人生经历和生命过程。《古诗十九首》中时间意识的主线是对人生无常、生命短暂的切肤痛感体验,时间的无情流逝、变迁导致对人生、生命与命运把握的无可奈何,进而产生幻灭感、及时行乐的享乐观甚至求仙得道的飞升思想。如上文引用的《驱车上东门》中的“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送,贤圣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不过,游仙与方外之思在《古诗十九首》中是一种遭否定的、自我麻痹的生命体验与生活方式,抒情主体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抒情主体的悲愁都是现世的、此岸的真实底层生活感受,而没有宗教式超世、彼岸的寄托。
重要的是,在这里通过这种无意识的升仙思想的流露,我们可以体会到《古诗十九首》的抒情展开方式,即一种多维的、网状的、复合的生命感受,一改民间乐府古辞创作中线性的、单一的抒情进路。这种复杂的基于时间感受的生命意识上承宋玉《九辩》所发明的“悲秋”主题。发展到《古诗十九首》时期,这种生命意识对应于时令之春夏秋冬形成复合的生命体验——一种建立在个体生命迁逝之悲情基础上的体验。其美学意义是,《古诗十九首》的迁逝时间美学彻底置换了庄子所构想的自然而自由的齐物式感性经验:“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慨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夏秋冬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嗷嗷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在庄子那里,生死如同“相与为春夏秋冬四时行也”,纯然是一种无生命症状的四季节令轮回,一种融入大化的自然气化运动,一种自然规律的演化形式,因此庄子是体会不到由于时令的变化而引起的生命流逝的悲情的。
三、对行旅诗的导引
作为“五言之冠冕”,《古诗十九首》的创作成就在多方面对五言诗的发展具有典范(paradigm)意义,后世多个五言诗的文类滥觞于此。从连续的诗歌运动进程来看,《青青陵上柏》、《涉江采芙蓉》、《明月皎夜光》、《回车驾言迈》、《东城高且长》、《驱车上东门》、《去者日以疏》等诗作以抒发游子愁思为题旨的羁旅诗,奏响了魏晋以降行旅诗问世的先声。从某种意义上说,《古诗十九首》中的羁旅诗本身即为早期行旅诗,因为接下来的行旅诗不但在时间先后与气质呈现上与之有承续性,而且可以见出古诗抒情传统的发展与新变。从“时间上”而言,就是《古诗十九首》羁旅诗与建安以来的行旅诗在历史纵向发展上看,是先后承续关系。至于《古诗十九首》中羁旅诗的精神“气质”主要表现在:以羁旅诗为代表的《古诗十九首》真实地呈现了一群挣扎在社会底层的文人的阴柔哀婉的情感样态。这种阴柔哀婉的情感格调在建安及其以后的行旅诗中一变而为“慷慨以任气”的刚健昂扬,都是个体觉醒后的个性情感气质的任真表达,他们饱满、直朴的情感浓度是一脉相承的。溯源性追索可以见出,《古诗十九首》中直朴缠绵的抒情方式上承《诗经》的国风传统,是《诗经》之“风”一系民间采诗传统的集萃和提高,且这种气质对后起诗类产生了持续的影响。刘勰认为《古诗十九首》“直而不野”,钟嵘说“《古诗》源于《国风》”,都是基于《古诗十九首》之前的创作成就对它的良性沾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