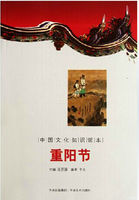吾留家四旬即行,至今抱愧恨未已。族兄叔邍第四子之芳来北京,将归乞言,故书吾之耿耿者勉之,使务学为善,庶不辱其先,汝勉之哉!归见同宗子弟,其悉以耄言励之,如能用吾言,非独老人有光,吾宗有光。苟不用吾言,或忝先世,非独不可见先祠,吾亦不愿见之,汝往勉之。”士奇对后辈晚出的失望跃然纸上,一纸难尽!不得已发出“惧吾宗之衰也”的哀叹。更使他痛心疾首的是其长子稷,“尝侵暴杀人”,有“横虐数十事”,受到朝廷惩处。名重天下的朝廷老臣,面子被不肖子丢尽了,年近八旬的士奇遇此打击郁积成病,他意识到维持故家更形重要。早在稷出事前,士奇就曾告诫他:“乡邑近年故家子孙皆以纷争产业交恶,此吾所甚薄者,汝宜戒之!汝宜戒之!”可惜杨稷一意孤行,酿成大祸。
杨士奇临终前,作《示长新妇(九事)》,对保持家风进行最后努力。他与杨稷的妻子说:“我今年七十有九,只为稷不孝违背父训,专交小人,作恶犯法,今得死罪,致我受气成病,渐至危,殆亦不过年间必死,理无疑也。汝吾家长妇,今家中之事一一付尔掌管,一家大小长幼皆付托汝,汝需每事尽心。今遣归发落数事,可皆遵依,行之勿违,切不可听信小人之言,有所改易,切记切记。一、田土多则税粮科差繁重,必至累子孙破家荡产,苦害难胜。即尽弃远乡田土山塘,皆不可要,近乡田土池塘利薄者,亦不可要,或还原主,或卖与人,皆须作急发落,不可听小人邪言,依阿不舍,至嘱至嘱。一、吾儒者之家,不可思量要富,户下田不许过百二三十石,户下粮不许过三四十石,尽足岁用,切。
不可过多。过多则后来必累子孙,为父母不可无远虑,切记切记。只是许多钱粮在户,后来科差子孙也,自难当。”士奇所言九事的头两件事就是如何保家,他告诫占田不可过多,不可思量要富,表面看是为避免科差之累,实质是坚守儒者之家的“文行”传统。士奇接着便说了我们曾在前面所引的——把自己收集的各种文献作为传家之宝、培养子孙读书不绝读书种子的话。总之是仍要成为故家。事实上故家的传统是很难一下子割断的,士奇的这些家训本身就已成为故家传统,教示、激励着后人。下文将要谈到的杨氏子孙不断有出仕者修谱就是一个证明,士奇可以稍慰矣。
士奇的宗族观也得自于自身的家族史。泰和人梁潜评论杨氏说:“惟杨氏之先世有盛德魁杰之人,其文章政绩蔚然有声于时。及其后也,遭世之乱,仓皇山泽之间,悲歌而流涕者,其言亦足以自著其志。盖太平之际,贤者皆乘时而用,及其乱也,皆沮塞而困穷,此势之所必至,无足怪者。大明之盛,杨氏之后人又以其学兴,至今学士君遭蒙主知,遂掌纶命,兼侍青宫。其清操雄文,足以追继先烈,恩典所加,贲于前人。”梁潜还说:“在吾邦世家文献鲜有过杨氏者,方宋元间杨氏所居台榭之壮接乡间,田园之富连阡陌,及丧乱起,凋落而消亡者多矣。独诗书礼仪之泽浸润涵蓄,沛然而不竭。予获与侍讲君同侍禁林,君之曾大父吟窗公以廉洁忠厚著声前代,累官翰林待制致仕,事在《元史·循吏传》中。吟窗公诸子如平洲、如望之,皆擅能文章。然皆遭时之乱,卒死于穷困,不得大振耀于时。今侍讲君生逢治世,列位清华,方受知圣上恩遇尤厚,而其从子相又擢进士第,居翰林。父祖子孙百数十年既偾而复兴,既坠而复振,何其盛哉。吾于是乎有以观君子之泽矣。谱之作徒然哉!”杨氏在宋代已成名族,特别是士奇的曾祖在元代官翰林,名重一时。但杨氏在元季衰落,至杨士奇重新崛起,振兴家族。值得注意的是,士奇非科举出身,一岁丧父,由外祖父教授学业,孤贫力学成名,因出色的文史才华被荐入翰林。他的成功的确与家学家风分不开,士奇幼时,母亲教导他:“吾初归汝家,见汝父昼夜不辍者四书诸经,余力则玩子史,汝今宜专事经传,未可泛阅,枉费日力。”并说“人居世未必长贫贱,亦未必长富贵,但贫贱入富贵,非读书而未易得也。”又说:“自我归汝家,耳闻目见杨氏仕者,皆以儒术进,皆秉廉洁,从来无以赃败者,虽家贫而誉好,汝曹勿坠也。”外家陈氏亦是世家。外祖父、母亲对士奇良好的教育,祖传的故家遗风,均影响他产生以故家论为中心的宗族观。
杨士奇给予本族及当地以相当的影响。杨氏族谱不断续修,明嘉靖年间,泰和人欧阳德说杨氏谱:“正统丙寅(十一年,1446年)评事德敷复修之”,今余百年,“续成新谱,其义例一遵文贞之旧,盖不能有所加也。论者狃于所见,乃谓古圣经训、时王政典犹未能人人兴善惩恶,谱区区未必为益。夫亦弗思尔矣,离逖他邦者闻乡音而喜,邂逅相犯者俄而知为同姓,遽惭悔自释。况谱之为教萃之于未离,和之于未隙,比于铎徇箴诵,不犹愈耶?兹文贞公所为拳拳者乎!公曾孙行人海、玄孙选主事载鸣,方缵成先德,响用于时,中兴休运,又将竞起而翼襄之,以益昌厥家。”可知士奇后人仍其谱例不断续修族谱,乡人以士奇重视修谱而批评忽视修谱者。士奇曾玄孙秉承先德,出仕中央,杨氏后继有人。杨德敷正统年间所修谱,有泰和人王直序言,谈到杨氏在宋元之际的盛况:“允素乃徙泰和,世以宦学显闻,后十七世有三人者联贡于漕,同授登仕郎,声称赫奕,杨氏之一盛也。”有助于了解杨氏在吟窗公以前的宦学。王直并高度评价了杨士奇的修谱活动:说他“惓惓于谱牒,以著其本,联其支,此仁人君子尊祖敬宗之道也。夫故家令族之所以光明硕大而不至于泯没无闻者,以谱牒传焉耳”。把不断修谱视为故家令族的标志。王直还认为“德敷明经取进士,今为大理评事,续著此谱,以成公之志,其贤可知矣!”肯定士奇宗族观念对后世的影响。事实上,杨氏在正统和嘉靖两次修谱之间,于正德年间还修过一次族谱。泰和人罗钦顺《泰和杨氏重修族谱序》说:“杨氏之居泰和,世久而族益蕃,遭元季兵乱,谱牒无复存者。国初乱定其族有隐君子曰与芳,尝追忆旧闻,旁咨故老,辑为谱图一帙。及太师文贞公出,乃据以作谱,用联属其族人。其后叙州太守德敷君因而续之,皆有版本行于其族。迄今正德丁卯(二年,1507年),又六十余年,后生绳绳,已多斑白之老,而名字犹未有登载,其承传序次,将久而或淆焉,谱其可无续乎!于是义官光序君慨然以为己任,顾族人散处不一,远或百数十里,或占籍他郡,乃驰书遍访,尽得其详,既克成编,将复锓诸梓而属序于余。”他称赞杨光序“能上体文贞与叙州之所用心,而惓惓以谱牒为重”,“无忝其世德”,不无感慨地说道:“杨氏之世德盛矣!”由上可知,泰和杨氏以修谱为世德,自杨士奇之后,于正统、正德、嘉靖年间不断续修,并请泰和人王直、罗钦顺、欧阳德先后作谱。
序,以光大祖德激励后人。此三人均是进士,都曾任官尚书,他们的谱序对教育杨氏族人、增加杨氏族人的自豪感和自信心有不可低估的作用。而王直、罗钦顺、欧阳德的谱序也有弘扬世德、修谱以传承故家的共识。特别是罗钦顺还指出:“君子之所先,莫大于文行。诚能汲汲焉用力于此,有行以为本,有文以为华,将所以大其族者,不亦有余地乎!莫非文也,而谱牒亦其一事,凡族之谱牒,非有才子孙出,盖亦莫能修之。谱牒不修,则本源弗明,昭穆弗辨,仁孝之道、雍穆之风,鲜不微矣。前代虽有显者,其风声事迹亦不复接于耳目,又安知践修之责之在于我,求其能免于卑陋而聿进于高明,岂不难哉!故善观人家族者,即其谱牒之废举而其昌大与否,亦自可见。”罗氏关于“文行”和谱牒与世家关系的论述,与杨士奇的有关看法如出一辙,使我们看到泰和故家的传统和杨士奇对后世的一定影响。
小结
杨士奇所作族谱序跋对宗族和修谱的论述中,有一个核心的东西,这就是他的故家情结。他的族谱序跋富有历史沧桑感,描写出一幅幅故家盛衰消长的图景,展示了世家名族顽强的生命力。他的族谱序跋洋溢着对诗书、仁德传家的礼赞,揭示了望族存在的基础在于文化的传承。士奇笔下泰和、吉安等地的宗族,主要是些故家,他们正是依靠世传文化取得科举和政治上的成功、维持望族的地位并进入政界和上流社会的。士奇出生于元朝末年,闻见了泰和及吉安大族的衰败,经历了破落家族的艰辛生活,也看到了世家名族的复兴,品尝了重新崛起的喜悦。他的故家论充满士族的自信与优越感,充满对富贵暴发户的鄙夷,与易代之际高岸陵谷的社会现实分不开。通过杨士奇所作族谱序跋,我们看到明初泰和及吉安宗族势力的强盛,这些宗族有不少出仕者,有的还位居高官,他们有因婚姻、师生、科举、同朝等关系结成社会网络,泰和及吉安是一个士大夫宗族为中心的社会。杨士奇所作族谱序跋虽然也有一定的政治性,但更多而且更重要的是探讨故家的维持与发展,将修谱的实质定位于延续故家的传统。杨士奇所作族谱序跋的特色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