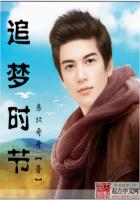拂晓之前,晦夜未央,湿润的气息清冷如水,雾气影影绰绰如同彷徨的幽灵,无论茅屋、石壁、残垣都被苍白的雾霭层层包裹。
星辰寥落,万籁俱寂,然而巴东郡守王羲之却已离开住处,空着手,只披着单薄的衣衫向城防走去,彻夜难眠令他头重脚轻,但他毫不在意,此时,没有什么比鸨羽的动向更让他忧心忡忡。
当他踏上最后一级石阶,最终出现在高耸的城壁中时,冰冷的晨风正肆无忌惮涌过城垣,他不禁打起寒颤。
荒原上满目疮痍,布满斑驳的暗影,极目之外,云翳的彼端已透出些许清明的光泽,夜色将尽,神农溪水流汩汩,可是天乌蜿蜒的营盘却依旧静谧如昨。
“也许,是莽草和雄黄的毒性生效了。”王羲之在风中自言自语,希望此般静谧,将会一直持续。
一点寒光毫无征兆地闪现,伴随着尖厉的啸声,擦过他的面颊,打破了拂晓的宁静,转眼已深深没入石壁,王羲之本能地隐入掩体,接着开始侧耳倾听...风声如旧,只是更添了凉意,是汗,他知道,汗已浸透衣衫。
他在掩体后隐身片刻,之后开始寻觅寒光的去向,在苍白的石壁衬托下,王羲之并未费力便找到了它——一枝玄青色的羽箭,它仍在不住震颤,发出细微的喧嚣,黑羽的箭尾附着一筒苍白的锦帛。
是鸨羽长箭,鸨羽的信物。
王羲之悄悄起身,沿着寒光来时的轨迹谛视,此时静谧的荒原除去盘桓的雾气外别无他物,溪流湍急,天乌的营帐中依旧毫无生息。
对方似乎只是想传递讯息,他把目光投向附着在羽箭尾端的棉帛,或是,炫耀武力?尽管他感到匪夷所思,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样的臂力,什么样的强弓,才能将一枝孱弱的羽箭射入石壁,在相隔如此迢遥的距离之下。
在最后一次确认安危后,王羲之走出掩体,开始尝试拔出羽箭,可是箭尖已嵌入石壁,动弹不得,他只好单独解下棉帛,“鸨羽不忍伤及庶民”其上一行字迹寥落,之后署着耆煌两字。
王羲之听过耆煌的名讳,被称为毁灭的末裔、继承饕餮之名的武者,是鸨羽的王。“耆煌,耆煌,不忍伤及庶民...”他沉吟着将锦帛揉作一团,可是随即又将之展开并叠好,收入怀中。
若是献城,可保一城性命,耆煌能左右支雄的意志吗?他摇了摇头。此时天光微亮,东方现出晨色,巴东住民纷纷开始忙碌,炊烟正陆续升起,忙于拾掇的农妇不时谈笑,男人们倚门而坐,一面聊着战事,一面为他们的女人分担家务。
这是王羲之早已熟识的光景,此刻他却感到心中五味陈杂,世事与生活不过如此,不过是烟灶旁清闲的谈笑,不过是如朝露般五十年,又何必为自己套上种族与国别的枷锁?
他思索着,安静走下城垣。
城中只有过冬的储备,可巴东的战争将持续很久,直至铁壁崩塌或是天乌退却,若耆煌言必信,对住民来说未必不是退路,可是...不,他忽然决绝地摇头,不,他甚至曾后悔笃信鸩水的计策,又何况此时陌生的耆煌?他更无权替住民做出决定,据守的目的本就是为捍卫他们的权利,而非剥夺。
“郡守大人,您来了。”有人殷切的向他问候,有人从锅里捞起冒着热气的块茎,手忙脚乱地撒上盐巴递给他,“您吃点吧,大人。”人们咧开嘴,露出真诚的笑意。
王羲之微笑着摆了摆手,如此安闲的清晨,就像城外从未驻扎一支浩瀚的敌军一样,他们没有逃避,即便他们畏惧战争,但这是他们的选择和决定,因为巴东是他们世居的家园,他们渴望在此处生息,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王羲之有了答案,他再次攀上城垣,用尽全力折断鸨羽长箭暴露在外的部分,之后将它和耆煌的锦帛一起狠狠抛下城壁,他已做出决定,与住民相同的决定。
之后他决定返回营中享用一顿温暖的早餐,然而片刻后,他又陷入了新的窘境,在他将自己的想法告诉苏璎珞之后。
“你要留下?先生,鸩水也要留下!”苏璎珞阴着脸,裹在温暖的兽裘中,“是我自己决定支援巴东,想离开时自会离开,先生,你无权命令我!”
“方寸山是神州的守护者,”王羲之说,“八荒使徒应以天下为重!”
“以天下为重?呵呵!”苏璎珞找到了反驳的理由,“先生,以天下为重就不会流连于巴东的险山恶水!”她鼓着脸兀自气愤不平,“鸨羽不是战争巨兽,不是有勇无谋的羯人!”她忽然抖落肩上的兽裘,指着王羲之喊道:“当鸨羽破城,先生,当鸨羽破城,你不过是一个可怜的、费力挥着无量心的垂暮老者,你将和无量心一起消失于混乱,变得,变得与那些残破的巨兽毫无分别!”
王羲之无言以对,他的确已不再年轻,他知道,昔日年轻的时光他奉献给了另一场战争,于是他只好长吁着说:“巴东铁壁不会不堪一击,即便面对鸨羽,”他的语气忽然透出悲凉,“璎珞,你把无量心一起带走,带回司命塔供奉。”
苏璎珞愣了半晌,忽然大喊道:“我端不动无量心!我端不动!”她红着眼,瞳底闪着波光,“还有,该走的时候我会走,城破的时候我会走,不用你赶我!”
“我没有赶你的意思,”王羲之说,“璎珞,我不想让你为巴东做出牺牲,方寸山也不想。”
“算了,”苏璎珞摇摇头重新缩回兽裘,她识得好坏,不过嘴上不客气罢了,“或许如先生所言,真正的敌人藏在心中,不止恐惧与畏怯,还有焦躁,不安,”她望着他忽然心生愧疚,“也许鸨羽不像传闻中那么可怕,”她尽量使语气缓和,安慰自己,也安慰王羲之,“毕竟我们谁都不曾与它交手,先生,可众生却皆知道三人成虎的道理。”
“希望如此,希望它只是虚张声势。”王羲之答得有气无力,之后他倚窗坐下,不再尝试说服苏璎珞。
“先生,虽然鸨羽受雇于石勒,可是支雄刚愎自用不听劝诫,他未必信任、也未必容得下鸨羽。”苏璎珞沉吟道。
“但他们目的一致。”
“那也未必,”她思忖半晌,忽然露出狡黠的笑意,“支雄是独断的暴君,若他轻慢鸨羽,耆煌会怎样?至于石勒的代价,先生,石勒的代价总有耗尽之时,而无主的鸨羽必定以利为先,或许在四凶图的字典中从无忠诚二字,他们更愿加入一场非对称战争,比如从旁协助十万天乌践踏一万巴东,可是...”她眨着眼,“先生,若支雄把鸨羽当作攻坚的先锋...鸨羽,聪明一世的鸨羽,或是战况胶着,不得不面对牺牲时...”
鸨羽不过千人,璎珞是在质疑他们是否真会为石勒的目的牺牲自己,王羲之摇摇头,质疑有理,可是...“要看石勒的代价够不够诱人,”他说,“璎珞,即便最原始的走兽也会因利益狼狈为奸,鸨羽此时出现在神农溪对岸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协助支雄,这是事实。”
“也许吧...”苏璎珞如同泄了气,王羲之也随之陷入沉默,两人不再成竹在胸,而是寄希望巧合,寄希望于奇迹,尽管世间从不会有凭空的奇迹,因为所有偶然都有它形成的必然原因与过程,关于巴东之于晋的重要,甚至之于天下的重要王羲之从不怀疑,巴东是确保天平两端平衡的重要砝码,九黎、秦、燕,大抵天下的所有势力都在耐心等待这场战役的结果,这一切的起因,仅仅是羯皇石勒背后那些生于繁华,从未体会过乱世残酷的人的私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