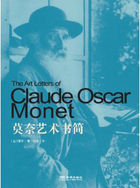对各种人类活动的思想性反思,可以称之为“研究”。电影研究、电影理论都应该是与电影相对应的反思性工作。但是,尽管电影理论似乎在不断地言说着电影,电影却对电影理论毫不关心。在今天的中国,从电影生产者到电影观众.认真对待电影理论者寥寥无几。电影艺术家们在说到“用电影理论指导电影创作”的时候,通常带着打趣的神气——这是明显的事实:中国电影理论无法对当下的电影创作、生产和理解提供实际意义上的帮助。这种状况与中国电影理论的初衷形成了很大的反差。与电影创作的密切联系原本是中国电影理论的传统,“振兴中国电影产业”也是当下电影理论界最热衷的话题,可以说,中国电影理论一直是标榜实践性的。但是,为什么这种标榜实践性的理论姿态,并没有产生具有实践意义的成果?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在“电影产业化”的观念逐步确立之后,中国电影理论自觉发生了转向。最明显的标志是目前电影理论普遍用以指称电影的两个术语“产品”和“文本”。这两个明显打上了后工业文化印记的词语,分别代表了学术界对电影进行研究的两个主要方面,其一是市场,其二是文化。从这两个关键词入手,来考察当代电影理论,或许能找到一些线索。以“产品”为核心展开的电影研究,将电影视为大众文化工业产品。把对电影的讨论转移到社会经济文化体制领域中来,这是一种很重要的理论发展。但是,目前的讨论基本上还是使用“市场”、“商品”、“消费者”这一类描述纯经济领域特征和运作的分析概念。这种理论框架并不能够完全说明电影的生产流通性质。原因很明显,这个术语掩盖了电影作为一种精神文化产品的特殊性,或者说作为“文化商品”的复杂性。文化商品并不是文化性质和商品性质的简单相加就能构成的。因此,在纯经济的框架中探讨电影的商业性质或产业性质,难以触及商业电影的实际问题。
另一方面,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引进的“文本”一词,逐渐取代了过去理论研究中使用的“作品”。术语的转换反映了观念的转换。当“作品”变成了“文本”,传统的电影创作也开始过渡为“文本读解”。应该说,“文本”理论的确为包括电影在内的当代文艺研究开拓了新的思路,以至于许多电影理论家欢呼电影理论的转型。然而,这里面包含着一个更为隐蔽的错误——以“文本”概念为基础的电影研究不可能具有生产意义上的实践性,它不可能取代传统“创作论”的地位(像一些理论家所认为的那样),更不应该也不可能占据电影理论的中心地位。这么说至少有几个理由:
首先,从理论发展的脉络上看,文艺研究中的“文本”概念,原本是随着罗兰·巴特“作者死了”的论断产生的,“文本”之诞生来自于“作者之死亡”。对“作者”的“遮蔽”,对作品产生的历史语境的屏蔽,包括对作者的创作意图的忽视,才使得作品成为没有确定含义的“文本”,使得无限的阐释可能性朝着“读者”开放。当研究者把关注的对象确立为“文本”,意味着他接下来的工作只能是“阐释”,而阐释出的意义是指向“读者”而非作者。具体到电影研究中,这种研究并不关心作品“怎么拍”,只关心读者“怎么读”。目前的电影批评和理论却将之用来针对现实创作问题,并试图由此对创作产生直接影响,这本身就是对方法的荒谬理解。
其次,“文本读解”不仅完全无助于创作实践,也无助于实践性的电影批评或电影评论。我特意指出是“实践性的电影批评”,意在将之与“学院派的电影批评”加以区分,因为文本读解恰恰构成了“学院派的电影批评”的主流,从巴特、麦茨、电影手册派以来,这样的批评在西方和东方高等院校的文学系和电影学专业中十分盛行。但是,这种研究所产生的电影批评与一般观众愿意接受的“影评”完全是两回事,我把后者——“电影评论”——称之为“实践性的电影批评”。“文本读解”对这样的实践性影评毫无用处。因为通常的影评总是需要对具体作品进行评价,分析作品的优劣等等,从而能够对电影市场和观众进行引导。但是,“文本读解”的价值观是明显混乱和隐晦的,或者说它根本就没有价值观,因而它无法对一个作品进行评价。这样的研究只是像巴特那样,通过对“作者”的“遮蔽”,来完成对作品“中心”意义的解构,用无限多的“读者”立场来瓦解整一的价值体系。因此,“文本读解”关心的是读者个人的主观感受,而不是对作品一般价值的探讨。基于这种立场,只有“可阐释”的文本和“不可阐释”的文本的分别,而没有好作品和坏作品的鉴别。这样的立场在理论上并没有什么错误,但从目前电影理论所要求的实践性来说,“实践”是指向价值的,而价值有正价值和负价值之分,有高低优劣之别。实践性的电影批评不仅需要衡量电影作品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标准和价值体系,还需要努力建构和完善这种标准和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文本读解”充其量只能是阐释者的“话语实践”。
再次,从理论的价值来看,“文本读解”只能提供个别的、一次性的阐释,阐释者的个人立场决定了其理论的价值就在于“读解”本身的独特性和不可重复性。它只是特定的读者在特定的时刻对作品的特定感受,是具体的,也是孤立的。从这一意义上说,这种“文本读解”与私人性的文学创作并无区别。然而奇怪的是,文学家不会认为自己在断言真理或生产知识,而“文本读解”的理论家却往往荒谬地认为自己的写作能够提供某种真理或知识。曾有学者指出,“如果一种电影理论只能阐释或解构一部《少年林肯》,这种理论的价值便很成问题。”这正是目前的电影读解的问题所在:从“文本”中阐释出来的“隐喻”、“寓言”、“神话”等“策略”并不是内在于作品的结构和技巧,而是阐释者自行推演的语言。一旦离开“阐释”的语境,这些结论立刻就会失去意义。也就是说,“文本读解”所产生的成果根本不是任何知识,它不可重复,因而也就不能在一定范围内普遍适用,不能累积和发展。正因为如此,“文本读解”的意义开始于阐释也结束于阐释,用它来取代以知识(创作方法和创作规律)为目的的作品研究,是一种荒唐的想法。
最后,即使只是在学院派的专业批评的层面上,对电影“文本”的“读解”也不可能真正实现。这一点是电影研究和文学研究之间的重要差异。在文学研究之中,文学语言与批评语言的同质性保证了诠释的专业性,而对于电影来说,“读解”所运用的文字语言和“文本”的视听语言不是对等的,语言的不对等使得“对话”“流动”的“意义”不可能完整和透明,阐释的“循环”也就无从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以“文本”这一术语为核心的电影研究注定不能成为缜密的、专业意义上的“细读”,而只能以“印象”的方式作用于外在的社会文化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