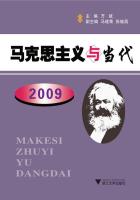或自愿让出权力,也都难以期待,因为基本上没有统治者会承认自己不具备政治才能而自动放弃权力;而教人成“圣”,即便假以时日,也是难为之事,这从孔门弟子无人称“圣”
可略见一斑。这样看来,由于这种王道政治完全依赖于难得一遇的不确定因素,它的实现,确乎是一种运气。不过,也有人认为,“命运是我们半个行动的主宰,但是它留下其余一半或者几乎一半归我们支配”,甚至,那些有勇气的人,“能够更加大胆地制服”它。这也正是荀子所考虑的:怎样使有赖于“时命”的“道”成为可以把握且可能实现的“人道”?他关注这一问题,不只是出于其传统主义立场,同时也是由其现实感所决定的。对他来说,好的政治和道德原则——礼义——业已确定,但是,仅仅认识到什么是“善”,对人们的生活并无太大意义;“善”不是知识,而是行动,并且应该成为普遍化的行动。这也就意味着,“善”不能只是少数有识之士的行动准则,更重要的是,它应该指导所有人的生活,规范他们的行为。由于关注“道”(礼义)如何实现的问题,荀子不可能满足于消极等待“圣人在位”的偶然机运,而必然寻求对这种偶然性的克服。
另一方面,“制服”命运的愿望,使人们必然要考虑那些有助于达成愿望的手段,这也就意味着他们不可能像那些顺从命运的人那样思考和行动,而必须根据现实情形作某种相应的策略性改变。有时候,这种改变可能是危险的,因为,对结果的过分期待,也许会导致忽视手段的正当性,甚至以目的的正当性为手段的非正当性辩护;并且,最终的结果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偏离最初的目的。就荀子而言,一旦他将礼的实践看作最为迫切的问题,他的解决方式及其具体化方案就可能存在同样的危险;实际上,他也明确意识到并排斥造成这种危险的可能性。因而,有理由相信,他会竭力避免上述危险。至于他的努力是否成功,则有待于对其论说作具体的考察。
关于时运无常所造成的德位不偕的问题,一种比较直接的思路或许是,既然“圣王”是实现“道”的关键,那么,不惜代价地使“圣人”获得政治权力,是一种便捷、有效的方式。但这实际上也就暗示了暴力革命的正当性。拒绝并谴责这种方式,是先秦儒家的一贯做法。孟子曾明确表示:“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在这方面,荀子的立场与他完全一致:“……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他们从根本上排除了所谓“用目的证明手段”的思路,并且将手段也看作目的的一部分。在此意义上,他们的道德态度带有“绝对伦理”的色彩。不过,至少在荀子那里,其表现与“绝对伦理”所要求的“不问后果”有很大区别。如前所说,他极其重视结果(礼治),甚至将努力促成此结果视为一种必要的道德行为。在否定了上述以行“道”为由而使用暴力手段获取政治权力的设想之后,荀子明确主张一种在相当意义上可以理解为权变的解决方式。权变意味着他会提出一些带有策略性的观点。这些观点并不能据以论定其思想面貌,因为他的兴趣不在理论建构方面,而在于礼的推行。具体一点说,他试图以这些策略性的观点说服人们,使他们相信礼有益于他们的生活,从而将他们引向礼。对他来说,这些有益于曲成“道”的变通性说法,虽然不必是知识论意义上的所谓“真相”,但具有效果上的“真实性”。从他的论说目的看,这种真实性更为重要。
前人有论,荀子“亦孔氏之支流,其书大旨在劝学,而其学主於修礼”。实际上,《荀子》一书,无论内容还是行文风格,都体现了较强的劝说意趋,是具有特定劝说目的的著作。关于这一点,已有论者提及:“他(荀子)的每一篇论文都是旨在说服具有一定价值、行为和态度的特定听众。”如章学诚所言,战国的个人著述,乃是不得不为之事,所谓“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立言与立功相准。盖必有所需而后从而给之,有所郁而后从而宣之,有所弊而后从而救之,而非徒夸声音采色,以为一己之名也”。以“有所需”、“有所郁”、“有所弊”来描述荀子的时代处境,至为恰切。顾炎武对战国风气有更为尖锐的评述:
如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
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於一百三十三年之间。……
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
对于荀子来说,重宣礼之必要性固然是拯救时弊所急需,但时代风尚颓败如此,“立言”就不仅仅意味着在理论上阐明礼,更为重要和迫切的是,说服那些漠视传统的人,帮助他们建立对传统生活方式的信念。其说服的对象,除了掌握政治权力的人,还包括其他可能成为“士、君子”的人——所谓“因众以成天下之大事”。
常规意义上的劝说,一般表现为口头形式,有特定的劝说对象和具体的场所,也需要听众接受说服者的劝说资格,因此是一种有限制的说服方式。实际上,如刘勰所论,大量的说服是通过书写的方式进行的:“夫说贵抚会,弛张相随,不专缓颊,亦在刀笔。”在劝说对象不确定的时候,诉诸“刀笔”的劝说方式显得尤为必要。在这种方式中,劝说者可以在读者的阅读过程中逐渐取得他们的信任,从而获得劝说的资格。在此意义上,不少写作可以理解为一种说服方式。鉴于荀子特定的思考目的和战国著述者普遍怀有的特殊现实感,有必要也能够将《荀子》视为一部以“说服”为主要目的的著作——虽然有必要谨慎对待那些明显是荀门弟子辑录的篇章,但无需对它们特别排除或另眼相看,因为它们记载的毕竟是荀子的教导。
不仅出于对传统的偏好和强烈的现实感,也基于对人性深刻而实际的考虑,对荀子来说,劝说才是必要且可行的。他相信或希望,通过恰当的辩说劝导,向来凭借机遇实现的“道”,有可能摆脱“命”的限制,成为一种可以现实地把握的人“道”。“道”之不行,在于人们不相信或不愿意遵从它,那么自然地,要实现“道”,就要让人们相信并遵从它。这个思路本质上并没有超出传统的一贯做法。荀子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不:再信任理想化的说教方式,不相信人们会出于对“善”的渴望而自愿服从“好”的生活原则。正是这种对现实人性颇具悲观色彩的理解,使得以下事实对荀子尤为重要:较之直接灌输“真理”,劝导或诱导是更为有效的传道方式。正是因此,不应将《萄子》一书理解为纯粹意义上的思想著作。
这部作品具有劝说的性质,其著者特殊的写作目的,使得它不可能是一部思想独白,而明显是一种辩说。《易·系辞上》日:“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从写作的角度看,“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荀子著作的突出之处,正在于试图通过一种人们可能接受的、灵活且现实的论说方式来文饰“道”,使之可亲可信,从而促使他们依循“道”。就此而言,他的写作其实是一种以鼓动天下之人从“道”为目的的辩说。
也只有通过这样的视角,《荀子》一书中不少看似突兀的地方才可得到合理的解释。这样,《荀子》作为一部注重现实效果的著作,其本身就可以理解为作者的一种救世“活动”。这一点,荀子在书中其实已经明示:“今圣王没,天下乱,奸言起,君子无势以临之,无刑以禁之,故辩说也。”他试图以写作的方式来获得其在现实中不太可能具有的“权力”,从而能够指导人们过一种遵礼循道的生活。通过这种努力,他想表明,“道”的实现实际上是可欲可为的。关于这一点,刘向叙录荀卿书,曾敏锐地指出:“观孙卿之书,其陈王道甚易行,疾世莫能用。”在荀子,“道”之为易行,不只在于他认为可以通过劝导说服人们顺从“道”,也由于他关于“道”(礼义)
及其实现有更为实际的理解或解说——这一点,显然是服务于劝导的需要。“劝导”是荀子推行礼的主要方式和论说基调。
对他来说,最根本的问题乃是礼如何可能在现实中规范人的生活,对这个问题具有时代特点的创造性回应及相应的努力,正是他的思想(或辩说)中真正值得关注的地方。因此,对苟书作体系性的理论建构,很可能是对它的解构。
《荀子》全书呈现出一套较为完整而有层次的劝说策略,但这应该看成作者无意识的结果,换言之,荀子并非特意以一整本书作系统的论说。因为,先秦时个人著述以单篇的形式流传,《荀子》各篇为刘向整理成书也是较晚的事。荀子的劝说工作,实际上是以篇为单位有针对性、有侧重点地展开的,这使得他的某些篇章具有相对独立的主题,而另一些则在内容上明显相互交叉或补充;即便是那些以专章讨论过的问题,在其他篇章中也会或隐或显地有所涉及,这可理解为荀子的基本问题意识和思考方式的连贯性表现。各篇在内容或问题上的共通性、较为一致的劝说风格,使对《荀子》作整体性的讨论成为可能;同时也有必要紧紧抓住荀子推行礼的根本动机,审视其著作,从中理清其基本思路。
与很多同样具有劝说倾向的著作不同,《荀子》有选择地设定说服对象,他们主要是掌握政治权力的人和潜在的“士、君子”。由于古时并非每个人都具备阅读能力,荀子的劝说对象并没有涵括所有人;对于那些他认为注定是“庶民”的人,他寄望于通过一种带有强制色彩的制度来使他们逐渐:习惯礼所规范的社会秩序。他的说服方案也非常现实,主要针对其同时代的人展开劝说。在他来说,既然已看到“道”的实现是一个生死攸关并且有可能解决的问题,“以俟后人”的态度就多少带有逃避责任的意味,因为,持这种超然态度的人,既不讳言自己在关键问题上的洞察力,又试图置身事外,把困难的问题延搁到无需自己付出努力的“将来”。荀子的诸多篇章勾画了他极具现实感的努力,其劝说也可谓步步为营。他首先面对的是一项可以称为“清扫”的工作,这主要体现为他针对诸子展开的辩说。如前所论,战国各家之间的论争从来就不是彼来我往的和平讨论,而常常表现为彼此之间不可调和的断然否定。在这方面,荀子的态度看起来有些特殊。一方面,他的著作涉及对众多学派的理解,承认诸家均有所见;另一方面,他拒斥各家学说的激烈程度又是前所未有的,甚至有点“刀戈相见”的意味:不只在理智上拒绝它们,更主张以一种暴力的方式使这类“邪说”无容身之地。这两种截然对立的态度互不相碍地出现在《荀子》书中,似乎有些令人费解。
但只有将荀子与诸子之间的碰撞仅仅看成学术论争,这种困惑才会存在。实际上,他对诸子展开批评是出于改善现实的目的,并非为立一家之言而排除异己,故他不拘门户之别、承认诸家各有所见,自是情理之中事;而就其劝说动机而言,他与诸子之间的争论又确乎是一种性命之争,不激烈不足以制服对手。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战国时礼乐崩坏的局面,筑成了百家学说相激相荡的思想盛景;但从荀子的角度看,各种“异说”的流传影响了人们的价值取向,加速了传统的崩解。对他来说,劝说的首要障碍,正是这些他所谓的“邪说”。它们不只会败坏人们的趣味,还可能影响到当国者的政治决策。因此,应该从劝说的角度来理解荀子针对诸子的论辩,并将这些论辩视为其劝说工作的一部分。如果再考虑到,其他一些根深蒂固的流俗观念同样也在影响当时人们的趣味和行为取向,荀子必须进行“清扫”的范围显然就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