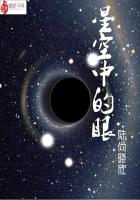关于风,最直接的感觉就是,我觉得风跟时间一样,在我们的生命之中无处不在。在我的记忆当中,太子丹和荆轲唱别时的“风潇潇兮易水寒”太悲壮,刘邦狂放写下的《大风歌》距今也太遥远,而现代诗人徐志摩的诗句“我不知道风是从哪个方向吹”又太文绉绉。印象最深的却是儿时的一堂课,只不过记不得具体的时间了,反正是儿童时代,大概三年级吧,那时候的小学生是要学习自然常识的。我至今清晰地记得,给我们上课的女民办老师很年轻,是个回乡知识青年,扎着两条大辫子,戴一架黑框近视眼镜,段落散文集长得还真秀气。她告诉懵懵懂懂的我们,风是由于空气流动而形成的。老师讲的当然是科普知识,但时至今日仍有一个疑问,一直固执地在我心头萦绕——为什么不是风的吹送而使空气流动呢?因为从小到大,从青年到中年,现在我都已经四十多岁了,我感觉得到的是风在吹来吹去,却从没有清清楚楚地看见过空气流动,倒是随时看到那些或大或小的风,在我生活的这个世界上不知疲倦地跑来跑去。在有知识的人看来,我的这个想法一定非常弱智,滑稽得不可思议。我可不管别人怎么看,只要自己不认为荒谬就没什么大不了的。一朵棉花似的白云远远地飘过来,我就看出来了,那是风然后又从我的身边掠过,我看见花草树木起伏摇曳,这时候我就知道,风朝着花草低头枝叶倾伏的方向跑掉了。
我承认自己面对这个世界,从小就多少有些胆怯和多愁善感,绝不是一个即便身陷狂风暴雨的包围也不晓得疼痛的强者。于是,我常常觉得,既然风无时不在无所不在地吹拂,那么,难免就会有一种忧伤与生俱来——其实人真的就如浮云,总是被四季的风吹得到处飘荡。我永远记得2002年11月19日,我儿子出生那天晚上,我在医院七楼产房外的走廊里焦急、担忧甚至心里有些发毛地踱来踱去。电压不太稳,静得瘆人的走廊里,惨白的光线一会儿明亮得耀眼,一会儿却又暗淡得仿佛危在旦夕似的奄奄一息。更要命的是,我听见初冬的风哇哇地在大楼外面咆哮,我真担心狂风会把整座大楼吹得飘浮起来。要不是不停地为在产床上挣扎的妻子祈祷,我紧张万分的神经可能一下子就崩溃了。儿子终于在凄厉的北风声中降生,放开稚嫩的小嗓子,嘹亮地一阵大哭。哭累了,他就安静地熟睡。但是,风仍然在呼啸,整整喧嚣了一夜。那一夜,我一宿未眠,除了初为人父的激动外,更多的是外面的风声折磨着我,也折磨着我虚弱的妻子,她时而昏睡,时而又被呜哇呜哇的风声吵醒。我心神不定,生怕才来到人世间的儿子,什么都还听不懂就被这该死的风声惊吓蹂躏。
在那样一个狂风大作的夜晚出世,我儿子的生命里便似乎注定始终有一股恶风在游荡。儿子生下来没有吃过一口母乳,一岁以前靠用奶瓶冲泡配方奶粉喂养。后来,儿子一天天长大,我们决定不再让他抱着奶瓶喝奶喝水,是该让他学着用口缸和水杯了。想想人真的很不容易,从小到大再到老,总有学不完的东西需要去学习去适应。我们将奶瓶藏起来,哄他说他的奶瓶被大风吹走了。他呜呜地哭闹了几次,也就不再嚷着到处找他的奶瓶。在父母善意的谎言中,他学会了忘掉一些事情,但也在幼小的心灵里认为,风一阻挡地钻进了我的身体,沿着全身的骨骼和经络游走。风,吹走了许多东西,健康,睡眠,温度……风,又吹来了许多东西,恐惧,忧郁,悲凉……老人们曾经告诉过我,人的肩头有两盏灯,那是生命之灯。我已经目睹过人世间太多的生离死别,我早就明白,生命儿子从小体质差,现在更是有可怕的病魔潜伏在他的心脏深处,通过先进的仪器,我们与医生一起,看得到那个恶魔的影子,却又一样的束手无策。检查结果让我失望,甚至可以说我走到绝望的边缘,我的心情因此一直沉重而又郁抑。作为父亲,我竟不知道自己究竟该怎么做,儿子才可以化险为夷保证以后平安健康。如果可能,我真的心甘情愿拿我的一切,去换取儿子的快乐与安康。现在,我和妻子经常下意识地拉紧儿子的小手,我们非常害怕一阵骤然而至的狂风,突然就将他从父母手里吹走。那些起了大风的夜晚,儿子蜷缩在床上,我总是在黑暗中睁大眼睛,把他轻柔地拥在怀里,让他睡得更安稳一些。儿子睡得很香,甚至发出幸福的梦呓。但是,我依然忧心仲仲,害怕风把他的好梦惊醒。风呼号着,在城市的钢筋水泥丛林里扫荡,扑打在窗户玻璃上,摇晃着窗子,发出令人不安的声响。潜入屋里的细风和着外面尖锐的风声,不可的灯盏,往往是在刹那间被风吹灭的。我和妻子现在竭尽全力在做段落散文集的,就是悉心呵护好儿子肩头熠熠发光的灯火。在挥之不去的忧愁中,看着儿子一天天长大,我越来越坚信,真正的爱,不但会给人予幸福,其实也会让人心徒生莫名的疼痛。然而,就是那份长久真实的疼痛,越发增加了爱的分量和质量。
儿子在艰难地成长,我也不知不觉步入了中年。人到中年,突然发现每个人的年龄都是在做加法,得数不断地变大,而自己生命中的亲友,却是在运算减法,一不小心,就会又减少一个。减少,意味着消失,我们都力不从心,谁也阻止不了这种悲凉的消失。有些亲友尚且活在这个世界上,却不知为什么从我的视线里和走,他们的肉体在这个世界消失了,却仍然生活在我的心里面。虽然不情愿,但中年以后,由不得你,有两个地方会去得多起来,一个是医院,另一个呢,是送别正常或非正常逝去的亲友不得不去的殡仪馆。去得次数多了,我居然与殡葬师成了熟人。他们甚至悄悄把我拉到火化炉前,将厚重炉门上紧闭的观察孔打开,腾腾热气轰地冒出来,惊得我赶紧往后退一步。我清清楚楚地看见,宽大的炉膛里哗哗地燃烧着熊熊火焰,曾经健壮的肉身被烧得蜷缩成一团。纯朴的火化工在一旁悄悄告诉我说,如果要想多留点骨灰,风门就关小点;如果想少要点骨灰,只要把风门稍稍开大一些,烧得细细的骨灰,就会被火烟裹挟着带走不少,最后剩下的,是灰白色的细碎骨灰。因此,只要去到殡仪馆,一看见高高的烟囱升腾起阵阵青烟,青烟在风中摇摇晃晃,最后随风飘远,这种时候,心感凄凉的我,不得不需要接受这样的现实:人的灵与肉,最终都将被风带离这个世界,没有谁能够最终躲过风的清扫。
不过,我还是一次又一次在心里提醒自己,在风把我们从这个世界上吹走,吹得一干二净之前,为了那些我们深爱着,同时也深爱着我们的人,我们一定得想方设法,在疾风吹过来的时候,把自己和那些我们深爱着的人藏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