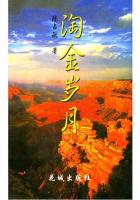玻璃门上方是一排由煤气灯光组成的几个大字——《法兰西生活报》,十分地引人注目。行人一走进这几个耀眼的大字所照亮的地方,顿时全身雪亮,如同置身在阳光下一样纤毫毕见;接着便又回到黑暗中。
弗雷斯蒂埃推开门,向杜洛瓦说了声“进来吧”。杜洛瓦进去后,登上一条建造考究能将整条街尽收眼底但肮脏不堪的楼梯,来到一间大厅里,里面两个实习生向弗雷斯蒂埃道了声晚安。然后,他们在一间类似接待室的房间里停了下来。这房内的摆设尽是灰尘,相当破旧。墙上挂的绿色仿天鹅绒帷幔,已经褪色发黄,并且污迹斑斑,许多地方像是被老鼠啃过似的,已烂成窟窿。
“请在这儿坐一会儿,我立刻就回来。”弗雷斯蒂埃说。
这个房间有三扇门与外边相通。他说着,便从其中一扇门走了出去。
房间里弥漫着一种让人难以描述的奇异气味——编辑部所特有的气味。杜洛瓦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略微有点胆怯,可更多的是惊奇。不时有人从他身边小跑过去。从一扇门进来,在他还没看清他们的面孔之前便又从另一扇门消失了。
进进出出的人时而是年纪很轻的小伙子,一副忙碌不堪的样子。手上拿着的纸牌因其步履迅疾而微微颤动;有的是排字工人,身穿油墨迹斑斑的长工作外套里,露出雪白的衬衫和有点像上层人士穿的那种呢料裤子,他们小心翼翼地捧着一摞摞印好的纸张及一些墨迹未干的校样。除这两种人以外,另一种则是身材矮小、穿着入时的男士进入房内;由于追求时髦,其上身的外套是那样紧,下身的两条裤管也紧紧地绷在腿上,脚上的皮鞋更是尖得出奇。这显然是某个负责采访社交场合的记者,赶回来提供当晚的有关新闻。
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些人进入这间房内。他们神态庄严、气度非凡,头上戴着高筒宽边礼帽,好像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显得与众不同。
这时,弗雷斯蒂埃走了进来,挽着一位身材颀长的先生,这个人约四十来岁,身穿黑色礼服,胸前系着白色的领带,头发是红棕色的,嘴角的两片卷曲的胡髭高高地翘起,一副自以为是、傲视一切的样子。
只听见弗雷斯蒂埃向他说道:
“那就再会了,先生。”
对方握握他的手,说道:
“再见,亲爱的。”说完,把手杖夹在胳膊下面,吹着口哨下楼去了。
杜洛瓦于是问道:
“这个人是谁?”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专栏作家、喜爱决斗的雅克·里瓦尔,他刚看过一篇作品。他同加兰、蒙泰尔合称当今巴黎三个最为出色的专栏作家。他的文章妙趣横生,饱含时代的风尚。他每周撰写两篇专稿,一年所得三万法郎。”
说着,两位旧友便向外走去。此时,从楼下上来了一位又矮又胖的先生,只见他衣履不整,蓄着长发,一副气喘吁吁的模样。
弗雷斯蒂埃向他深深鞠了一躬,而后说道:
“诺贝尔·德·瓦伦,诗人,《死亡的太阳》的作者,同样也是一个一字值千金的家伙。报馆每收到他一篇小东西,每篇最长不超过二百行,便得拿三百法郎付给他。我们到‘那不勒斯咖啡馆’去喝一杯吧,我已经渴得快不行了。”
在咖啡馆刚一落座,弗雷斯蒂埃就喊:
“两杯啤酒。”
他把他的那杯一口气干了,而杜洛瓦却小口小口地慢慢啜饮着、品味着,仿佛在喝什么罕见的珍贵饮料。弗雷斯蒂埃一言不发,好像在思索着什么,突然问道:
“你为何不试试记者这一行呢?”
杜洛瓦瞠目以对,半晌才说道:
“但是……况且……我一篇东西也没写过。”
“这又有什么关系呀?试试看,从头来嘛。我可以聘请你作我的帮手,为我去各处走走,拜访一些人,搜集点资料。你在开始的时候每月可有二百五十法郎的薪酬,车费由报馆支付。你要是同意,我就去找经理谈一谈。”
“这真是太好了。”
“这样,你明晚先到我家来吃顿便饭。我只请五六个人,我的老板瓦尔特先生和他的太太,以及你刚才见到的雅克·里瓦尔和诺贝尔·德·瓦伦,还有我妻子的一位女友,就这样定了,行吗?”
杜洛瓦神慌意乱,迟疑良久,最后才结结巴巴地说道:
“叫我怎么说呢?……我连一件像样的衣服也没有啊。”
弗雷斯蒂埃惊讶不已,说道:
“是吗?真糟糕,这可是一样必不可少的东西。你瞧,在巴黎即使投有栖身之地,也不能没有一套像样的衣裳。”
说着,他摸了摸他的背心口袋,从里面掏出几枚金币,拿出两个金路易,放到杜洛瓦面前,真诚而亲切地说:
“这钱你先拿去,以后什么时候有了,什么时候再还我。先拿去租一套,或者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去买一套,以应急需。抓紧时间去办吧。明天的晚饭定在七点半,请一定准时来。我家就住在泉水街十七号。”
激动不已的杜洛瓦,一面收起桌上的钱,一面结结巴巴地说:
“非常感谢,你对我真是太好了。我是不会忘记你的仗义相助的……”
弗雷斯蒂埃立即打断了他:
“看你,快别说了。再来一杯吧?”
接着,他转过头去喊了一声:
“伙计,再来两杯啤酒。”
等这两杯啤酒喝完后,弗雷斯蒂埃问道:
“咱们到外面去走一走,你看怎样?”
“好。”
随后他们走出了咖啡馆,向着玛德莱纳教堂走了过去。
“咱们到哪儿去呢?”弗雷斯蒂埃问道。“有的人说,巴黎人散步都有着明确的目的,这可不对,我就不是这样。我每晚都出来散步,就不知道往哪儿走。要是有个女人陪伴,去布洛涅林苑转上一圈,倒也有点情趣,可是不会每次都能如愿。我常去买药,那家药房老板和他的妻子喜欢光顾音乐茶座,我可没有这种兴致。我们现在去哪儿呢?实在没有什么地方可去。这附近有个花园,叫蒙梭公园,夏天夜间开放。人们可以坐在树底下,一边喝着清凉的饮料,一边听着飘扬的乐曲。不过这个公园可不是个娱乐场所,而是供清闲之辈们消遣漫步的地方,因此门票很贵,以便招来美貌的女士。人们既可以在闪耀着电灯光的的沙土小径上徜徉,也可以或远或近随地坐下来听音乐。以前在缪萨尔也有这么个类似场所,不过格调太低,跳舞的曲子太乱,同时场地不够开阔,缺乏浓荫和幽暗的角落。只有大的花园才有这种条件,那才荡人心脾呢!现在咱们到底去哪儿呢?”
杜洛瓦诚惶诚恐,一时竟然无言以对。直到最后才嘣出一句:
“‘风流牧羊女娱乐场’,我至今还未去过,我想去看看。”
弗雷斯蒂埃不由叫了起来:
“‘风流牧羊女娱乐场’,天哪,现在去那儿还不会烤成肉饼啊?行,就去那里。那地方总还有点意思。”
于是两人转过身朝蒙玛特关厢街走去。
戏院的门口在强烈的灯光照射下一片明亮,把在此交汇的四条街映照得如同白昼。一排出租马车停在出口处。
弗雷斯蒂埃正要走进去,杜洛瓦在后面拽了他一把:
“我们还没有买票呢。”
弗雷斯蒂埃用一种不在乎的口气说:
“不用,到这儿来我从不用买票的。”
走到检票处,三个检票员向他打招呼。站在中间的一位还将手向他伸了过来。我们这位记者便向他问道:
“有没有位置较好一点的包厢?”
“当然有的,弗雷斯蒂埃先生。”
他接过对方递过来的包厢票,推开包着绒皮并装有铜闩的门,同杜洛瓦一起进到剧场里面。
场内烟雾腾腾,使得舞台和入口部分以及较远的地方被薄雾所笼罩。座位上的人几乎都在吸烟,有的抽雪茄、有的抽香烟,从这些雪茄和香烟冒出的缕缕白烟不停地袅袅上升,汇成了一片淡淡的雾气,聚集在天花板下,在巨大的圆形窑顶下面、枝形吊灯周围以及坐满观众的二层看台上方形成灰蒙蒙的一片。
剧场四周是个圆形通道,入口处尤其宽敞,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人坦然自若地在黑压压的男士中转来转去。墙边立着三个柜台,每个柜台里边都站着一个青春已谢但仍浓妆艳抹的女人,她们既出卖饮料也出卖风情。其中一个柜台前正站着一群姑娘等候着来客。
在她们的身后有几面高大的镜子,从镜子中可以看到她们袒露的背脊和过往男士的面孔。
弗雷斯蒂埃像一个理应受到尊重的人物似的,分开人群,俨然一副非同寻常的神态。
只见他走到一位女招待身旁,向她问道:
“请问十七号包厢在哪儿?”
“请跟我来,先生。”
很快他们被带到一间用木板围成的包厢里,包厢非常小,没有顶篷,地上铺着红色的地毯,四把座椅也是红色的,彼此间间隔很小,客人刚好可以从中间通过。两位异地相逢的好友坐了下来。左右两边,沿着一条直达舞台的弧线,立着一连串差不多的木格子,每个格子里也都坐了人,但只能看到他们的脑袋和胸部。
舞台上三个穿着紧身运动衫的年轻男子正在轮流作吊杠演出,其中一高一矮,第三个为中等身材。
首先,个儿最高者迈着急促的碎步走到台前。他微微一笑,向观众挥了一下手臂,投去一个飞吻。
在他的紧身衣下,呈现出胳膊和腿上肌肉的轮廓。他挺了挺胸,以便把过分凸出的腹部掩藏起来。他看上去很像一个年轻的理发师,头发从正中央一分为二。只见他纵身一跃握住吊杠,然后两手悬在上面,让整个身体像迅速转动的车轮一样,围着吊杠翻转。随后,他绷紧两臂,身体笔直,在空中作了个骑卧势,他完全靠两只手的腕力握住吊杠。
从杠上下来后,他在前排观众的掌声中微笑着再度向众人致意,接着就走到布幕边站着,每走一步他腿部发达的肌肉都得到了充分的显示。
轮到第二个人表演了,这一个比前者要矮,但身体更为粗壮。他走到前台,作了同样的表演。第三个人做的也是同样的动作,可是观众的掌声却要更为热情。
对于台上的表演,杜洛瓦并没有怎么看,他不时回转头去,向身后的回廊张望着,因为那里站满了男士和姑娘们。弗雷斯蒂埃对他说道:
“你看看池座,注意正厅前座,那儿都是些愚蠢的宝货,带着妻儿来开眼界。坐在包厢里的则是爱逛剧院的常客,几个搞艺术的和几个二流妓女。在我们身后的是巴黎古怪的大杂烩。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呢?你仔细观察观察吧。真是什么人都有,各行各业,哪个等级都有,但大多数是些浪荡子。有银行职员、商店店员、政府各部的办事人员,以及外勤记者、妓院老鸨、穿着便服的军官和衣冠楚楚的纨绔子弟。有的刚在饭馆吃过晚饭,有的才从歌剧院出来,待会儿还要去意大利剧场。剩下的人便属于不三不四、行踪诡谲一类的了,一眼就可看出来。至于那些女人,则清一色都是晚间在‘美洲人咖啡馆’打尖的那种。这些女人只需一两个路易便可跟着你走,因此整天都在接肯出五路易的外乡来客,而一有空便会通知老主顾前来相会。她们在这一带操此营生已有六年之久,一年之中每天晚上都出没于同样的地方。除了有时在圣拉扎或卢西纳医院接受治疗以外。”
对他的这些话杜洛瓦已经没有心思去听了,因为正有一个这样的妓女将胳膊靠在他们的包厢上,目不转睛地看着他。这是一个体态丰腴的褐发女人,脸部由于抹了一层脂粉而显得很白,在两道描得很粗的浓眉下有着一双黑黑的眼睛,眼角也描得长长的,显得更为突出。丰满的乳房,把深色的丝绸长裙绷得鼓鼓的。涂了口红的双唇酷似鲜血淋漓的伤口,表现出一种过分热烈的野性,不过却能唤起人们心头的欲望。
她向经过这里的一个女友点点头,把她叫住,是一个把金发染成红色、长得也很胖的女人,用谁都能听得见的声音对她说道:
“瞧,一个好漂亮的小伙子。他若肯出十路易要我,我是一定会高兴的。”
弗雷斯蒂埃转过头来,微笑着在杜洛瓦的大腿上拍了一下:
“这话是说给你听的,她已经看上你了。亲爱的,请接受她的邀请。”
杜洛瓦立即满脸通红,手不由自主地摸了摸放在背心口袋里的两枚金币。
台上的大幕已经落下了,乐队奏起了华尔兹舞曲。
杜洛瓦乘机向弗雷斯蒂埃问道:
“咱们是不是出去避避?”
“走吧。”
他们走出包厢,马上被卷进了走廊里的滚滚人流中。他们被人推着,挤着,身边一点回旋的余地也没有,忽而往东忽而往西。眼前只见到男人们戴着的清一色的高筒礼帽。那些妓女,则两个两个地贴着男人们的胳肘、胸膛和背脊,在他们中间钻来钻去,随意穿行,如同在自己家里一样。她们的脚步是如此地轻盈、敏捷,在男人堆里,她们就像水中的鱼一样自由自在。
杜洛瓦心神荡漾,任凭自己被人流夹着往前走。周围的空气已经被烟草味、汗酸味和女人们身上的香水味弄得污浊不堪,但杜洛瓦吸入体内还是那样地如痴如醉。但弗雷斯蒂埃不行了,只见他大汗淋漓、气喘吁吁,并且又咳了起来,只得说道:
“咱们赶快到外面去吧!”
于是向左一拐,到了一个搭有凉篷的院落之中,两个设计粗糙的大水池,使得院内的空气显得格外地清爽宜人。花盆里栽着紫杉和侧柏,近旁的小桌边已坐了一群男女。
“再来一杯啤酒吧?”弗雷斯蒂埃问道。
“好。”
他们坐了下来,看着从面前经过的来来往往的游客。
不时有个在院内走来走去的女人停下来,面带着媚笑问道:
“先生,能请我也喝点什么吗?”
弗雷斯蒂埃答道:
“可以,请喝杯喷泉水。”
“去你的,真没有教养。”搭讪的姑娘嘟囔着悻悻走开了。刚才依偎在他们包厢后面的褐发女人这时又走了过来。她手上还挽着那个肥胖的金发女友,目光中透出傲慢的神情。这两人可真是天生的一对,不论从哪一方面都十分般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