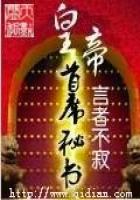1935年3月4日,中革军委召开鸭溪会议并发布命令:“为加强和统一作战起见,兹于此次战役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
一场大战即将来临,毛泽东等人也许已经开始在想象一个崭新根据地里的景象。
出乎意料的是,周浑元根本不接招,一时形成了红军徘徊诱敌、敌军主力坚守不动的僵持局面。
恰恰就在这个当口上,3月10日凌晨,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联名发来急电,请求进攻打鼓新场。
林彪的这个想法是可以理解的。就在前不久,彭德怀指挥红一、三军团取得了遵义大捷,极大地鼓舞了红军。那么还不到28岁、血气方刚的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自然也希望自己能够指挥红军再打上一个大胜仗。
就在红军准备发起和国民党主力部队的决战、为实现赤化全贵州创造条件的时候,红一军团的领导人提出了攻打黔军部队的主张。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讲,这都是一件大事,所以只有召开政治局会议来进行讨论。
为什么一次军事行动要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呢?
原来,为了避免再次出现军事上的独断专行,遵义会议决定取消最高“三人团”。但战争中需要最多的就是不断地做出决策,于是在遵义会议后就形成了一切重大军事决策都要经过政治局讨论的局面。
3月10日天一亮,张闻天就在苟坝新房子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主题简单明确:讨论林彪、聂荣臻进攻打鼓新场的建议。
二
在会上,毛泽东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不能进攻打鼓新场。
理由是红军距打鼓新场有两天的行程,待红军长途奔袭抵达后,面临的将是这样的态势:正面是滇军、黔军,两翼是川军和中央军。
这就等于钻进了张开的口袋,搞不好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然而参会的20多人中,大多数人都支持林彪的意见,认为进攻打鼓新场是可行的。
于是大家就围绕着“打”还是“不打”争论开来,任凭毛泽东如何劝说,一整天下来,大家的想法没有任何改变。
面对僵持不下的局面,张闻天只好提出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表决。
眼看着一个错误的决定就要做出,毛泽东真的急了,提出如果坚持要打的话,他就不当前敌司令部的政委了!
不料众人不仅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通过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决定,还同样通过了撤销他前敌司令部政委的决定,同时决定由彭德怀暂时代理前敌司令部政委。
会议最后确定由周恩来连夜起草攻打打鼓新场的命令,并在第二天早晨正式下达。
会议结束时已是深夜,对红军和革命前途的担忧令早已把个人荣辱置之度外的毛泽东久久无法释怀。
思虑良久,以大局为重的毛泽东决定还是不能放弃任何一点希望。于是,极度疲惫的他提着马灯走进了漆黑的夜色。
通过一条弯弯曲曲的田埂小路,毛泽东找到了周恩来的住处。
周恩来给了毛泽东一次充分阐释、说明自己观点的机会,在周恩来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后,两人又一起找到了朱德,三人认真地探讨了攻打打鼓新场的利弊,最终达成了一致意见。
次日一早,周恩来就提议继续开会重新讨论是否进攻打鼓新场。再一
次激烈争论之后,毛、朱、周三人终于说服大家放弃进攻打鼓新场的设想。
事后,红军破译了国民党的几份电报,证明不仅黔军和滇军已纷纷向打鼓新场集结,蒋介石也判定打鼓新场是红军向西的必经之地,早已暗中做好布置,等待着将红军一网打尽!如果真的去进攻打鼓新场,那么肯定被包了饺子,说不定就会全军覆没。
在是否进攻打鼓新场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之所以能够以一人之力反对大多数人的意见并最终获得认同,是因为毛泽东对当时的敌我形势进行了理性的、充分的、科学的研判。因而清楚地知道红军的根本目的在于跳出包围圈,所以在他看来一仗要不要打,不是能不能赢的问题,而是能不能走的问题。打不是为了赢而是为了走,这是红军长征期间能够摆脱国民党围追堵截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毛泽东做出的正确选择。完成任何事情,理想、信念、热情等固然重要,但在每一个选择的关口只有通过研判做出正确的选择才能确保能把心目中的事业推向前进,这是苟坝会议留给今天的重要启示之一。
取消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决定,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务自然也恢复了。
但毛泽东的思考没有就此停步,苟坝会议上发生的一切让他意识到:总是由20多个人组成的政治局开会来讨论军事行动方针,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决策是不能适应战争需要的,更无法实现真正的机动灵活。
于是毛泽东向张闻天提议成立“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全权负责军事指挥。
遵义会议以来的军事决策过程也让这位不懂军事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感到十分头疼,单纯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决策的弊端他也深有感触,于是张闻天对毛泽东的提议完全赞同。
3月12日,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通过了毛泽东成立“三人军事领导小组”的提议,确定小组的成员为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
苟坝会议的召开是一次意外,没有进攻打鼓新场的提议,就不会召开这次会议。
会议的过程也很意外,毛泽东的正确意见竟然被“大多数”了。在两个月前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才刚刚被确定为高层领导人;在“鸡鸣三省”会议上,毛泽东才成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会议的最终结果更“意外”,不仅否决了本已通过的进攻打鼓新场的决定,还最终成立了新的“三人团”,这使得民主集中制原则变得更加完善。
新“三人团”所达成的集中是在充分民主的基础上进行的集中,是被实践检验了的集中,是真正保证效率的集中。
至此,民主集中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已完全成熟,这是中国革命乃至建设事业中的一件至关重要的大事,没有民主集中制的成熟,中国共产党就需要更长时间的实践和探索,也就会走更多的弯路。因而,从长远来看,成立新“三人团”的意义十分重大。
三
我们到苟坝会议会址开展主题党课活动的时候,大家重走了当年毛泽东深夜去寻找周恩来的那条小路。
当戴着小红帽的我们整齐地走在田间小路上的时候,不远处村子里的小孩们在齐声地喊着:
“红军,加油!红军,加油!”
小孩子无意识的“穿越”,让每个人都精神为之一振。
即便是在白天,这条穿过农田和丘陵的逼仄小路也并不好走。
据当地的向导介绍,从毛泽东当年在苟坝新房子的住处到周恩来的住处,有5里左右的路程。
当年,毛泽东一个人在深夜里靠着马灯的微光走过这里的沟沟坎坎和坑坑洼洼时,他的情绪一定不会好到哪里去,但他的内心一定是坚定的、刚毅的、执着的。他知道,脚下的路看不清顶多自己滑上一跤、摔个跟头,但红军军事作战的路选错了,就可能给整个国家和民族带来灾难般的后果,他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变成事实。正是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让毛泽东义无反顾地在这条崎岖的小路上艰难地跋涉。
所幸的是,毛泽东的努力起了作用,这条路也因而见证和承载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与一次大灾大难擦肩而过的厚重历史。
如果不是毛泽东连夜去找周恩来和朱德,如果周恩来没有给毛泽东重新阐述的机会,我们甚至无法想象究竟会是什么样的结果。也许红军因此又打了一场血战,除了少数人突围以外,绝大部分人壮烈牺牲了,力量一下子衰微了,道路也因此更加艰辛和漫长了。即便我们再乐观地去想象,红军也要损失一部分力量,这不仅会减弱整体的战斗力,也会动摇红军刚刚恢复的信心,其负面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
好在这一切没有变成事实。
苟坝会议上根据政治局集体决策带来的弊端成立了新的“三人团”,这是自猴场会议、遵义会议限制和取消老的“三人团”的指挥权以后,根据实际需要做出的一次大胆的、及时的、正确的调整。如果没有这次调整,红军的指挥体系就不能适应变化多端的战争形势的需要,也就很难形成第三次、第四次渡过赤水河的决议,那么红军的命运也会更曲折。
因而,苟坝会议解决的是一个最实际、最关键、最重要的问题,苟坝会议才是红军长征中的根本转折点。
不得不说,周恩来在苟坝会议上给予毛泽东的支持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
苟坝最初的名字叫作“狗坝”,当地人说这是因为附近有一座山形似天狗;后来还有人发现“天狗山”的对面是一座象山,而天狗山正在朝拜这座有着一条像蛇一样的长鼻子的大象,这些传说更为苟坝增添了几分神奇色彩!
“苟”字是暂且的意思,坝则象征着力量的蓄积。当年中共中央正是在这里先是因为分歧而停顿,之后又因为在民主的基础上加强集中而获得了更大力量。这是一种质变,也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
鲁班场的历史回音
一
在很早以前研读长征的时候,我就意识到了鲁班场战斗在整个长征中不同寻常的分量。正是因为在这次战斗中对国民党中央军形成了震慑,才使得红军三渡赤水能够顺利进行,红军才开始真正地在军事上变被动为主动,拉开了转败为胜的大幕。因而,我一直希望能去鲁班场实地考察感受一次。
当机会终于到来的时候,没想到首先带给我深刻记忆的却是“一部活着的历史”。
那次我们一行人到仁怀考察项目,其中有红色旅游的内容,于是我们就得到了去鲁班场红军烈士陵园凭吊的机会。
当我们走进陵园门口正准备找个人了解一下情况时,一位个子瘦小的老人快步走了过来,热情地和我们打着招呼。交谈中,我们才知道这位白帕缠头、白须白发却十分矍铄的老人已经90多岁了。他叫刘福昌,是这处陵园的看护人,一个人守护着这里已有40多年了。
老人的事迹让我们很是感动,大家就纷纷和老人攀谈起来,这一番谈话让鲁班场的这段历史在我们的视野中变得愈发清晰、深刻。
刘老出生于1919年,1935年鲁班场战斗发生的时候他刚刚16岁。
当年,他躲在山林中目睹了这场惨烈的战斗。虽然战斗给刘老留下了至今难以磨灭的印象,但当初的那个懵懂少年肯定没有想到这场战斗会是历史巨变中的一个节点,更没有想到他自己的人生也将逐渐地融入这汹涌而来的历史洪流之中。
鲁班场战斗之后的第9个年头,已经25岁的刘福昌从一段历史的见证人变成了另外一段历史的亲历者。
那一年,日本侵略军打到了独山,刘福昌成了一名国民党士兵,被编入54军81师无线电排。
后来,刘福昌又成了中国远征军的一分子,曾先后在云南和缅甸与日军作战。日本宣布投降后,刘福昌曾接受派遣押送日本战俘到台湾,等他回到大陆的时候,解放战争已经打响,当时仍是一名国民党士兵的他,先后在山东和辽宁等地参加了作战。
1948年,刘福昌在团长的带领下起义投诚,正式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的一名战士。此后,他参加了渡江战役和解放浙江、福建等地的作战。
新中国成立后,刘福昌曾经跟随部队在福建沿海一带驻扎并修筑工事,1955年,已经36岁的他复员回到了家乡。
这位在解放战争中曾经两次荣立三等功、一次荣立二等功的老兵,因为不识字担心干不好而推掉了当地政府给他安排的公社武装部长职务,做回了一个普通百姓。
1968年,当地政府开始给建于1953年的红军烈士公墓修筑围墙,刘福昌被选为监工。他一干就是3年,也从此与这些当年在鲁班场战斗中牺牲的红军烈士结下了难解的缘分。
1971年的一天,当时的仁怀区区委书记征得刘福昌的同意,决定派他去守红军烈士陵园,从此,刘福昌也开始了一种新的人生。
40多年来,刘福昌就这样伴着日月星辰和长眠在这里的红军战士一起走过漫长的静静岁月。
每天把陵园清扫干净就要用去两个小时的时间,但他一天也没有间断过……作为个体生命,刘福昌的人生轨迹和大历史的车辙先是并行、继而融合,之后又用自己的全部余生续写着那份从历史深处一路走来的真诚和执着。
在“五四”运动爆发的年份里出生,见证过长征中的鲁班场战斗,曾经走上国内外的抗日战场,又先后以不同的身份参加了解放战争,在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上的几次重大事件中,都能发现老人用生命刻画下的痕迹。
同样,历史也在这位老人身上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迹,在交谈中,老人说到抗日时期的往事,激动地撸起袖管让我们看他当年和日本人拼刺刀时留下的刀伤。那伴随了老人半个多世纪的疤痕让我们油然而生敬重之心。
老人简陋的住所墙壁上挂的写着“革命老人”“抗日英雄”“抗日英雄民族脊梁,功昭日月国人共仰”等字样的锦旗,也许算是历史对老人的一个交代吧!
这样一位浑身写满历史、写满传奇、写满追求的历史见证人和亲历者,在已过知天命之年的时候,又选择了为鲁班场战斗中牺牲的红军烈士守墓,既是把自己的生命永远地定格在他少年时期目睹的悲壮一幕里,也是在和平年代里继续谱写着一位老兵的精神和气魄。
也许在一些人的眼里,刘福昌老人40多年来做的不过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诚然,比起当年他跟随大军南征北战的金戈铁马岁月,这些在烈士陵园中一分一秒度过的15000多天确实显得平淡如水。但在40多年的时光中饱含赤诚、饱含激情、饱含虔诚做一件在有些人看来索然无味的事情,这本身就是一种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