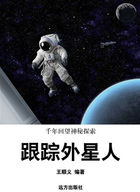以氯化钠为主体的食盐是人类生存、生长所必需的营养品。在自然界中,依它存在的状态不同,又可分为海盐、池盐、石盐、井盐及土盐等。食盐的采集和加工一直是人类生产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古代中国它还与金属材料特别是铁的生产一起构成了国家经济的两大支柱。此外,食盐也曾是医药和炼丹活动中的重要材料。在近代化学工业兴起后,它又成为无机化工生产中的重要原料。至今,食盐仍被视为经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资源。
糖,主要指食糖,是生活中常见的食品和调味品。它主要由蔗糖、果糖、麦芽糖、葡萄糖、乳糖等最简单的碳水化合物组成,是人体新陈代谢、生长发育所必需的营养成分。从化学知识来看,葡萄糖、果糖属于单糖,麦芽糖、蔗糖属于双糖,双糖可以水解为单糖。相对而言,淀粉是一类较复杂的碳水化合物,在酶的作用下,它最终也将被分解成葡萄糖一类单糖而成为生物新陈代谢的基础物质之一。将含淀粉的谷物等转变成上述糖类,其中必然经过了复杂的化学变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认识,制糖工艺当属古代的化学工艺,由于糖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制糖业也应是古代一项不可缺少的手工业部门。
皮革加工成衣着服饰应该说比棉、麻、丝制品要早。兽皮的主要成分是动物蛋白质纤维。当饥不择食时,去掉兽皮表层的毛后,也可烹煮以充饥。为了抗寒,先民们挑选了一些兽皮,加工成皮革,制成衣服或用具。加工的方法主要是鞣制,鞣制的实质是对这些蛋白质纤维进行化学的和物理的加工,这种加工技术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因此制革工艺可以说也是一项最古老的化工技术。
制盐工艺
当人类结束了茹毛饮血的蒙昧生活后,原先主要从禽兽血肉中汲取的盐分,必须寻找新的来源。这就促使人们去认识自然界中天然存在的各种食盐,认识的手段大概主要通过采集、品尝、识别、鉴定,尔后发展起加工提纯的技术,总括出对它的性质及功能的认识。食盐,首先是海盐和池盐很快成为生活的必需品。
先秦古籍《世本·卷一》云:“黄帝时,诸侯有夙沙氏,始以海水煮乳煎成盐,其色有青、黄、白、黑、紫五样。”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则称:“古者宿沙初作煮海盐。”宿沙即夙沙。隋代虞世南的《北堂书钞》引《世本》云:“夙沙氏始煮海为盐,夙沙黄帝臣。”上述记载表明夙沙煮海为盐之事应是发生在五六千年前的黄帝、神农时代,即中国古代农耕生活的开始时期。
《尚书·禹贡》载“青州厥贡盐”,“海岱惟青州”。夏禹已命青州贡盐,表明渤海沿岸和泰山一带当时已是盛产海盐的地区。《周礼·天官冢宰》记载:周代天宫中设有“盐人”,它“掌盐之政令,以供百事之盐”。当时在祭祀中主要供用苦盐和散盐。据后来的文献的解释,苦盐即是出自于盐池的颗盐。未炼冶,其味咸苦。散盐即末盐,是煮水为之,出于东海的海盐。当时供王者膳食用饴盐,饴盐以饴拌成者,或云生于戎地,味甜而美也。款待宾客时用散盐和形盐,形盐即印盐,或以盐刻作成虎形,或积卤所结,其形似虎也。此外还有生于山崖的崖盐、产于土中的戎盐、生于井中的伞子盐、产于石岩中的石盐、生于树中的木盐、长于草中的蓬盐。可见周代已开发出多种盐,并进行适当的加工和利用。这些盐作为食用的盐,口味和质量尚缺乏研究,也难以研究。
春秋时,管仲在齐国拜相,开始设置盐官和收缴盐税,此后历代都对盐务设官课税。在社会生活中,盐的消耗量是很大的,生产和分配没有政府的管理是要出问题的,同时盐税又是国家财政的一笔大宗收入,故历代政府都十分重视盐务的管理。下面就几种盐的早期生产作一简介。
池盐池盐,即内陆湖盐,指盐湖中天然结晶或以盐湖表层卤水晒制的盐。中国的盐池主要分布在西部和北部干旱气候的地带,即西起新疆,向东经青海、藏北、陕西、甘肃、宁夏、内蒙古、山西直至吉林和黑龙江等的广大地区中。在中国历史上,最早也是最著名的池盐产地是解州盐池,即今日山西运城盐湖,所以也称之为解盐。
近几十年来,古人类学家们相继在山西襄汾发现了“丁村人”、在陕西发现了“蓝田人”、在西安市郊发现了“半坡人”等遗址,它们分属于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值得注意的是,在进入新石器时代后,自半坡氏族社会开始,中国最早的一批原始公社部落就纷纷以山西运城为中心,在黄河中游两岸聚居,甚至相互争战,从自然条件看,除因这一地区土地肥沃,气候温凉适宜,有众多水源和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外,运城解池盛产食盐也是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又据历史文献和考古发掘发现,今临汾市南郊有尧都古迹,今永济县薄州镇东南有舜都故址,今夏县禹王城是禹都遗址又同时为夏朝国都。此外,距夏县城北十二里的西阴村相传为西陵氏之女、黄帝之妻、我国养蚕织丝的发明者嫘祖的故乡,运城平原北侧的稷王山相传为后稷教民稼穑之地。其后几个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主要国都也都建在距运城盐湖不太远的西安、咸阳、洛阳、开封及许昌等地。显而易见,当时建都选址与解池的精盐不无关系。
运城盐湖的开发源远流长。《战国策》谓:“骥之齿至矣,服(驾)盐车而上太行……负辕而不能上。”就是描写驱赶良马驾着运盐的车攀登太行山时的劳累情景。所运的盐大概就是山西安邑、解州等处所产的池盐。《山海经》中则有“景山,南望盐贩之泽”之语,据晋代郭璞注:“即解县盐池也。”这是明确提到解州的。《周礼·天官·盐人》谓:“祭祀共其苦盐、散盐。”据唐人司马贞《史记索隐·货殖列传》考证:“盐,音古……杜子春以读苦为监,谓出盐直用不炼冶。一说,云监,河东大盐。”又《说文·盐部》云:“盐,河东盐池,袤五十一里,广七里,周百十六里。”所以古人特意造了个“盐”字来指称盐池和解州的池盐。表明春秋时期池盐已很受重视。
自原始社会后期到春秋时期,运城盐湖的生产方式大概还只是组织大批人力采捞由卤水中自然析出的食盐结晶,即那时的解州池盐还属于石盐。池盐开发的正式记载始见于《左传》,谓:成公六年“晋人谋去故绛(在今山西临汾南),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饶而近监,国利君乐,不可失也。’”可见当时河东大盐的开采获利丰厚。《水经注》(卷六)对这句话又做了考释,谓:“《汉书·地理志》曰:‘盐池在安邑西南。’今池水东西七十里,南北十七里,紫色澄淖,浑而不流,水出石盐,自然印成,朝取夕复,终无减损。唯水暴,雨澍甘潦奔迭,则盐池用耗。故公私共竭水径,防其淫滥,故谓之盐水,亦为竭水也。”故《山海经》谓之盐贩之泽也……《春秋》(指《春秋左氏传》,即《左传》)谓:“成公六年,晋谋去故绛,大夫曰:‘郇,瑕也,沃饶近盐。’服虔曰:‘土平有溉曰沃,盐,监也。’土人乡俗引水沃麻,分灌川野,畦水耗竭,土自成盐,即所谓咸鹾也。而味苦,号曰盐田,盐监之名,始资是矣。”按此论,春秋时解州盐民便已采用原始的天日晒盐法了。因为运城盐湖卤水属SO42-·C1——Na+·Mg2+型,氯化钠含量相对来说并不很高,经长期不间断地“集工采捞”后,卤水含盐量要显著下降,自然结晶的石盐必然越来越少。而随着中原人口的增长,盐的需要量却在不断增加。所以这种形势必然促使当地盐民(亭户)开始试用卤水晒盐。若此工艺肇兴于春秋时期,那么这在世界盐业史上要算走在前列了。当然,此后“集工采捞”的原始方式仍在持续着。
安邑、解州的池盐日晒法至盛唐时期趋于成熟,形成了“垦畦浇晒”的完整工艺。唐人张守节在其《史记正义》对此有翔实的记载:“河东盐池畦种,作畦若种韭一畦,天雨下池中,咸淡得均,既驮池中水上畦中,深一尺许,以日曝之,五六日则成盐,若白矾石,大小若双陆。及暮则呼为畦盐。”这种人工垦地建畦,将经天雨适当稀释的卤水引入畦内,再靠天日、风吹蒸发浓缩晒制食盐的方法,能够从SO42-·C1——Na+·Mg2+型的复杂体系中使食盐单独结晶析出。这样便使池盐的产量猛增,品质也得到改善。《新唐书·食货志》记载了当时解池的产盐量,谓:“蒲州安邑、解县有池五,总曰两池,岁岁得盐万斛(按唐代仍以十斗为一斛),以供京师。”
自唐以后,这种“垦畦浇晒”的方法得到大力推广,并应用于海盐的晒制。有关记载更是陆续不绝,如《图经本草》谓:“解人取盐,于池旁耕地,沃以池水,每临南风急,则宿昔成盐满畦,彼人谓之种盐。”书中并附有精美插图。
宋代解州盐池海盐关于煮海卤为盐的史料,今存最早的可算《管子·地数篇》,其中有管仲答桓公关于盐政之所问,谓:
齐有渠展之盐……君伐菹薪煮沸水为盐,正而积之三万钟,至阳春请籍于时……阳春农事方作……北海之众毋得聚庸而煮盐。然盐之贾(价)必四十倍,君以四十之贾,修河济之流,南输梁、赵、宋、卫、濮阳。
按古渠展是古水的入海处。沸水即古济水,据《汉书·地理志》及《水经》记载,济水自今荥阳县北分黄河东出,下游即今小清河,从羊角沟入渤海莱州湾,即相当于今山东永利、王官两盐场处。从上段引文可以了解到,春秋时齐国的海盐生产规模应该已经相当大,可供应北方梁、赵、宋、卫诸国,而且有必要适当控制,以防影响农耕劳力和盐价跌落。
中国先民煮海做盐的活动传说兴起于神农教民稼穑的时代,这是可信的。至于初期的加工过程是怎样的,现在已不可考了。鉴于海水中的食盐含量并不算很高,每千克海水中平均大约含食盐27克,而食盐的浓度要达到每千克海水含265克时(30℃)才会结晶出来,所以若直接煮海水提取食盐,燃料要消耗很大,效率相当低。估计中国沿海盐民很早时就已先加工海水为卤水(即适当浓缩海水),然后再煎煮为食盐,可能与后世宋人的举措相似,或是它的某种雏形。
(1)制卤
制卤基本上都是利用海滩沙土来吸附、富集海盐,然后利用潮汐淋洗或人工舀水浸卤来获得较浓的卤水。北宋苏颂《图经本草》的记载已相当详明,谓:“于海滨掘土为坑,上布竹木,覆以蓬茅,又积沙(按指已吸附大量海盐的海滩沙土)于其上。每潮汐冲沙,卤咸淋于坑中……因取海卤注于盘中煎之,顷刻而就。”。宋人乐史的《太平寰宇记》在介绍通州海门县(今江苏省长江口)海陵盐监时,对刮沙浸卤的方法有翔实记载,但不是利用潮水冲沙,而是靠人工提舀海水入坑渠浸渍盐沙。
(2)煎制
煎炼海卤的锅,汉代时叫做“牢盆”,因《史记·平准书》中有“因官器做煮盐,官与牢盆”的话,所以它是官方提供给盐户使用的,但其形制已不可考。《图经本草》说:“其煮盐之器,汉谓之牢盆,今或鼓铁为之;或编竹为之,上下周以蜃灰,广丈,深尺,平底,置于灶背,谓之盐盆。《南越志》所谓‘织篾为鼎,和以牡蛎’是也。”可知,当时的煎盐器是很大的,直径过丈,深有尺余,平底,其状若盘。一种是铁制的,当然比较耐用;一种是用竹篾编成的而外敷以牡蛎灰(主要成分为CaO),虽易烧坏,但就地取材,成本低廉。
《太平寰宇记》谓:一盘可得盐三至五石(宋制每石五十斤)。此外,南宋人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谓:淮浙之盐亭户以“镬子”煮盐。按镬为无足的釜,一镬可成盐三十斤。镬亦分铁制与竹编两种。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太平寰宇记》还叙及海陵盐户在起火煎卤以前已采用了“散皂角于盘内”的方法絮凝食盐散晶,以利于食盐结晶的析出和成长,谓:“[将卤水]载入灶屋……取采芦柴、茅屋之属,旋以石灰封盘,[倾入卤水,]散皂角于盘内。起火煮卤。一溜之卤分三盘至五盘,每盘成盐三石至五石,既成,人户疾着木履上盘,冒热收取,稍迟则不及收讫。”
井盐井盐,即所谓“凿井取卤,煎炼成盐”,是以凿井的方法开采地下天然卤水及固态的岩盐。巴蜀之地是我国井盐的发祥地,古代井盐的开采也集中在川、滇一带。而四川自贡则号称中国古代盐都,是我国井盐技术创造发明的中心。
中国井盐开采大约创始于战国晚期。据晋人常璩的《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周灭后,秦孝文王(当作秦昭襄王)以李冰为蜀守(约前256~前251)。冰能知天文地理……又识齐水脉,穿广都(今双流县境)盐井、诸彼地,蜀于是有养生之饶焉。”李冰是战国时期的著名水利专家,可能是他在带领巴蜀百姓开山移土,修筑都江堰工程时发现了成都平原的地下卤水。《华阳国志·蜀志》又谓:“南安县(今四川乐山市)……治清衣江会。县溉有名滩……二曰盐溉,李冰所平也。”明确指出了李冰曾平整过地下卤水流出所形成的盐滩。当时,秦据蜀地后,大量移民,带来了外地的各种先进技术,包括中原的凿水井技术。加之蜀地人口猛增,必然急需更多食盐供应,在这种形势下,李冰首创开凿盐井,既富国利民,又推动了凿岩穿井技术,他的这项伟绩可以说不逊于他在水利方面的贡献。
自秦初李冰开凿广都盐井直到赵宋初年,可以认为是我国盐井史发展的第一阶段,可称之为大口浅井时期。这个时期的凿井技术还比较原始,主要是靠人力,使用简单的锸、锄、凿等挖掘工具采进,通道至少得留有一人掘进、运土等劳作的空间,所以盐井的口径很大。历史上典型的大口井可列举出唐代时在今川中平原仁寿县开凿的“陵井”,纵广30丈,深80余丈,当时益州盐井最多,据说以此井为冠。
大约在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成都枥子山汉代砖室墓中发现了一块画像砖,其上清晰地描绘着一幅生动的井盐场生产全景图。图左方有一大口盐井,井架的顶上安置有滑车,架上有4个盐工两两相对,汉代盐井场画像砖上下汲卤,灌入旁边的卤池。卤水又通过“笕”(即输卤管道,《富顺县志》谓:“以大斑竹或南竹,通其节,公母榫接逗,外用油麻、油灰缠缚。”),被翻山越岭输送到图中右方的盐灶,灶房内有贮卤缸。卤水由卤缸挹入盐锅,盐工则以从山上背运而来的柴草熬盐。这个场面,表明汉代的井盐生产已经具有一定的机械化,生产规模也相当大了。当时汲卤的方法是利用井干上的辘轳式滑车提卤。若如画像砖所绘,绳的两端所系是吊桶,一上一下,可提高效率。而唐代的陵井,汲卤已用大皮囊,满载卤水的大皮囊十分沉重。所以“井侧设大车绞之”,当已有牛牵拉的绞车了。
岩盐岩盐又名石盐,是自然界中天然形成的食盐晶体,可以直接取来应用。这种盐的精上之晶呈玻璃光泽,无色透明或白色,晶形正立方体,往往“累累相缀,如棋之积”,所以又称“光明盐”、“水晶盐”、“玉华盐”和“白盐”。有的则因混入一些金属化合物的杂质或污泥,而带有某种特殊的色调。
这类石盐,有的生于盐池之下,《本草经集注》便提到:“河南盐池泥中,自然凝盐如石片,打破皆方,青黑色。”这是不纯净者。而更有上品者,如《唐·新修本草》(卷四)谓:“光明盐……生盐州五原(今陕西定边)。盐池下凿取之。大者如升,皆正方光澈。一名石盐。”《本草纲目》也提到:“石盐……水产者生池底,状如水晶、石英,出西域诸处。”有的石盐则生于地下,须掘土挖取。这种地方大多原是内陆干涸的湖床。
但最主要的石盐则是自盐井或盐湖中自然凝结析出的。《水经注》(卷三十三)曾提及:汤溪“水源出[朐忍]县(今四川云阳县西)北六百余里上庸界,南流历其县,翼带盐井一百所,巴川资以自给,粒大者方寸,中央隆起,形如张伞,故因名之曰伞子盐。有不成者,形亦必方,异于常盐矣”。这种盐形状怪异,颇有名声,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亦云:“巴东朐忍县北岸(崖)有盐井,盐水自凝生粥(伞)子盐,方一二寸,中央突张如伞形,亦有方如石膏、博棋者。”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之十)也提到:“朐忍县盐井,有盐方寸,中央隆起如张伞,名曰伞子盐。”矿物学家夏湘蓉对这种盐曾解释说:“在现在盐湖里,当平静的天气,水分急剧蒸发时,卤液表面常形成无数浮游的石盐‘结晶小艇’,这就是石盐的规则连生体——伞子盐。”这类石盐则广泛出现于我国西北的广大地区,因为那里的内陆湖星罗棋布,气候干热,盐湖表面经常厚厚地凝结着晶莹的石盐。由于这些地区在古代属于胡人居处的地带,所以那里所产的石盐统称为“戎盐”,也称“胡盐”、“羌盐”。早在秦汉之际,戎盐便从那里大量贩运到中原地区,成为我国食盐的主要来源之一。
除了以上四大类食盐资源外,过去民间还有刮盐碱土熬盐取食的,这就是土盐,古时称为末盐。
在今河南东部、河北南部、山东西北部以及苏北、陕西、晋北这一广大地区,土壤中含有较多盐分,俗名叫“盐碱土”,每至秋高气爽之季,地面上便泛起白霜一层,远望如积雪,取来用水淋洗,便得到卤水,可煎炼成盐。这些地区的土壤中为何富含盐分?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地区是“历代泛黄的灾难地区”,因此在很长的岁月里,不断向堤防两边漫溢或渗出的黄河水,经蒸发而遗留下了盐分;今鲁南、苏北沿海地区则大面积散布着因海水涨潮所泛起的沙土,或者过去那里就是海底,后来被冲积而形成了陆地;又有的地区,如河南东北部本系黄河故道,地势低下,河流极少,以致排水不良,所积之水惟靠天日蒸发才是它的宣泄途径,所以地中可溶性盐、碱、硝随积水而上升,达到地表。由于这些土地碱性太强,不堪农耕粮棉,所以这一带过去晒盐池“一望无际,乡民惟藉刮土淋盐以谋生活”。
刮土熬盐的记载最早见于《图经本草》,谓:
又有并州(治所在今山西太原市)两监末盐,乃刮咸煎炼,不甚佳……又通(治所在今江苏南通)、秦(治所在今江苏泰州)、海(治所在今江苏连云港)州并有亭户刮咸,煎盐输官,如并州末盐之类,以供给江湖,极为饶衍,其味乃优于并州末盐也。
上表中举出了河南开封、商丘地区土盐(指未经煎炼前的盐霜)的成分,以供参考。那些镁盐杂质的存在使这类盐味道多有苦涩,而且生产手续麻烦,费工多而效率低。过去这些地区交通闭塞,缺乏外来盐源,只得就地取之。而随着海盐;池盐的发展,行销各地,所以土盐生产后来已经基本上被淘汰了。
饴糖工艺
食糖在提高人类的营养和丰富人们的物质生活方面都扮演着一个很受欢迎的角色,所以从古至今它始终在农艺、食品加工和轻工业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中国古代的医药中食糖也一直受到重视,并广泛被利用。
中国古代的食糖中,主要的是饴糖和蔗糖。饴糖的主要成分是麦芽糖,它出现较早,是利用风干的麦芽和谷物来酿造的。因为麦芽中含有淀粉糖化酶,在它的作用下,谷物淀粉会部分水解而形成麦芽糖。它的制造工艺与酿酒相似,也可以说是人类利用生物化学过程的先声。蔗糖当然主要是从甘蔗榨取得到,它的结晶和脱色,都是物理化学过程,因此白砂糖的制作工艺也可从属于古代化学的一部分。现代蔗糖的主要原料中还有甜菜,但中国古代只把它作为蔬菜,加工甜菜糖的工艺是20世纪初才从国外引进的。
此外,中国古代的食糖中还应包括蜂蜜。蜂蜜中含有大量转化酶,因为蜜蜂体内含有转化酶,可以水解蔗糖转化为等量的葡萄糖和果糖的混合物。不过那是从自然界采集来的,养蜂业的兴起似乎也是较晚的事,其工艺中也谈不到什么化学过程,因此难以纳入古代化学工艺的范畴。
中国先民尝到香甜的麦芽糖大概很早,而且也绝非是某人一时的发明,而是与酒的发明相似,初时是一种自然发生的事。我们可以设想,在原始社会中,当人们步入农耕为主的时代以后,收获的谷物越来越多,当时又没有较好的储藏设备和处所,被雨淋受潮的机会是很多的,于是谷物就会发芽。在谷物生长的过程中,便自发地产生出糖化酵素而使谷物中的淀粉水解生成麦芽糖以作为谷芽生长和生根的营养。当时的人们如果不舍得丢弃这种发芽的谷物,仍然取来加工、炊煮食用,就会发现它们变得香甜,更加可口,这就是说,尝到了麦芽糖的味道。于是人们便会逐步总结经验,慢慢优选出了谷芽(药),风干后磨碎制成“曲”,像酒曲那样,用它来糖化各种蒸煮熟的稻米、大小麦、黄米、高粱、糯米等,再经过滤、煎熬就会得到含有丰富麦芽糖的糖食了。这种糖食最初叫做“饧”或“饴”。这个饧字初时读如“唐”,汉寸则读如“洋”,其后又改饧声从唐,写为醣,或从米为糖,即成为现在的“糖”字了。山从有关的各种文字,可以推断知,约在公元前1000年,即周代甚至殷代时大概就已经出现了制饧的加工制作工艺了,例如战国时成书的《书经·尚书》中的“洪范章”里就已有“稼穑作甘”的话,意思就是耕作收获的谷物可制作出味甜的饧。
中国古代与“饧”含义相近或与之相关的字,出现过很多,常见的除“饴”外,还“馓”等。关于“饴”,例如《诗经·大雅》的“绵篇”谈到古公直父从迁岐开创基业时,便歌颂道:“周原月无月无,堇茶如饴。”儒家礼教经典《礼记·内则》谓:“妇事舅姑,如事父母……枣、栗、饴、蜜以甘之。”再如《山海经·南山经》有“又东三百七十里曰仓者之山……有木焉,其状如谷而赤理,其汁如漆,其味如饴,其名曰白(音皋)”的话。《淮南子·说林训》中有“柳下惠见饴曰:‘可以养老。’盗跖见饴曰:‘可以粘牡。’见物同而用之异”的话。对于“饴”,《说文》谓:“饴,米糵煎也。”汉代杨雄撰《方言》又说:“凡饴谓之饧,自关而东,陈、楚、宋、卫之通语也。”是知先秦时人们就熟悉饴饧了。最早见于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里辑录的楚国辞赋家宋玉的“招魂篇”(一说为屈原之作),其中有“敉蜜饵,有些”的词句,《方言》(卷十三)曰:“饧谓之;饧,谓之。”晋代郭璞注:“即干饴也。”关于“馓”,西汉史游《急就篇》提到“枣、杏、瓜、棣、馓、饴、饧”。《说文》曰:“馓,熬稻也。”唐人颜师古注:“馓之言馓也,熬稻米饭使发散也。古谓之张皇,亦目其开张而大也。”即也是一种麦芽糖甜食。汉代刘熙的《释名疏证·饮食·》则谓:“哺也,如饧而浊,可哺也。”所以它那时已经是《齐民要术》中所描述的那种颜色发黑、含有少许糟饭渣的。
但是若细究起来,饴与饧的含义似乎又稍有区别。东汉郭璞注释《方言》进谓:“饧,即干饴也。”《急就篇》颜师古注曰:“厚强者曰饧。”可见,饧当是熬煎糖化液汁时火候较充分,冷凝后成为凝重甚至固化了的麦芽糖,若经进一步挽打成白色后就成为今人非常熟悉的关东糖了。因此,《齐民要术》(卷六)在“养牛马驴骡篇”中的“治马中谷又方”里有“取饧如鸡子大,打碎”的话,表明饧是坚硬的糖块,所以这种干饴也叫“脆饧”。而饴则是煎熬时间较短,浓缩程度较差,因而尚保留较多的水分,是比较柔薄如糖稀的麦芽糖,《释名·释饮食》中解释“饧”、“饴”这两个字时,也讲得相当清楚,它说:“饧,洋也,煮来消烂,洋洋然也;饴,小弱于饧,形怡怡然也。”所以陶弘景说:“方家用饴糖,乃云胶饴,皆是湿糖如厚蜜者。”
总之,到了汉代,人们食用麦芽糖制品已经很普遍了。郑玄在注释《诗经·周颂·有瞽》里“箫管备举”和《周礼·春官》里“小师掌教鼓、箫、管、弦、歌”两句中的“箫”字时都说:“编小竹管,如今卖饧者所吹者。”可见东汉时已有沿街吹箫叫卖麦芽糖的小贩,表明饴已经成为平民的小食品了。
现存关于饴饧制作工艺的文字记载则出现较晚。最早提到饴饧制作之事的大概是东汉时期崔定所撰的《四民月令》,但讲得很简单:“十月先冰冻,作凉饧,煮暴饴。”农学史家缪启愉解释说:“崔宜所谓‘凉饧’犹言‘冻饴’,是一种较强厚的饧;‘暴’是‘猝’、‘速,的意思,意即速成;又‘暴’是暴露,引申为稀薄(见《尔雅·释诂》),所谓‘暴饴’即煎熬的时间较短、浓缩度较弱的、速煎成的‘薄饴’。”但《四民月令》未谈及饴饧的制作工艺。至于制饧为何安排在农历十月,李治寰曾作过很好的解释,他指出,这是家庭自用饴饧的加工月份,原因主要有:新谷比隔年陈谷出糖率高,故用十月份新收打的谷物;孟冬和春节是农民的传统节日,祀神祭祖都要用饧;夏秋日天气,熬出的饧放久易酸易烊,所以要冰冻后开始熬糖。至于商业性熬饧,随产随销,那就不拘时间了。
最早记载熬饧工艺的大概要算东晋(大约)人谢讽所撰的《食经》了。其“作饴法”是:“取黍米(按即黄米)一石,炊作黍(按,这里是饭的代称),著盆中。糵末一斗搅和。一宿,则得一斛五斗。煎成饴。”根据这段文字,用糵和黍米的比例是1:10.
皮革工艺
皮革工艺是人类最古老的技艺之一。从科学上说,这是一个复杂的物理—化学加工过程,机理较深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即只有加工经验的积累,而没有系统的机理可讲。这就造成在中国的古代文献中,有关制革工艺的记载极少的状况。
从当代科学的知识库里,人们才知道,制革就其本质来说应是蛋白质的取舍及变性过程,属于高分子的加工技术。原料皮即生皮的组织结构可以分为三层:表皮、真皮和结缔组织。它们的化学成分主要是蛋白质和脂肪。在加工中,表皮很薄,不能成革,故要将其除去。结缔组织是动物皮与身体之间的一种疏松组织,包括人们熟悉的皮下脂肪等。这部分对于皮革也是有害无用的,在加工中也应除去。皮革的基本组成部分是真皮,鞣制加工的主要对象就是该真皮层。真皮又可以分为两层。上层是皮革的表面层,呈粒状的结构,它是衡量皮革质量的重要指标。下层是网状的纤维层,革制品的物理强度主要取决于它。此外,在真皮纤维结构的空隙里,有一些胶状的蛋白质即纤维间质,这也需要在加工中予以去除。
真皮经加工后保留下来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质纤维,它包括胶原纤维、弹性纤维、网状纤维。这些蛋白质纤维中的98%是由胶原组成,因此从化学意义上讲,皮革是胶原的加工产物。通过X射线观察,可以看到上述蛋白质纤维的结构就像海绵一样,可以汲入大量的鞣剂、染料及助剂,这就是皮革可以鞣制的基础。鞣制的实质是利用鞣剂对上述蛋白质纤维进行化学和物理的加工,是鞣质与蛋白质分子上的活性基团(主要是氨基)进行交联反应的过程。那些对皮革性能有不良影响的球状蛋白质,在酸、碱、酶的作用下,会被水解而除去。在合理的鞣制中,蛋白质纤维得到变性的加工,从而使皮革具有较好的物理性能,主要表现在不易腐坏、柔软、坚实。
毛皮是附有动物毛的兽皮,古时沿称“裘”。将动物毛除去之后制成的兽皮,习称为“熟革”。它们的加工方法有所不同,而原理则是一样的。
传统的皮革工艺当人类还处于茹毛饮血、以采集渔猎为主的原始社会时,就已发现兽皮可以用来御寒护体。于是人们开始利用刮削石器或尖状石器剥刮动物外皮,再缝制成衣饰或用具。虽然刚屠宰剥下来的湿皮很软,但将生皮晒干,会变得十分僵硬,不仅穿起来如盔似甲,很难受,同时加工缝制也很不方便。为了克服上述两难的状况,在实践中人们逐渐摸索到,可以利用野兽的脑浆、骨髓、油脂等涂抹在生皮的表面,通过太阳光的照射,然后用手搓,兽皮就会变得较为柔软,而且不易腐烂。这方法实际上是由于油脂等被空气氧化后产生醛,它作为鞣剂而加工了皮革,这是最原始的皮革加工技术。
在实践中,人们可能从熏肉不易腐败的经验中发现,可以采用烟熏的方法来加工生皮。经烟熏加工的兽皮既可以防腐,又能防虫。这种方法后来演进为古老的烟熏鞣法。当然,古代人是不知烟中含有醛的,这种方法实质上是醛鞣法。后来人们又发现搭在某些树枝或木头上的湿生皮,经过一段时间,会使生皮染上某些颜色。从中受到启发,推测这些树木可能含有能与生皮发生作用的汁液。于是人们用热水泡浸某些树皮或树枝,再将生皮浸泡在这种汁液中,浸泡后再晾干,生皮既不收缩,也不腐烂,还较柔软、坚韧。这就是植物鞣法的开端。当然,当时的人们还不知道这种方法是利用了某些植物内所含的单宁做鞣剂。
制裘,需要保存皮上的毛绒。在古代这并不容易。人们发现将毛皮放在温暖而又潮湿的地方,几天后,毛会自动脱落。由此人们掌握了发汗脱毛法。裘有它的用处,脱了毛的革也有自己独特的用途,甚至有更广泛的用途。所以在古代,裘和革长期共存。制革要脱毛,人们又发现用石灰碱液来浸泡生皮,脱毛的效果较发汗脱毛要好得多。在古代长期沿用的脱毛法就是这两种,它的机理就是利用了微生物酶的作用。
在实践摸索中,人们又发现,禽畜的粪便,例如鸽粪、鸡粪、狗粪等,经温水发酵后,其发酵液用来浸泡生皮也能使皮革变得柔软。这一技术曾被视为制造软革的关键技术。但是这种方法若掌握不当,会损坏生皮。因此,掌握这项技术必须要有经验,古代曾视为秘密,只能是师徒传授。在制革中,人们更多采用的方法是先用石灰水浸泡生皮以脱毛,然后再用芒硝或明矾、食盐及酸奶来鞣革。
在古代的漫长岁月中,皮革工艺的进步是很缓慢的,它长期停留在以经验为基础的家庭手工作坊的生产形态。直到18世纪末以前,没有人对皮革的加工方法进行过科学的研究,而是世代相传地使用油脂、烟熏、树皮、明矾、芒硝等制革方法。《天工开物·乃服》中有关皮革工艺只写道:“其老大羊皮,硝熟为裘”,“若南方短毛革,硝其鞟如纸薄,止供画灯之用而已”,“麂皮去毛,硝熟为袄、裤,御风便体,袜靴更佳”。
有关这些工艺的细节,古代文献也没有详细的记载,这可能是:第一,这种工艺太古老了,而被人漠视。第二,在封建社会中长期存在着鄙视体力劳动,轻视技艺的观念,而制革工艺则是传统工艺中最脏、最累的一项。第三,更重要的是,当麻、丝、棉纺织品问世后,原料有限、制作工艺复杂、难度较大、成品率低下的皮革制品只能在服装业中占据一个很次要的地位。少数裘类成品大多作装饰品而为权贵们所占有。一般革制品曾用于军事,例如甲胄。孔颖达在注疏《尚书·费誓》中说:“古之作甲用皮,秦汉以来用铁,铠、鍪二两皆从金,盖用铁为之。”可见秦汉以后,连甲胄之类的军事装备也由金属材料制作。
皮革的产量相对于麻、棉、丝织品来说,实在是少得可怜。皮革工艺没有详细记载,可能还有一些原因,值得深入探讨。
古代的皮革业在北京房山周口店北京人的文化遗址中,曾发现有刮削石器和尖状石器,表明当时的原始人已用这些石器来剥取兽皮了。在周口唐的山顶洞穴中还发现有磨制而成的骨针,这很可能是用来缝制兽皮的。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仰韶文化的许多遗址中都发现有更多的骨针,推测当时加工缝制兽皮已是常事。据分析,制革成为专业工种大概始于商代。在河南安阳出土的殷商时代的戍革鼎上,就刻有“革”字。其字形很像一个披着盔甲的武士,表示当时常用兽皮防御护身。甲骨文、金文中均有“裘”字,表示用兽皮做的衣服。《尚书·费誓》正义引《世本》的话,认为皮甲始于夏代第六世帝杼(少康之子)。
在河南安阳侯家庄的一座殷商时代的墓葬中,曾发现皮甲的两处残迹,残迹是皮革腐烂后留在土里的纹理。在长沙也曾发现春秋晚期的皮甲。在湖北江陵也发现过战国时代的皮甲。按理,皮甲在土中是很难长期保存的,能出土皮甲说明这些皮革制品在防腐处理上是很成功的。
《诗经·召南·羔羊》曰:“羔羊之皮,素丝五纶。退食自公,委蛇委蛇。羔羊之革,素丝五缄。委蛇委蛇,自公退食。羔羊之缝,素丝五总。委蛇委蛇,退食自公。”这里描写的是穿着做工考究的羔羊之裘的大夫饱餐以后,悠闲归来的情景。
周代设有金、玉、皮、工、石等五种官吏来管理王室中相关物资的生产和分配使用。《周礼·考工记》称制革工匠为“鲍人”,说:“鲍人之事……革欲其茶白,而疾浣之,则坚。欲其柔滑,而腥脂之,则需(柔需也)……卷而搏之而不迤,则厚薄序也(均也)。胝其著而浅,则革信也(无缩缓也),察其线而藏,则虽敞不瓿(磨而不磷)。”《周礼·天官·掌皮》也记载:“掌秋敛皮,冬敛革。”这里讲的是制革工匠的工作,但不是很细致清楚。《礼记·月令》还记载,季春之三月命工师、命百工审查五库器材的质量,五库里就有皮、革、筋等物。《楚辞·国殇》中有“操吴科兮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之句,形象地描绘了当时战士披甲操戈的战斗情景。可见当时皮甲已被大量用做防御的装备。《战国策·秦策一》中说:“兵革大强,诸侯畏惧。”说明革制甲胄的数量也反映了军事的实力。
《韩非子·五蠹》中说:“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又说:“孙叔敖相楚,栈车牝马(柴车也),粝饭菜羹,枯鱼之膳,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饥色,则良大夫也,其俭倡下。”《韩非子》中这两段话表明,皮革在当时已较普遍。
战国皮手套
漆髹工艺
天然漆又名“大漆”,是漆树皮里的黏汁。其主要成分为漆酚和漆酶。在一定的温度和湿度条件下,漆酶能催化漆酚的氧化作用而生成半醌,再经过半醌的催聚,使漆酚多聚成链,又经过过氧交联使链交织成片状漆膜。所以,用漆涂饰木器、车辆、房屋等,干燥后就覆盖着一层坚牢、光亮的薄膜,不仅保护了材料,而且明亮美观,具有一定的耐热、耐酸、耐碱的能力。
漆树是高大的阔叶落叶乔木,生长在气温较高、雨量丰富的暖湿地区。古代中国的中原地区由于当时气候温暖,因而有丰富的漆树资源。《诗经·秦风》有“阪有漆,有栗”,《诗经·庸风》中有“树之榛栗,椅桐梓漆”,《诗经·唐风》中有“山有枢、栲、漆,隰有榆、扭、栗”等记述。《山海经》也多处记载了许多地区的漆树分布。漆树自然分泌树汁,在其干燥固化后形成坚硬、光亮的涂层。这一自然现象为中国的先民所发现,他们开始使用这种天然涂料对木器、陶器进行保护或装饰。
1978年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曾发掘到一件器壁外有朱红色涂料,微有光泽的木碗。对此涂料,经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专家鉴定,确认为中国生漆。1960年在江苏吴江梅堰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也发现两件漆绘陶罐,所绘的原料经鉴定亦为生漆。1977年在辽宁新石器时代的墓葬中也发现了漆器。总之,在史前的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已开始采集和利用生漆了。
古人的早期生活用具中,木器占了相当数量,为了保护木器,最好的方法是涂上一层漆,因此漆器有了很快的发展。商代的贵族拥有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遗址出土的漆木碗大量的漆器已不是稀罕事。1972年在河北藁城台西村的商代遗址中,发现了漆器。尽管胎已腐朽,而漆壳尚可辨识。出土的漆器有好多种,都是朱地黑漆,图画很好,足以证明商代漆器的工艺水平已相当高了。1950年在河南安阳武官村的商代贵族墓葬中,也曾发现雕花的朱漆木器。西周时期的漆器数量明显增多。1958年湖北蕲春毛家嘴西周早期遗址出土的一件漆杯,是在黑色和棕色的漆底上,绘上美观的各式红色花纹,装饰之好,令人惊叹。它是目前发现的较早的成型漆器。河南浚县的周墓中就出土了涂漆的车马具、弓矢、兵甲等。
春秋战国是古代漆器取得巨大成就的时期。出土的该时期的漆器不仅数量多、分布地域广,而且进入了饮食器、日用器具、家具、乐器、兵器、交通工具等领域,并形成了中原、楚国、巴蜀三大漆器产地。漆器也由商周的朱红色;黑色,演进到战国的红、黄、绿、蓝、白、金等多种色彩。色漆的调剂使用是生漆工艺的一大进步。明代黄成的《髹饰录》在谈及各种色漆时说:“油饰,即桐油调色也。各色鲜明,复髹饰中之一奇也,然不宜黑。”杨明注曰:“此色漆则殊鲜妍。然黑唯宜漆色,而白唯非油则无应矣。”说明调制色漆时必须加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战国时黑漆朱绘卧鹿油。出土的战国时期楚国的大量漆器,其花纹清晰,漆层厚度有明显差别,可以推测当时这些色漆是用生漆加桐油及颜料调制而成的,表明当时已掌握了油与漆并用的工艺。
桐油是从桐树种子中榨出来的干性植物油,它的主要成分是桐油酸(C17H29COH)。桐油也具有成膜的性能,在战国时期人们已用桐油与各种颜料配成油彩来绘饰各种花纹图案。油彩的亮度比漆高,但抗老化性不及漆。漆的产量比桐油小,成本比桐油高。桐油和漆合用,正可取长补短,改善性能,降低成本。在化学技术史上,这也是一个具有民族特色的创举。
生漆作为涂料不仅具有涂饰的保护作用,而且还有较强的黏合能力,先民很早就利用这一特性,将金银珠玉镶嵌在漆器上。镶嵌工艺约萌芽在商代,到战国时期则发展到使金属构件与漆器黏结为一体。有了金属扣器,漆器的使用更加方便和坚固耐用了。
春秋时期人们已很重视漆树、桐树的栽培。战国时期则设有官营的漆林,由专设的官员管理。《史记·老庄列传》中说:“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尝为漆园吏。”秦汉时期,油漆技术和漆树、桐树的栽培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出土的漆器遍及全国,有勺、盘、案、奁、盒、耳环、枕、棺椁等,内胎除木之外还有麻,麻胎的称“夹”。此外,漆器上还饰以奢侈的金、银扣器。汉代桓宽《盐铁论·散不足》篇在谈到各种漆器时指出,“富者银口黄耳,金罍玉钟;中者舒玉器,金错蜀环”。“夫二文(纹)杯得铜杯十”。这是说当时一件纹饰漆杯等于十件铜杯,当然有金银做扣器的更为贵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