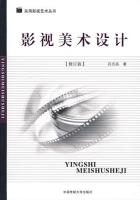中国饮茶史上向来就有“茶兴于唐而盛于宋”的说法,宋朝茶事,总体上离不开品和斗,这种社会风气,深刻地影响着人们,以至他们在茶文化的整个过程中,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挖空心思闯出新路。北宋蔡绦在《铁围山丛谈》中就很客观地谈到:“茶之尚,盖自唐人始,至本朝为盛。而本朝又至陵(即宋徽宗)时益穷极新出,而无以加矣。”宋徽宗自己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说,当时“采择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胜,亨点之妙,莫不盛造其极。”以至宋朝的茶学专著虽多,却都没能走出这个怪圈,一律在钻牛角尖,对茶质、茶艺、茶具的过分讲究,形成了宋代的茶风,如果崇尚质朴自然的茶神陆羽泉下有知,不被气歪鼻子才怪呢!
我们先来看看宋代流传下来的茶学专著,有专谈斗茶技术要领的,如蔡襄的《茶录》,宋徽宗的《大观茶论》;有品第茶品高下的,如黄儒的《品茶要录》;有专门记载皇家茶园茶叶制法及品名的,如赵汝的《北苑别录》、熊蕃的《宣和北苑贡茶录》;有专论福建建安名茶的,如宋子安的《东溪试茶录》。真是详之又详,蔚为大观。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茶饼制作愈趋小巧、精致,象“白芽”、“龙团胜雪”、“小龙团”、“密云龙”等茶,光听茶名就可知其珍贵价值了,大文豪苏轼由是感叹:“君不见斗茶公子不忍斗小团,上有双衔绶带双飞鸾。”
茶如是,茶具也自不能免。同唐朝的质朴相反,宋朝茶具走向了一个极端,变得非常讲究。人们不但在乎茶具的功用、外观和造型,而且更看重其质地,由前朝的陶或瓷,发展为玉、金或银,并相沿成风,日趋奢侈。周密在《癸辛杂识》中记载:“长沙茶具,精妙甲天下,每副用白金三百星,或五百星,凡茶之具悉备,外则以大缕银合贮之。越南仲丞相帅潭日,尝以黄金千两为之,以进上方。”一副茶具竟然要值一千两黄金,固然说明了茶具在宋人心目中的份量,但这种奢侈腐化,也反映了宋人失衡的心态,泱泱大国屡被小国欺压而至国威扫地的遭遇当然是切肤之痛,但不在政治上发奋图强,却深陷于市井文化的沼泽之中,这是不是宋人的悲哀?让人更难理解的是,周在《清波杂志》里告诉我们,造这种茶具,“工值之厚,等于所用白金之数”,“士大夫家有之,置几案间”,“但知以侈靡相夸,初不常用也”。这种金碧辉煌的茶具,成了士大夫案头的装饰品,纯粹是为了夸豪斗富的摆设,这又是茶具本身的悲哀!
当然,绝大多数人对茶具还是珍爱有加的,北宋失意文人唐庚就曾写了一篇名叫《失茶具说》的文章,借茶具遭窃之事,对世事大发议论,并从中描述了自己的特殊情感。文章是这样写的:
“吾家失茶具,戒妇勿求。妇曰:‘何也?’吾应之曰:‘彼窃者必其所好也。心之所好则思得之,惧吾靳之不予也,而窃之,则斯人也得其所好矣。得其所好则宝之,惧其泄而密之,惧其坏而安置之,则是物也得其所托矣。人得其所好,物得其所托,复何求哉?’妇曰:‘嘻!乌得不贫?’”
我们无从知道唐庚的茶具是金抑或是银制,但唐庚酷爱饮,却不是道听途说的,他常与友人聚会欢饮,并曾写过一篇短文《斗茶记》来记录此事。他的茶具被人偷走却告诫妻子不要查找,并说了一番富含哲理的话,茶具虽然被人偷走,但行窃者一定是爱它之人,他一定会悉心保藏,再也不至于遗失,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得遂愿,物得其所,还有什么可遗憾的呢?这种达观的态度,既反映了唐庚的思想境界,也体现了茶具在他心目中真正的价值,这种豁达,是任何有形有价茶具都无法比拟的。
仿佛为了印证宋人的奢华成风,有关茶学著作对茶具的质地不约而同地作了苛刻的要求,我们试从蔡襄的《茶录》和徽宗赵佶的《大观茶论》里撷取几个片断便知端的。
(1)《茶录》:
砧椎砧椎盖以砧茶。砧以木为之,椎或金或铁,取于便用。
茶钤茶钤屈金铁为之,用以炙茶。
茶碾茶碾以银或铁为之,黄金性柔,铜及喻石皆能生钅生,不入用。
茶匙茶匙要重,击拂有力。黄金为上,人间以银铁为之。
汤瓶瓶要小者,易候汤。又点茶注汤有准,黄金为上,人间以银铁或瓷石为之。
(2)《大观茶论》
罗碾碾以银为上,熟铁次之。
瓶瓶宜金银。
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蔡、赵两位对茶具的要求是惊人的相似,炙茶、碾茶、点茶和贮水用具一律是金碧辉煌或银光闪闪,饮茶用的茶盏也一致要求用名贵的建盏,可以说,宋代茶事的奢靡之风,与他们二位的推波助澜是分不开的。联系到宋人当时侈糜相夸、斗豪斗富的风气,这种要求未必全是从茶艺的需要出发的。
当然,崇金尚银似乎不能全怪宋人,他们的前辈唐人苏曾经洋洋自得地写了一篇名为《十六汤品》的文章,内中根据汤器质地的不同,划分了五种汤品,即:
“富贵汤以金银为汤器,惟富贵者具焉。所以茶功建汤业,贫贱者有不能遂也。汤器之不可舍金银,犹琴之不可舍桐,墨之不可舍胶。”
秀碧汤石凝结天地秀气而赋形者也。琢以为器,秀犹在焉,其汤不良,未之有也。
压一汤贵欠金银,贱恶铜铁,则瓷瓶有足取焉。幽士隐夫,品色犹宜,岂不为瓶中之压一乎?然勿与夸珍衔豪臭公子道。
缠口汤猥人俗辈炼水之器,岂暇深择?铜、铁、铅、锡,取熟而已,夫是汤也,腥苦且涩,饮之逾时,恶气缠口而不得去。
减价汤无油之瓦,渗水而有土气,虽御胯宸缄,且将败德消声。谚日:茶瓶又瓦,如乘折脚骏登高。好事者幸志之。
五种汤品,仅观其名就可优劣自判,喜欢“斗”的宋人自不会选择用无釉之瓦盛放的“减价汤”了,自然会直奔金银玉器名之的“富贵汤”与“秀碧汤”了,于是,崇金尚银就变得再自然不过的了。
在宋朝的大量诗文中,也有相关茶具的记载,范仲淹的“黄金碾畔绿尘飞,碧玉瓯中翠涛起”,释惠洪“金鼎浪翻螃蟹眼,玉瓯纹刷鹧鸪斑”,都无一例外地说明了金银茶具在宋代的普及和炙手可热。近年在福建福州出土的许峻墓中的一批茶具,为我们印证这一点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
许峻(1223~1272),字景大,是南宋福建建唐(今福清长乐)人。出身子名门望族,自己也官至架阁朝清通判。在他的墓里,发现了一批精巧别致的茶具,计有鎏金银碗托、盏、执壶、茶罐、银钵、银壶、铜筷、铜夹等点茶饮茶用具。这些金银茶具,是宋朝侈糜豪华茶道的一个缩影。
富足的生活,畸形的文化,腐败的政治,颓废的国威,是造成宋人追求富丽豪华的茶道的主要原因。其实宋人自己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晁冲之曾赋诗作文:“争新斗试夸击拂,风俗移人可深痛”,对斗茶现象口诛笔伐,但到后来,他自己也欲罢不能而深陷于其中,以至又“老夫病渴手自煎,嗜好悠悠亦从众”。这说明对一种社会现象,仅凭个人的微薄之力是无法改变的,灰心之余也只好随波逐流了。
在极力追求茶具的精巧豪华之余,宋人针对点茶、分茶当道的客观现实,对前朝茶器也作了一番改进,首先就是创制了茶筅,也就是竹帚。据《大观茶论》载:
“茶筅以竹老者为之,身欲厚重。筅歌疏劲,本欲壮而未必,当如剑瘠之状。盖身厚重,则操之有力而易于运用,筅疏劲如剑瘠,则击拂虽过而浮沫不生。”
这种用老竹制成的竹帚,用于煎茶后分茶前来搅动茶汤,只有厚重才能有力地搅动茶汤,使汤花密布,分茶后汤花不易消散。这种源于斗茶,但却毫不起眼的小竹帚,很快传入日本,融进了日本茶道之中,并保留至今。
在煮水器方面,唐代风行一时的也基本绝迹,而代之以更为小巧精致的铫、瓶之类。陶彀《清异录》说:“当以银铫煮之佳甚,铜铫煮之,锡壶注茶次之。”铫即吊子,是一种有柄有嘴的烹煮器皿。对茶瓶的要求也一样,蔡襄说:“瓶,要小者,易候汤;又点茶、注汤有准。”宋徽宗在《大观茶论》里说得更为详细具体:
“瓶宜金银,大小之制惟所裁给,注汤害利,独瓶之口嘴而已。嘴之口,差大而宛直,则注汤力紧而不散。嘴之末,欲圆小而峻削,则用汤有节,而不滴沥。盖汤力紧则发速有节,不滴沥则茶面不破。”
很显然,不用而改为有柄有嘴的茶铫茶瓶,其目的还是为了适应斗茶的需要,所以,宋代的茶瓶一般都是鼓腹细颈,单柄长嘴,这一点在出土文物中已得到验证。用这种茶瓶注水,容易控制自如,因此,更利于斗茶者技艺的发挥。
综上所述,宋朝茶具的损益,是以斗茶为中心的,这与前朝有相似之处,但更存在本质的差别,从艺术品饮的角度看,宋比唐要更为发达,其普及性与专业化程度要高一些,但也正因为如此,宋人失却了一份恬静的心态和清雅的情趣,更多的却是流于世俗。在这种市井文化的深刻影响之下,集实用性与观赏性于一身的茶具,逐渐失去了它原有的功能,沦落为权贵们夸豪斗富的替代品。宋人失衡的心态,使他们不可避免地步入了误区,这的确给茶具艺术的健康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虽然,宋代茶具并非乏善可陈,以品饮艺术推动茶具的生产和发展,其结果也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珍贵的实物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