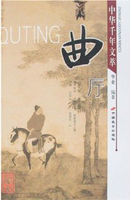一、由“清”到“韵”
魏晋至隋唐诗论主张辨析“清浊”,多崇尚“清音”、“丽句”。王昌龄更将“清浊规矩”看做诗歌创作关键。唐代处士潘阆的《自序吟》诗云:“发任茎茎白,诗须字字清。”随着格律诗的成熟,在诗法盛行的唐代,作为古体五言诗代表的《古诗十九首》在声律上遭到批评,《文笔式》、《文镜秘府论》等唐代著作均有涉及,主要提及《古诗十九首》的五种文病:平头、上尾、鹤膝、蜂腰和大韵,如《文笔式》中曰:“上尾诗者,五言诗中,第五字不得与第十字同声,名为上尾。诗曰:‘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如此之类,是其病也。”
宋代谈“韵”,首先还是浅层面的理解,即指诗歌表层之声律、病犯与语词。宋代曾慥承接唐人讲“韵”,在《百家类说》的诗苑类格中讲八病,乃以沈约的“八病”苛求古诗:“梁沈约曰:诗病有八。一曰平头,第一字、第二字不得与第六第七字同声,如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今欢皆平声也。第二曰上尾,谓第五字不得与第十字同声,如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草柳皆上声也。……四曰鹤膝,谓第五字不得与第十五字同声,如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来思皆平声也。”
宋代诗论对诗法的探讨中,对《古诗十九首》的用韵、用典、炼字和锻句特点也有总结,如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话》转述建安严有翼的《艺苑雌黄》曰:“古人用韵,如文选古诗杜子美韩退之,重复押韵者,甚多。文选古诗押二‘促’字。”“案《文选》载《古诗》曰:‘晨风怀苦心,蟋蟀伤局促’,又曰:‘音响一何悲,弦悲知柱促’,一篇押二促字也。”
严羽在《沧浪诗话·诗体》的古今用韵举例中,也提到了《古诗十九首》:“有协韵(楚词及选诗多用协韵),有古韵(选诗盖多如此)。”但严羽对诗法的探究更具系统性、理论性,已将其纳入诗学思想的总体框架中,因而显出其独特的价值,其《沧浪诗话·诗法》谈及“学诗先除五俗:一曰俗体,二曰俗意,三曰俗句,四曰俗字,五曰俗韵”,“韵”乃指称诗歌的声律音韵。
当然,作为古诗,其体式特征不同于律诗。唐宋诗论多以律诗之声律规范与要求去剪裁古诗,当然不得要领。但声律作为古诗之体式特征最基本的要素,在明清格调派诗论家们的诗论批评中得以集中认识与反思,认为“古诗只是合古体”。声律学更成为清代诗学一门专门的学问,以探讨古诗声调学说为其核心,首先还是考调审音,从音节神气上区分古律之不同。历代对于《古诗十九首》语言声色之“清”美的赞扬,正如钟嵘所说“清音独远”,绵延不绝。
蒋寅先生认为:“对清的阐释肇始于宋代,当时它受到了‘韵’的有力挑战。经过宋诗对诗歌美学理想的改造,‘韵’的范畴登上了古典诗歌理想的最高位置,而“清”由此后退一步,作为一种风格类型而存在。”诚然,宋代美学的新崇尚之一,就是“韵”风行于文化和诗歌审美领域。但“清”与“韵”是不同属类的概念,不存在孰高孰低。宋代“清”与“韵”并重,而唐宋诗论喜将“气清韵古”或“音清韵古”作为评价诗歌的标准,唐代宋之问的《太平公主山池赋》中就有“藏清兮蓄韵”这样的语句。苏轼、白石与诚斋以“清”泛论诗与诗人,以“清诗”泛指好诗。据《四库全书》资料,“清韵”一词在唐宋诗词中使用频率较高,如唐代韦庄的《李氏小池亭》诗云“家藏何所宝,清韵满琅函”,宋代程公许的《沧洲尘缶编》卷十一有诗曰“铜彛深养玉肤肌,更着图书绕四围。千古离骚谁与续,袭人清韵自芳菲”。“清韵”一词,多喻指铿锵优美的诗文。
宋代范温的《潜溪诗眼》历史地描述了“韵”的演变过程:“自三代秦汉,非声不言韵;舍声言韵,自晋人始;唐人言韵者,亦不多见,惟论书画者颇及之。至近代先达,始推尊之以为极致。”何为“韵”?《说文解字》曰:“韵,和也。”《玉篇校释》也解释为“声音和曰韵”,“和”、“韵”互文。刘勰的《文心雕龙·声律》篇曰:“异音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韵。”唐代李善注的《文选·卢谌〈赠刘琨〉》说:“韵,谓德音之和也。”由“音和”到“德和”,是儒家诗教思想的产物。相应地,“韵”由最初的声律之美上升为和谐之美。
钱钟书在《管锥编》中谈道:“吾国首拈‘韵’以通论书画诗文者,北宋范温其人也。温著《潜溪诗眼》,今已久佚,……惟《永乐大典》卷八〇七《诗》字下所引一则,因书画之‘韵’推及诗文之‘韵’,洋洋千数百言,匪特为‘神韵说’之弘纲要领。亦且为由画‘韵’而及诗‘韵’之转捩进阶。”宋代对“韵”的重视与探讨,确实为明清时期出现的“神韵”说奠定了基础。但刘勰《文心雕龙》在《声律》篇中已谈及诗韵,钱钟书先生说因书画之“韵”推及诗文之“韵”,这一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更具体地看,唐宋诗论中“韵”包括声律层面的“韵”,但“韵”的内涵更为丰富,“韵”已被提升为诗歌审美的核心元素,“韵”作为诗学批评标准,诸如“韵不可及”、“声清韵古”、“神清韵远”等语常用于诗歌评论。
历代诗论家有许多关于“韵”的论述,如范温谓“有余意之谓韵”,推崇“韵者美之极”。范温的“韵”与刘勰《文心雕龙·隐秀》篇中“文外之重旨”的“隐”,钟嵘《诗品》中以“文已尽而意有余”之“兴”,皎然的“文外之旨”、“但见性情,不睹文字”,司空图倾心的“韵外之致”、“味外之旨”、“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审美情趣一脉相承,异曲同工。钱先生认识到这一点,对“韵”也界定为:“取之象外,得之言表,‘韵’之谓也。”这种观点与宋代诗论中对《古诗十九首》“韵不可及”,即“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无意与工、妙然天成的诗歌境界妙合神会。更进一步来看,“韵”的本质内涵乃为“和”,即由“自然”而达至“中和”、“和谐”的“神”与“化”之美。
二、韵不可及:张戒与《古诗十九首》
“作为宋人论诗的一个核心范畴,‘韵’成为宋人建构其诗学理论系统的基本质素和子系统,它从一个视域影响了宋代诗学批评和理论面貌的生成。”张戒与严羽的诗论始肇从审美本质论“韵”。姜夔将“韵”视为诗歌审美的质性要素,在《白石道人诗说》中论道:“大凡诗,自有气象、体面、血脉、韵度。气象欲其浑厚,其失也俗;体面欲其宏大,其失也狂;血脉欲其贯穿,其失也露;韵度欲其飘逸,其失也轻。”张戒对“韵”的标举、严羽对“入神”的力推,启发了明清有关诗歌审美的“神韵”说。
张戒的《岁寒堂诗话》以“意”、“味”、“韵”和“气”四大范畴品评诗人与论诗。在张戒看来,诗人各有所长,诗歌各显其貌,如:“阮嗣宗诗,专以意胜;陶渊明诗,专以味胜;曹子建诗,专以韵胜;杜子美诗,专以气胜。”“韦苏州诗,韵高而气清。王右丞诗,格老而味长。虽皆五言之宗匠,然互有得失,不无优劣。以标韵观之,右丞远不逮苏州。至于词不迫切,而味甚长,虽苏州亦所不及也。”
张戒通过区分“意”、“味”、“韵”和“气”,明确地把“韵”提升为诗歌审美的核心元素。对此四者,张戒认为:“然意可学也,味亦可学也,若夫韵有高下,气有强弱,则不可强矣。‘意’、‘味’易学,可‘用工’(诗意与语词的工巧)而‘中的’,而‘韵’、‘气’难至,乃出自天然,‘人才各有分限,尺寸不可强’。”显然,韵味之出自天然,不可模仿。南宋姜夔的《白石道人诗说》也说:“一家之语自有一家之风味,如乐之二十四调各有韵声,乃是归宿处。模仿者语虽似之,韵已无矣。”
张戒之所以推崇《古诗十九首》,首先在于其“韵不可及”。张戒认为:“观子建之诗,铿锵音节,抑扬态度,温润清和,金声而玉振之,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与《三百五篇》异世同律,此所谓韵不可及也。”更无须说“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无意与工、妙然天成的《古诗十九首》了。张、严对《古诗十九首》“韵不可及”的断语,正是来自其对《古诗十九首》“浑然天成”、“无迹可求”、“难以句摘”的认识。
张戒诗评中广泛使用“韵”一词,加上与“韵”字搭配的如“洒落之韵”、“韵度”、“标韵”、“高韵”、“格韵”等称呼多达二十余处。譬如他说:“韵有不可及者,曹子建是也”;“韦苏州诗,韵高而气清”;“随州诗,韵度不能如苏州之高简”,等等。他认为“温润清和”、“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的“韵”是诗歌审美本质的体现与至高境界。
宋人论“韵”重“意”,论诗多谈“格韵”,承接了唐人王昌龄、皎然以意论格,以格论诗的传统,崇尚“情格并高”、“格高律清”的诗学思想。《东坡诗话》有云:“鲁直诗文,如蝤蛑、江瑶柱,格韵高绝。”有宋一代之诗话里,此类言论举不胜举。很显然,宋人已将“韵”作为诗学批评标准用于论诗之中。张戒也讲格韵,其《岁寒堂诗话》下卷“江头五咏”一条中说:“物类虽同,格韵不等。同是花也,而梅花与桃李异观;同是鸟也,而鹰隼与燕雀殊科,咏物者要当高得其格致韵味,下得其形似,各相称耳。”同时,张戒将“韵”与“气”、“味”相连,追求诗歌卓然天成、不可复及的诗歌美之极,即意高、气胜、味长、情真之“众善皆备”的韵之至。
宋代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说道:“古诗苏李曹刘陶阮本不期于咏物,而咏物之工,卓然天成,不可复及。其情真,其味长,其气胜,视《三百篇》几于无愧,凡以得诗人之本意也。”他特以《古诗十九首》中句子为范例来解释古诗的“情真、味长、气胜”,而达其“意在言外,词婉意微,不迫不露的格致韵味”,如:
“萧萧马鸣,悠悠旆旌”,以“萧萧”、“悠悠”字,而出师整暇之情状,宛在目前。此语非惟创始之为难,乃中的之为工也。荆轲云:“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自常人观之,语既不多,又无新巧,然而此二语遂能写出天地愁惨之状,极壮士赴死如归之情,此亦所谓中的也。《古诗》:“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萧萧”两字,处处可用,然惟坟墓之间,白杨悲风,尤为至切,所以为奇。乐天云:“说喜不得言喜,说怨不得言怨。”乐天特得其粗尔。此句用“悲”、“愁”字,乃愈见其亲切处,何可少耶?诗人之工,特在一时情味,固不可预设法式也。
张戒以“萧萧”两字为例,认为其处处可用。通过比照,《诗经》中创始之为难,乃中的之为工,楚调中虽无新巧,但也能“中的”。“中的”乃辞能合意,已而《古诗十九首》不仅“中的”,且“尤为至切,所以为奇”,因其特在一时情真味长,用词不预设法式,又如:
《国风》云:“爱而不见,搔首踟蹰。”“瞻望弗及,伫立以泣。”其词婉,其意微,不迫不露,此其所以可贵也。《古诗》云:“馨香盈怀袖,路远莫致之。”李太白云:“皓齿终不发,芳心空自持。”皆无愧于《国风》矣。
张戒论诗处处比附《诗经》,以“馨香盈怀袖,路远莫致之”为例,谈起词婉意微,不迫不露。又如:
陶渊明云:“世间有乔松,于今定何闻。”此则初出于无意。曹子建云:“虚无求列仙,松子久吾欺。”此语虽甚工,而意乃怨怒。《古诗》云:“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可谓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也。
在张戒眼中,“陶渊明诗,专以味胜;曹子建诗,专以韵胜”,“韵有不可及者,曹子建是也。味有不可及者,渊明是也”,而与《古诗十九首》比较,也略逊一筹,其对古诗的推崇可见一斑。
张戒《岁寒堂诗话》虽着力构建自己的诗学理论框架,提出许多有价值的诗学主张,但始终未能摆脱儒家诗学观念的影响。其诗论主张情志要“正”,不落“邪思”,并多次引述《诗大序》的论点,处处以《诗三百》为典范。如“言志乃诗人之本意,咏物特诗人之余事”,把“言志”作为论诗的宗旨。并认为杜甫诗作在思想内容上继承了由《诗经》和《离骚》开创的“言志”传统,而在形式和技巧上则吸取了汉、魏以来的艺术成就。
张戒把历代诗歌分为五等,主张学诗者应逐段研究,从头学起,反对直接学习杜甫,更反对学习苏、黄。他说:“国朝诸人诗为一等,唐人诗为一等,六朝诗为一等,陶、阮、建安七子、两汉为一等,《风》《骚》为一等,学者须以次参究,盈科而后进,可也。”宋代诗论大多未能越出儒家道统的范畴,甚至连苏东坡这样的大家也不例外,但严羽的《沧浪诗话》却没有涉及《诗经》的典范意义,更无称引《诗经》之处。在严羽的诗学体系中,《楚辞》乃诗歌之本,“至于汉魏晋宋齐梁之诗,其品第相去高下悬绝,乃混而称之,谓锱铢而较实有不同处,大率异户而同门,岂其然乎”(《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可见,严羽舍齐梁之诗,标“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
三、“韵”不假悟:严羽与《古诗十九首》
严羽以禅喻诗,以“悟”沟通诗禅,虽未明言“韵”,但在审美本质上则以“韵味”系之。《沧浪诗话》云:“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所谓“神”,《易经·系辞上》韩康伯注:“神也者,变化之极。妙万物而言,不可形诘者也。”在严羽的诗学思想中,“入神”乃诗歌美的极致,其具体体现在诗歌的“兴趣”,即“不涉理路、不落言筌”、“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为“无迹可求”、“言有尽而意无穷”的韵味。在严氏眼里,这种“韵味”无疑即诗歌的审美本质。不假悟,也就是不拘泥于外在形式的束缚,妙然天成。
严羽又提出以词、理、意兴为参照的标准论诗,认为:“南朝人尚词而病于理,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汉魏之诗词理意兴无迹可求。”虽然无迹可求的汉魏古诗“气象混沌,难以句摘”,建安之作也“全在气象,不可寻枝摘叶”,而晋以还方有佳句。在严羽的美学标准中,浑成质朴自然之美高于精工之作,汉魏古诗的美学品格较之唐诗高出一层。从学诗的角度,严羽认为“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其总的原则“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具体来说,学诗“工夫须从上做下,不可从下做上,先须熟读楚词,朝夕风咏,以为之本;及读古诗十九首、乐府四篇;李陵、苏武、汉魏五言皆须熟读;即以李杜二集枕藉观之,如今人之治经”。熟读楚词、《古诗十九首》、乐府四篇、李陵、苏武、汉魏五言很重要,而真正可以为法的乃盛唐之“李杜二集”。严羽认为学诗“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但“汉魏尚矣,不假悟也”。所以,严羽“推原汉魏以来,而截然谓当以盛唐为法”。
然悟有浅深、有分限、有透彻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谢灵运至盛唐诸公乃透彻之悟也,可以学,而汉魏古诗不假悟,不可学。汉魏古诗中,严羽又突显汉诗,首推《古诗十九首》。如他说:“‘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一连六句皆用叠字,令人必以为句法重复之甚。古诗正不当以此论之也。”古诗不专注于词句的锤炼安排,不拘泥于外在形式的束缚,一切以情性为本,乃不假悟也。
宋代诗话繁兴,其内容则大都比较零碎,近于随笔,“以资闲谈”(《六一诗话》),但潘德舆将南宋张戒的《岁寒堂诗话》、严羽的《沧浪诗话》与姜夔的《白石道人诗说》推许为“鼎足”的“金绳宝筏”(《养一斋诗话》卷八)。其中,《岁寒堂诗话》自成体系,张宗泰说它“远出诸家评诗者之上”(《鲁岩所学集·跋〈岁寒堂诗话〉》)。严羽的《沧浪诗话》更是一部有系统之作,它们的出现标志着以诗话形式探讨诗歌艺术理论进入了更自觉的阶段。虽然张戒与严羽的诗话均是针对宋诗,尤其是江西诗派以及“四灵”和江湖派的流弊而作的,其论诗宗旨均标榜盛唐,推崇杜甫,但他们对《古诗十九首》的地位与审美价值的认识是一致的。张戒认为:“古今诗人推及陈王及古诗第一,此乃不易之论。”严羽认为汉魏盛唐的诗歌,才是“大乘禅”、“正法眼”、“第一义”。张戒推崇杜甫,其《岁寒堂诗话》下卷乃杜甫之专论,将杜甫渊源追溯到汉魏古诗,“识汉魏诗,然后知子美遣词处”,“屋下架屋,愈见其小,后有作者出,必欲与李杜争衡,当复从汉魏诗中出尔”。汉魏之诗中,张戒最推崇的是古诗,其曰:“钟嵘《诗品》以《古诗》第一,子建次之,此论诚然。”由此看来,两者均“推源汉魏以来,而截然谓当以盛唐为法”。
张戒和严羽都认为汉魏古诗的美学品格高于盛唐之诗,为什么他们又都极力主张向盛唐学习呢?对这一问题,严羽自己有过解释。严羽认为“后舍汉魏而独言盛唐者,谓古律之体备也”,也就是说诗到盛唐,各体具备,诸法并存,各种体裁和格律都已经充分成熟完备,盛唐诗歌有阶级可循,更便于人们参悟和模习;而“汉魏古诗,气象混沌,难以句摘”,“词理意兴无迹可求”,浑成质朴,具有化工之妙,达到诗歌“极其致”的境界。“韵不可及”、“韵不假悟”的诗歌经典《古诗十九首》,才真正是其诗美理想的最高追求,是中国古代诗歌的极致,其无迹可求,妙不可学。
纵观六朝至宋元时代,“清诗”一直是被用来评价“好诗”的。对《古诗十九首》的审美阐释,从“丽”、“真”到“韵”,“清”贯穿其中。随着时代审美风尚的迁移与审美趣味的转换,对诗歌的审美认识也不断深入。“清丽”之“丽”,反映了六朝时期人们对于文学之为文学外在表征的发现与弘扬;“清真”之“真”的转向,说明了道佛思想对唐人的浸染,并折射出诗歌审美“质”的光亮;“清韵”之“韵”的崇尚,透露了宋人的雅趣及对“全美”的追求。《古诗十九首》作为诗歌经典的价值与意义,体现在其提供了这样一种审美参照——不同时代的人与之遭遇,进入其中,都能带回他们所需的宝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