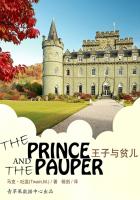日本人怏怏地转身回房间,一边自言自语:"不对呀,以前打电话过来的中国女人,不会说英语的。"
任百加不理他,让他一个人纳闷去。
周末那天,任百加一早就起了床,关在卫生间里仔细地刮脸修面,收拾自己。他先穿了一套西服,打上前一天特意上街买回来的领带,又往头发上抹一点摩丝。对镜细看,怎么都像个新郎官的样子,正经得可笑。他赶快脱了西服,换上一条牛仔裤,配一件黑色高领毛衣,头发重新洗过,用手心胡掳得乱一些,镜子里的人看上去才比较地随意和自然。
他不想到得太早,以免让别人觉得他过份的急迫。他磨磨蹭蹭到中午,吃下去一包方便面,才出发赶火车。两小时后他到了牛津,先买一张地图,弄清楚陈抱婴家的大致方位,用原珠笔画出最简捷的路径,然后一路对照地图走过去,竟然不需要询问一个人,就摸到了他要找的地方。
他站在涂白漆的铸铁栅栏前,定了好一会儿神,才抬高嗓门喊一句:"家里有人吗?"
同样涂着白漆的木房门应声而开,扎着一条花布围裙的陈抱婴笑嘻嘻走出来:"任百加,你最后一个到,晚上要罚你喝白酒。"
屋里已经热热闹闹围了一大帮子人,切肉的,洗菜的,从窗户里钻进钻出拉电线的,个个手里都有活儿干。因为都是国内来的留学生,彼此之间很有认同感,见面不久自来熟,大家很快混成了老朋友。
陈抱婴对任百加介绍她的新婚丈夫,一个戴眼镜、瘦巴巴、面孔有点严肃的人,学数力学的。任百加握着他的手,感觉这个人在这一群人当中有点例外,任百加怎么也不能对他亲近起来,只好例行公事地说:"很高兴能够认识你。"
对方同样是公事公办的样子:"我也高兴认识你。"
任百加掏出一瓶香奈儿的"COCO"香水,迟疑一下,递给陈抱婴:"不知道给你送什么结婚礼物好。不知道这个牌子的味道你喜欢不喜欢。"
陈抱婴握着香水,有一点惊喜:"喜欢啊!你选的东西,我肯定都喜欢啊!"
任百加看到陈抱婴丈夫的脸颊抽动了一下,不知道他是不满意陈抱婴的有点轻佻的说话呢,还是不满意别人给他的妻子送香水?
很快,任百加洗了手,挽起袖子,加入到忙碌的备餐人员中。他对厨艺还是有一些无师自通的领悟力的,加上出国大半年的历练,煎炒炖炸都能够玩出一些花样。他自告奋勇给大家做锅贴:其实就是芹菜猪肉馅的饺子,不用水煮,改用平底锅加水和油煎。他做出来的锅贴很像那么回事,表皮黄澄澄的,冒着滋滋的油泡,咬开来,里面汪着一包汁水,实在称得上里焦外嫩。结果这些锅贴不等上桌就被大家抢得精光,连盘子都不需要用,直接从锅里拈出来往嘴巴送,一边烫得舌头打滚,嘴角滴油,一边称赞好吃。
陈抱婴在旁边笑着:"任百加,干脆我们大家凑钱出股份,你到牛津来开个锅贴店算了。"
任百加回答:"能不能赚大钱?能赚大钱我就干。"
他变戏法样地从灶台后面拖出一个盘子,里面盛着十来只煎好的锅贴,塞到陈抱婴手上,小声说:"拿着,到一边吃去,我看你总是抢不到食。"
陈抱婴说:"你吃!你忙了半天,都忙到了别人的肚子里。"
任百加心满意足地搓着手:"大厨师都这样啊,看到别人吃得高兴,自己就饱了,吃不吃都无所谓。"
陈抱婴瞪圆了眼睛:"什么大厨师啊!说你胖,你还真就喘了。"
两个人都笑起来。任百加觉得自己出国以后还从来没有这么开心过。
烧烤餐会一直热闹到晚上十点钟。每个人都吃了一肚子的牛肉羊肉,听了一肚子的荤段子素段子,尽兴而散。陈抱婴在楼下的小客厅里收拾出一张比较宽大的沙发,临时铺了被褥,对任百加道歉说:"这房子里没有多余的床,只好请你睡沙发了。"任百加一屁股坐下来,说:"沙发很好,比大学宿舍里的双人架子床好得多。"
任百加简单地洗漱之后,在沙发上和衣而卧。想到从认识陈抱婴之后,这么多年,他还是第一次跟她睡在同一座房子里,心里不免激动,一时间鼻子里闻到的都是她的气味,耳朵里听到的也全是她的呼吸声和说话声。
陈抱婴果真是在说话,在跟她的丈夫争论什么。一开始在楼上淋浴房里,她丈夫的声音很琐碎,绵延不绝,无休无止,像从前小巷子里用木弓弹棉花的那种单调和寡味。陈抱婴偶尔应答一句,言辞果断而又干脆,与她丈夫的声音恰成对比。水声哗哗,好像她一直不停地在洗浴,说话只是洗浴过程中可有可无的插曲。沐浴露的热烘烘的香味从门缝里渗出来,淡淡地弥漫到楼下,任百加的鼻子有一点发痒,忍不住要打喷嚏。然后水声停了,陈抱婴的脚穿到了拖鞋里,拖鞋轻轻地响动,在淋浴房里来回转了两圈,接着穿过很短的走廊,进到卧室。卧室的位置应该在小客厅上方,任百加觉得楼上所有的动作都是在他头顶上进行的,他如果屏住呼吸,展开想像,完全可以判断出他们两个人所站的角落,临睡前所做的每一件琐事,甚至猜得出他们是脸对脸,还是背靠背,他们分别睡在床的哪一边,以及他们说话时脸上分分秒秒变化的神情。总之,任百加从来没有发现自己有这样奇妙的能力,他的脑子里像新装了一台极端灵敏的雷达,能够捕捉到所有飘扬在楼内空气中的微妙的气息。
后来,楼上完全地安静了,可是任百加仍然睡不着觉。翻来复去,总在惦记一件事情。最后他明白了自己惦记的是什么:楼上床铺的响动。他也搞不清他为什么要在意这个,绝对不是出于隐秘促狭的欲望,他还不至于无聊如此。那么他到底为什么呢?他想,大概,在意识深处,他只是希望看到由一个陌生人来实现的对陈抱婴的征服,从而证明她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他期盼陈抱婴在他心中从神的位置上降下来,降到与他等高的平面,从此他可以跟她平等相处。
可是,楼上的两个人一动不动,安静得像死了一样,像是存心要让任百加的希望落空,让他辗转反侧不得安眠。
结果任百加第二天早上醒过来的时候,拉开窗帘,阳光已经照满房间。他穿衣出门,陈抱婴手里拿着装牛奶的塑料小桶,笑吟吟地迎上前来。
"睡得还好吗?"
任百加点头:"挺好。挺舒服。"
"去洗把脸,来吃早饭。我煮了牛奶麦片粥。"
任百加转动着脑袋,往四下里看。
陈抱婴知道他看什么,说:"他不在,一早就去了实验室。"
任百加惊讶:"星期天也去吗?"
陈抱婴回答:"每天都去,雷打不动。"
任百加想,学理科的人就要有这样的毅力才能成功吧?
他走进卫生间,陈抱婴已经替他把牙膏挤到了牙刷上,简易刮胡刀也搁在水盆边。他吐着泡沫刷牙的时候,陈抱婴在外面征询他的意见:"上午我们出去采蘑菇,好不好?"
他无法说话,在喉咙里大声地嗯了一下。
陈抱婴像孩子一样开心:"这儿的草地太肥沃了,蘑菇到处都是!刚来的时候我还不敢采,怕有毒。我们有个朋友是学农林的,他说没事,只管采回家吃吧,煮出汤来会鲜得让你掉下巴呀!"
他吐出一口漱口水,转头对门外说:"蘑菇吃多了,当心皮肤上长出孢菌来。"
陈抱婴先是吃惊地:"会吗?"然后又自言自语:"不会吧?"
任百加把脑袋扎在水盆里,笑得肩膀直发抖。
稍顷,他坐到了餐桌边,看着陈抱婴一道一道给他上早餐,享受一家之主才有的幸福。早餐的内容包括煎火腿蛋,咖啡,牛奶麦片粥,煮花生米,扬州酱菜,真正的中西结合。陈抱婴笑着声明:"全是为你准备的。他早上只喝咖啡,最多烤一片面包。"
任百加目不转睛看着她:"你把头发剪短了?"
陈抱婴抬手胡掳了一下她的短发,扬起脸:"是不是看着有点蠢?"
任百加说:"不,短了有短的味道,显得很年轻,很精神。"又说:"我昨天就想告诉你,人太多,不好说。"
陈抱婴小姑娘似地红了红脸:"出国前剪的。单位同事说,国外剪头发特别贵,我就索性剪成这么个男孩样的头。以后,隔一两个月,把耳朵下面长出来的修一修就行,最简单最省钱。"
她说完,自己忽然觉得很好笑,捂着嘴笑起来,肩膀轻轻地晃动着,上身有一点小幅度的摇摆。她左手无名指上有一颗碎钻的婚戒,手抬起来捂在脸上的时候,钻戒恰好停留在嘴巴的位置,一晃一晃,波光流淌,活像说话时口吐莲花。
任百加端起咖啡,咕咚咕咚一口气喝完,夹起整只煎蛋塞进嘴巴,又将一碗麦片粥三口两口吞进喉咙,最后伸长脖子,顺下一口气去,抹抹嘴巴说:"我必须走了。"
陈抱婴睁大眼睛:"为什么?不是说好了采蘑菇去吗?"
任百加别过脸:"我必须走,我不能跟你装模作样地采一上午蘑菇,好像我们之间什么关系都没有,我对你什么也不想。我做不到。"
陈抱婴嘴巴张了一张,戴钻戒的那只左手又一次抬起来,停留在脖颈处,扼住喉咙似的,不动。
任百加站起身,恳求她:"你送送我。"
陈抱婴转过头:"不。"
"求你!就送到街口,免得我走得太难过。"
陈抱婴沉默了半分钟,忽然轻轻地笑了一下,跟着站起来:"任百加,我们两个人永远都是生活在尴尬中啊!"
她真的只把任百加送到街口,就停下来,不再往前。
十二
一年访问期满,任百加没有再申请延长,收拾行装回国了。走前他给陈抱婴打了个电话,没有人接。他转而发了张明信片,告之行踪的意思,免得陈抱婴有事再找他时,以为他忽然从人间蒸发。
回国第二天,李梅上班,阳阳上学,他在家里整理自己的衣箱,该洗的洗,该收的收,该挂的挂。这些零碎的事,一般都是他自己做,李梅不插手。
他打开卧室大衣橱,往里面顺几套换洗内衣时,发现了一条陌生的男用三角裤。裤子是淡灰色,半新不旧,但是质地很好,地道的国外名牌。肯定不是他自己的,他从来不舍得买这么名牌的内衣,而且,他一向穿平脚裤,不穿三角裤。他在李梅面前穿着三角裤会觉得不自在。
任百加用两根指头拎着这条裤子,在衣橱前呆呆地站了很久。他看见穿衣镜里自己的形像很落拓,头发太长,胡子拉楂,眼神灰暗无光,就连皮肤的颜色都显出沉闷,旧,打了一层哑光蜡似的。
任百加把裤子叠放在床罩上,在进卧室的醒目处。然后,他继续收拾自己的东西。再然后,他出门买了菜,做好饭,去学校接回阳阳,坐下来督促他做作业。
李梅回来了,招呼了他们,进卧室换衣服,许久没动静。
任百加进去看她,顺手把卧室门关严,不让阳阳听见夫妻间的话。任百加看见李梅坐在床沿上,背着身,三角裤头正好坐在她的屁股下。他起先以为她在哭,绕到她的正面去细瞧,她脸上没有泪,是在出神。
"饭已经做好了,先去吃饭吧。"任百加劝她。
李梅凄凄地望着他:"任百加,我们肯定是要离婚的。"
任百加点头:"我想到了。"
"我本来不想这么早说。你刚回来,我该让你好好歇几天。"
任百加苦笑:"还是早点说的好。迟说不如早说。"
"我……我准备……我原来想……"李梅结结巴巴,要哭出来的模样。
任百加忽然有些心疼她,走过去,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顺便拉她站起来:"走走,吃饭去,现在不提这事。"
餐桌上,他着意要冲淡一些弥漫在家庭中的悲伤气氛,就搜肠刮肚讲他留学生涯中的有趣故事,甚至讲到了陈抱婴家的烧烤会,他做的那些色香味俱全的猪肉芹菜锅贴。
李梅一直闷头听,此刻才不经意地问了一句话:"陈抱婴结婚后还好吧?"
任百加想了想:"应该还好吧?她在牛津做全职太太,看上去还快乐。"
"全职太太她做得惯?"
"只能这样。她在英国找不到工作的,除非打零工。"
"那就应该快点要个孩子,好打发时间。"李梅替古人担忧。
阳阳建议说:"爸爸,你明天也给我们做一次锅贴吧。"
任百加说:"好,做三鲜锅贴,用虾仁、香菇、鸡肉。做上几大盘,冻在冰箱里,让你想吃就能吃得到。"
晚饭后,李梅主动去洗碗,任百加继续辅导阳阳做作业。作业太多,阳阳的小手写得都有点发肿,头低得久了,眼泡也是肿肿的。任百加万般不舍,却又无可奈何,只能在旁边帮他削铅笔,递橡皮。一直到九点多钟,功课结束,任百加才如释重负,帮他洗了澡,把他送上床。任百加腰酸背疼地想,看孩子做功课真比自己写论文还累。
李梅早早地进了卧室,开了一盏床头灯,坐在床边上等着他。任百加一进门之后,李梅就说:"你什么都不要问,我来把一切告诉你。"
是一个私营企业主,开办公用品公司的,李梅说。一开始,他的女儿在李梅家里上家教,课结束之后,都是这个人来接孩子。李梅觉得奇怪,就顺便问起了孩子的妈妈。原来他们早就离婚了。也不叫离婚,是孩子的妈妈离家出走。那时女人还年轻,男人的公司刚起步,很艰难,也没有什么钱。女人看不到希望,生下孩子就去了北京,做起了京漂一族。好像现在自己也开了公司,不再结婚,跟人同居着。李梅喜欢这个上家教的女孩子,也心疼她没有母亲照顾,常常接她到家里来吃饭,跟阳阳做玩伴。女孩的爸爸为表示感谢,常买些礼物送过来。后来,父女两个都到李梅家里来吃饭了。再后来,男人吃完饭,把女儿送到奶奶家,自己又开车回来了,来了就不再走了……
"你确信自己喜欢她?"任百加冷静地问。
李梅问头。
"他正式向你求过婚?"
"他说,要是我跟他结合,我们就有一儿一女,天底下最幸福的家庭。"
任百加心里闷得发疼,像堵了一个大秤砣。
李梅始终低着头,一副任打任骂的可怜样。任百加沉默了好一会儿,心里涌出很多愤怒的话,挖苦的话,嘲讽刺人的话。可是他最终什么也没说。他站起来,把床上的被子往李梅那边推了推,然后从壁橱里拿出另外的一床,铺开,留给自己睡。他们的房子就这么大,分床暂时还不可能,那就用被子隔一隔,算是他的一个态度。
任百加睡下去之后,李梅还是坐在床边,一动不动。任百加催她:"耗着干什么呢?你明天不还要上班吗?"
李梅转过身,幽幽地问了他一句:"任百加,你想不想最后再要我一次?"
任百加看了她足有两分钟,摇了摇头。
李梅的眼泪一下子出来了:"求求你,让我们有个圆满的结局,别让我心里欠你太多。"
任百加朝自己身下瞥一眼:"不行,就是我想要,它也不想,不肯帮忙。"
李梅喘一口粗气,忽然疯了一样地扑上去,掀开任百加的被子,不由分说把他的短裤扯下来,整个脑袋热乎乎地埋到他的小腹处,贴紧了、粘上了一样,再也不肯松开来。任百加何时经历过这样激情勃发的阵势呢?他只觉得体内"轰"地一下就着了火,火苗儿烧得他口干舌燥,星光飞舞,他不由自主地挺起身,两手抱紧李梅的脑袋,只差没把她的头发搓碎和揉烂。
这一场搏斗整整持续半个多小时,双方都精疲力尽,都耗尽了全部的激情和体力。李梅最后瘫倒在枕头上的时候,鱼一样地张着嘴,大喘气,断断续续说:"任百加,你从来没有这么好。"
任百加心里想,其实是她自己从来没有章 淡漠的、被动的人,他们的性生活从来都是按部就班,点到为止。可是在他出国的章 恣意而又激情澎湃的人。
士别三日,刮目相看。只是,人性的完善为什么不是经由他的手?为什么他从来没有想到花朵也要浇灌才开放?
任百加在黑暗中睡不着觉,把他婚姻的前后经历想了又想。李梅也睡不着,脑袋在他旁边的枕头上悉悉索索,转来倒去。过了很久,她轻轻叹一口气,说:"每次我跟他做过事,他都要抱着我,直到我睡着。你不会,一次都没有,因为你从来就没有爱过我。"
十三
任百加离婚后,觉得应该给陈抱婴打个电话,告诉她有这么一件事。电话打过去,接电话的偏巧是那个学数力学的博士后,听到他一声平淡无味的"哈罗?"任百加立刻把话筒搁下了。他不愿意跟那个人说话。倒也不是有多么大的成见,只是没兴趣开口,连一声"你好!能不能请陈抱婴接电话?"都不想说。
后来他就没有再跟陈抱婴联系过。他对自己说,电话是打过的,陈抱婴没有接到,那是她的原因,责任不在他。
他的导师去了加拿大,与多伦多大学的教授合作做一个课题,有关东方巫术的研究。导师去了两个月之后,写了很正式的信给任百加,说是课题太大,人手不够,希望任百加过去帮忙,经费已经帮他申请下来了。任百加拿着导师的信去找系领导紧急磋商,得到同意后,又急急忙忙找使馆办签证,在最短的时间内打点妥了一切,登上飞机直奔多伦多。
加拿大给他的第一印像就是冷,比英国又要冷很多,十月底已经是冰天雪地的样子,南方长大的任百加相当不习惯。他买了一辆二手车,因为一开始不懂得严寒天气下如何去保养,汽车老是发动不起来,给他摆脸子看,弄得他很狼狈。有一次在学校停车场,他坐进汽车,折腾半天都无法让这个铁家伙挪动一下窝的时候,走过来一个穿大红色羽绒服的东方女孩子,敲着他的窗户,声音脆脆地询问他:"请问需要帮忙吗?"
他打开车门,脚踩在雪地里的刹那间,惊讶得呼吸都冻住了。女孩子身材高挑,模样相当洋气,眼睛、嘴巴、鼻子在那张脸上无一处不和谐,说不出来的生动和出彩,活脱脱一个年轻的陈抱婴。
她果然就是陈抱婴的妹妹,名字也近得很,叫"爱婴"。她说她已经在加拿大好多年了,大学毕业就工作,已经是一家华语电台的资深主持人。她笑,眉眼里飞扬着跟陈抱婴相似的韵致,说:"我姐姐以前跟我说过你。"
爱婴单身。有过几次跟西方男人同居的经历,结果总是新鲜劲儿一过,彼此和平分手。她告诉任百加说:"到底不是一回事。"
任百加无论如何也不肯再失去机会了。他争分夺秒地跟陈爱婴谈恋爱,同居,结婚。两年过后导师回国时,任百加没有回,因为他已经有了一个女儿,一个总也让他抱不够的可爱的婴儿。导师临上飞机前跟任百加开玩笑,说,百加啊,你要记住,是我的课题成全了你哦。
任百加感激涕零,决定这一辈子要把他的导师当作父亲爱。每天晚上他睡在暖气很足的房子里,左边搂着陈爱婴,右边拥着他们的小女儿,心里想,他总算看到了女人如花开放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他可以从从容容地看,全心全意地爱抚和宝贝。在这样静谧的夜晚中,所有的梦境都变成了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