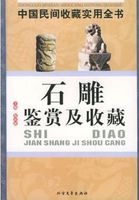如果说《东》昭示了宽松以来新生代电影中“先锋”与“民间”转喻共生链条的迅速崩离,那么其后《无用》的三段论叙事自身就带有“无用”的时代症候。影片希望借助服装制作作为切入点,将广州的现代化服装流水线、巴黎的神秘风格时装发布会和汾阳老旧的裁缝店贯穿在一个故事链条之内,在结构上以三段论的方式追问时尚与权力的合谋关系,然而在叙事上势必要遭遇草根与先锋两种叙事立场的错位交锋。
第一段故事在自左而右缓慢平移的长镜头中,堆积如山的衣料,“兄弟牌”缝纫机高速旋转,工人佝着腰操作,笨重而锋利的裁衣剪、嗒嗒作响的“银箭牌”锁边机依次闪过,最后静静地定格在衣领处的外文商标上。这些像带鱼一样从工厂栅栏中挤进挤出的青年人,吃着廉价的盒饭,抱怨着咽痛和眼疾,与他们所代工的国际知名服装品牌分属两个存在着天壤之别的世界。作为这种真实的发掘者与提示者,导演一如既往地站在镜头后面,他甚至突兀地切入十几年前的流行老歌,黄家驹的《情人》,为这段枯燥的工作场景做出煽人泪下的批注。第二个段落迅速转场到巴黎时装周一场题为“无用”的时装展示。依然是节奏缓慢的水平长镜头,一丝不苟地捕捉设计师的言行举止,从服装样式的选择、模特的化妆,到秀场的灯光处理,甚至现场泥土的性状与颜色都不分巨细记录下来。将这些琐碎的镜头连缀起来,就会发现导演在努力寻找与服装设计师理念相匹配的文化逻辑:工业流水线产品的使用者与制造者不存在情感关联,因此要返回纯粹手工时代,重建肉身与衣服的历史记忆。由此,“土地”在服装与个人之间承担了历史媒介的作用。怀着对生活常识之外时尚经验的真诚好奇,导演的目光被设计师的玄幻理念所吸引。也许导演希望借此切入国际服装产业经济链条,完成对现行市场消费主义的批判。但是,与这种坚定的批判立场相比,导演面对“无用”的态度却显得暧昧而游移。一方面,在纺织艺人手工赶制服装的特写镜头中一如既往地表现出对于劳作的朴素热情;另一方面,导演借助“无用”批判当代时尚,却恰恰堕入了新的权力圈套。设计师鼓吹自然法则,将手工制作的衣物埋藏在土壤里,依靠自然造化创造永不落伍的“无时间性”服装,这不过是品牌策略所惯用的广告噱头。“土地”、“历史”与“记忆”等宏大叙述的元概念仅仅在修辞的效果上完成了臆想中的“重建”,而所谓“人衣合一”的场景更不过是巴黎秀场的一簇烟幕弹,是消费资本主义生产过剩之后无力续借繁华的虚幻假象,岂非是对《无用》民间立场迷失后的一次嘲讽?
也许是一种下意识的文化修复,第三段伊始,时装设计师驱车走在尘土飞扬的盘桓山道上,画外音提示,国际设计师想从陌生的山村生活中寻找新的时尚灵感。然而这次不知所终的探险提前暴露了她与当下现实价值的严重疏离。与此相反,咣当作响的铁轨,公共汽车掀起的烟尘,夜幕下静静伫立的煤矿工人,面目全非的“蝴蝶牌”和“上工牌”缝纫机,统统携带着鲜活的真实感扑面而来。连导演都被这种呼之欲出的气氛所感染,终于,掌镜者的声音迫不及待地在镜头后面响起来,扑入他所记录的事件当中。生动的现场感不仅保证了记录的真实性,而且也将此前被强行“圈入”的“民间”从观念先行的“先锋”文化中剥离出来,重新焕发出盲目的、粗野的和前进的力量,这恰恰才是“民间”精神的本源所在。
可写性/可读性:后殖民视阈下的国际旅行
以“可写的”(Scriptible)或“可读的”(Lisible)来考察新世纪以来新生代电影的不同叙事面向,其目的是为了探讨国际电影节之于新生代创作的影响因素。如同一把双刃剑,国际电影节为新生代导演创造了跻身全球电影市场最为便捷的路径,而与此同时,国内投资与国际基金两种资本力量之间存在着极度的失衡,新生代电影很难避免被某些国际电影节特定美学趣味影响甚至左右。
当新生代导演最初动手拍摄属于他们自己的生活时,通常表现为一种“情动于中,故形于声”的艺术自觉,并非某些国际电影节评委所一味暗示的“意识形态”的要求,或者“反意识形态”的要求。如前所述,在新生代导演的早期电影创作中,自传或者半自传体的成长故事占据了大量的篇幅。如果联想到启蒙运动之后德国最早兴起的“成长小说”(Bildungaroman),就会发现这种新的创作主题的产生,其实源自于德国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冲动。因为“国家”、“主体”等相对于彼时的德国而言是陌生的外来词汇,需要不断克服自身的弱点将自己培养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成人”。参见樊国宾:《主体的生成——50年成长小说研究》,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年,页1。而对这批“红小兵”来说,面对1990年代以来的意识形态变局以及随之而来的新的国家形象叙事冲动,“他们既没有壮烈的历史可以反思,也没有极端的现实可以批判”林少雄:《关于近20年中国电影的18个关键词》,陈犀禾、石川:《多元语境中的新生代电影》,学林出版社,2002年,页204。,这些“没有自己的时代”张闳:《此致,敬礼!此致,那个敬礼!》,《天涯》1996年第3期。的“一代人”也不相信未来的“美丽新世界”“美丽新世界”的说法来自于新生代导演施润玖的同名电影《美丽新世界》。,最终选择恪守“我的摄影机不撒谎”的叙事伦理,近乎写实地呈现出自己的人生境遇,借助微观的“内部世界”(Interior)完成对破碎主体的经验性重构。可以说,新生代导演的文化身份一开始是被个人的主体性言说冲动和社会现实的互文书写所定义,他们的作品也因此与时代生活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三峡好人》虽然不一定是导演最优秀的作品,却是新生代影像与时代情感的互文关系结合得最好的一部。在这部不断被阐释的未完成的“可写的”文本中,导演的“叙事本文”、剧中人物的“行文本文”与作为故事背景的“历史本文”有机统一起来。
然而,在新生代电影作品频频进出于国际电影节之后,情势开始变得微妙起来。张元、王小帅和吴文光等人的作品在几个商业色彩不太浓厚的电影节(如荷兰鹿特丹、日本东京、法国南特和埃及开罗)上获得了最初的国际认可,然而这种认可却夹杂着来自不同利益团体的怀疑与竞相定义中国新生代导演文化身份的意愿。ZhangZhen,TheUrbanGeneration:ChineseCinemaandSocietyattheTurnofTheTwentyfirstCentury,DukeUniversityPress,2007,p.10.而正如学者张颐武所批评的那样,国际电影节造就了两个巨大的神话,首先,第一世界的电影节评委成为第三世界“艺术电影”的守护神;其次,跨国资本运作成为中国“艺术电影”获得救赎的唯一出路。参见张颐武:《后新时期中国电影:分裂的挑战》,《当代电影》1994年第5期。如果说,新生代导演进军国际电影节的出发点是寻求多元文化理解的自由度,如张元所言,“在国外参加电影节,我得到的一个感触就是他们的电影氛围更加宽容”程青松、黄鸥:《我的摄影机不撒谎》,页111。,那么接下来,新生代导演半推半就地默认了国际电影节对自己的命名与定义同样是张元,当他第一次参加南特电影节,组委会将张元与一位智利导演一起请到台上,介绍他是“独立导演”。张元自己当时听到之后的反应是“吓了我一大跳!”参见程青松、黄鸥:《我的摄影机不撒谎》,页117。。由此,某些新生代电影逐渐演变为“特供”某一类国际电影节消费的“可读的”文本。一部新生代电影辗转于多个国际电影节的经历,同时也是一个不断被国际视野改写的过程。这种改写有增有删。影片中的国际普适性内容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强化,反倒是国族奇观化身份在不断被“擦除”的过程中遭到扭曲和放大。从质的意义上看,新生代电影依然没有挣脱第五代电影文本国际旅行的宿命。唯一不同的是,第五代电影为所谓的“国际视野”提供了窥探历史奇观的窗口,而新生代导演则成为中国当下现实视觉奇观的代言者。“中国”作为一个被定型化了的“他者”,不过是从“历史”的陷阱跌入“现实”的陷阱。
如果说,早先处于“地下”状态的新生代导演尚且不自觉地受到来自国际影展的意识形态预期1993年当中方联络人告知丹麦鹿特丹电影节组织者,中国官方曾认可的唯一参赛者黄建新未能获准成行之时,对方一反常态地没有表述愤怒或抗议,相反轻松地表示:“我们已经得到了我们所需要的电影。”这部电影就是《北京杂种》,它不仅为张元赢得了第22届荷兰鹿特丹电影节“最有希望导演奖”,影片在1994年的第18届香港国际电影节上的瞩目也缘于此。但结果却产生了意味深长的错位:“许多观众,包括影评家登徒、杨孝文等,慕名观看这部在电影局惹了麻烦的影片,不免怀着捕捉其政治异己观点的心态,而当他们走出影院之时,却无法掩饰他们深深的失望。”以上分别参见戴锦华:《雾中风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页406;林勇:《“文革”后时代中国电影与全球文化》,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页155—156。,与这一群体彼时的客观生存处境不无关系,那么,“解禁”后新生代电影的国际营销策略应当对上述后殖民症候保持足够清醒的反思意识。不可否认,在全球化时代,国际电影节作为世界电影交易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世界电影创作的美学趋势具有引领作用,而且电影制作团队与发行体系的跨地域性已然成为国族电影未来的发展趋势。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新生代电影导演可以放弃对国际电影节的文化警醒。事实上,国际电影节鼓吹的“艺术电影”观念成型于上一世纪后半叶,强调以欧洲经典艺术为源头的跨文化交流。在“冷战”时期,中国电影几乎处于欧洲“艺术电影”观念的盲区。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社会现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也给致力于“艺术电影”创作的新生代导演以现实启示,即不能一味沿用定型化的个人风格与美学标准,反过来要与国际电影节的权力保持一定的游离。与此同时,目前国内数量有限的电影节也应当争取创造良好的电影交易平台,为新生代电影创作者尽可能提供更多的投资机会。但愿针对新生代电影被国际电影节“文化领养”的担忧仅仅只是笔者的杞人忧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