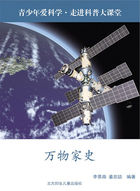不久,达尔文开始整理旅行期间所写的日记和采集的标本,并出版了具有科学价值的《航海旅行日记》。这一期间,他还在地质学会担任了3年秘书,不过最大的收获,莫过于收获了与爱玛的爱情。他一直爱着爱玛,爱玛也一直爱着他,只不过他一直没有意识到这点。在一个星期天的晚上,他和爱玛一起坐在客厅里,爱玛为他轻柔地演奏了几首莫扎特的浪漫曲。达尔文正式向爱玛求婚。他对爱玛说:"我最亲爱的爱玛,我一直是最喜欢你的。现在我明白了——请原谅我明白得太慢太迟,因为我好像生性如此——我爱你已经爱了很久。你愿意嫁给我吗?"爱玛毫不犹豫地回答:"我当然愿意了。我等待你求婚已有多年了,咱们两家的每个亲人都希望咱们能结婚。这你难道不知道吗?"看着达尔文什么都不知道的可怜样子,爱玛无声地哭了。当天晚上,他们向全家人宣布了这个喜讯,爱玛家的许多亲戚都被邀请了来,大家都激动万分,同时达尔文的父亲和姐姐也一直希望他们能够早点结婚,毕竟他们年龄都已经不小了。舅舅还跟达尔文谈起嫁妆问题,答应为他们的婚礼提供5000英磅。
1月29日,爱玛与达尔文正式举行婚礼,地点就在他的房子上边的那座小山上的教堂里。结婚那天,爱玛身穿灰绿色丝绸的结婚礼服,头戴十分漂亮的用薄木片编成的白帽,上面点缀着一些淡黄色的花朵,真是楚楚动人。教堂里气氛相当适宜,冬天的阳光透过彩色玻璃照进来,显得格外亮堂,主持婚礼的是教区牧师,他声音相当洪亮,小教堂里一直回荡着他的嗓音。
结婚后的达尔文住在伦敦,靠近地质学会以及地质学家赖尔的住处。爱玛很贤惠,把整个家布置得井井有条,达尔文沉浸在融洽和谐的婚姻生活中。他过了8天的蜜月生活,这段时间,他陪爱玛上街采购物品,在天气好时做长时间的散步或者去听音乐会。到了第9天,他从睡梦中惊醒,猛地从床上蹿下来,爱玛被他吵醒,惊讶地问发生了什么事。达尔文说,当他要开始工作时,总是这样起床的,这招他是从别人那里学来,他认为一旦侧过身睡一会儿,肯定又要睡着了。于是他走进书房,把门关上,然后一头扎进关于珊瑚岛的著述中去。爱玛则在10点钟招呼他去吃早饭,给他端上可口的饭菜。他们一边吃着,一边轻松地东拉西扯,直到11点钟他又投入工作。这段时间他每天集中精力工作5小时,闲暇时则走上一小段路去赖尔家去喝茶,他跟赖尔没完没了地谈论地质学,爱玛则跟赖尔的妻子玛丽谈论一些日常生活方面的问题。同时每个星期天早晨,不管天气好坏,他都要陪爱玛去一个不太远的教堂做礼拜,并听唱诗班唱诗,爱玛是个虔诚的教徒。就这样,他们生活稳定而有序,后来,爱玛认为住在伦敦社交应酬太多,不利于达尔文的科学研究和身体健康,便把全家移居到离伦敦20英里的乡间唐思,并且终生住在那里。爱玛不仅是一个体贴丈夫的好妻子,而且积极支持达尔文的科学研究,经常替他整理和抄写论文。
结婚后不久,他就集中精力对物种起源问题进行系统的探索,同时动手写笔记。为揭开物种起源的秘密,他首先从家养条件下的动植物着手。当时,英国畜牧业和园艺业发展很迅速,全国上下都在鼓励选种工作,以培养大批新品种。达尔文充分利用各种方式收集有关人工选择的资料,有时还亲自参加小麦、玉米等农作物培育以及家鸽杂交培育实验。由此他惊奇地发现,同种动植物,经过连续选育,造成的区别相当大,甚至超过那些公认异种的动植物间的区别。后来他得出"物种在人工的干预下是可以改变的"这一人工选择理论,因此他觉得各种特征明显不同的物种起源于同一祖先是可能的。为了寻找根据,了解自然界中是否也存在着类似于人工选择的物种进化,他查阅了大量资料,其中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对他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一理论声称,人口按几何级数成倍增加,而食物(动植物)按算术级数逐渐增加,最后必然产生人口过剩;过剩的人口,只好让贫穷、饥饿、疾病来消灭掉一部分,即通过生存斗争来解决。达尔文把这一理论推广到所有生物中去,于是发现了生物进化的规律:自然界的生物,普遍地具有变异的可能,当生活条件改变时,生物会在构造上、机能上、习惯上发生变异。有利于生产的变异经过生存竞争保留了下来。终于形成新类型物种。自然界的生物由于自然选择、适者生存逐渐由低到高、由简到繁地发展进化。由于对科学态度严谨,达尔文还对细胞学、胚胎学和古生物学最新成就进行了研究,以充实自己的理论,到1844年,他已将2年前写的提纲扩充到230页,从而非常完整地提出了后来包括在《物种起源》中的观点。1856年,他正式著述《物种起源》一书,这时从环球旅行归国已经研究整整20年了。1858年,另一位博物学家华莱士给他寄来了一篇论文请他审阅,论文中提到自下而上竞争的自然法则,与达尔文关于物种变化的观点相同。华莱士的文章是在马来群岛考察时,经过观察研究和结合史料独立完成的。他的文章使达尔文陷入苦恼中。虽然达尔文更早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结论也更成熟,但他怕引起华莱士的误会,多次想把自己的写作中断,后来在赖学和檬克的劝说下,才将自己的著作提纲与华莱士的论文同时发表。这就是华莱士事件。华莱士相当高兴,谦虚地把进化论的完成归于达尔文,称它为"达尔文学说"。
在朋友的鼓励支持下,达尔文把自己花20多年心血著成的《物种起源》正式出版,该书受到普遍欢迎,第1版1250册当天销售一空,此后,又出了6版,也被抢购殆尽,他的理论以令人信服的事实论证了物种的演变,从根本上推翻了神创论和物种不变论,在整个欧美大陆掀起轩然大波。
"牛津大辩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引起了宗教界的极大恐慌,许多人都责难、诬蔑他,包括他先前的一些好友与顾问,如在剑桥时带他出去考察的地质学家。与此同时,大学里的一些进步教师和青年学生也挺身而出,积极宣传和捍卫达尔文学说,对宗教势力的攻击展开了有力的回击。最有名的一次正面交锋,就是轰动一时的"牛津大辩论"。
"牛津大辩论"是由牛津大主教韦勃甫斯引起的,他事先经过策划,拉来了一帮狂热的宗教徒,在会上高喊"打倒达尔文",以壮声势。与他相对垒的是由赫胥黎领导的进步学者和青年学生,他们支持达尔文学说。双方人数加起来共达8000人。论战一开始,大主教就先跳上讲坛,歪曲《物种起源》的原理,公然恶毒地嘲笑达尔文和进化论,最后还恶狠狠地嘲讽赫胥黎:"试问,你自己是由你的祖父还是由你的祖母的猴群变来的?"听了这句刻薄话,神学界人士及狂热的宗教徒们纷纷叫好,一位信教的贵妇人甚至如癫如狂地喝彩。面对挑战,赫胥黎胸有成竹,他坚定明晰地阐述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指出这个理论不是什么猜想和捏造,而是科学真理。
他言辞雄辩,论据充足,与主教空洞乏味的攻击恰成鲜明的对比。针对大主教的嘲讽,他反唇相讥:"一个人没有任何理由因为他的祖先是猿猴而感到羞惭。我以为应该感到羞耻的,倒是那些惯于信口开河、不满足于自己活动范围内的可疑的成功而要粗暴地干涉他一窍不通的科学问题的人……"赫胥黎的发言赢得了与会者热烈的掌声,大主教则理屈词穷,瘫倒在坐位上,刚才为大主教喝彩的那位贵妇人竟当场晕倒,被人抬了出去。
"牛津大辩论"使达尔文精神大为振作,很多外行的人鉴于大主教的教训不敢再对进化论滥发言论和冷嘲热讽,使进化论得到进一步的捍卫和发展,影响逐渐深远。
达尔文在出版《物种起源》之后,继续观察、实验、研究,撰写了大量著作,如《攀援植物》、《人类的起源和性选择》、《人类和动物的表情》等巨著。这些著作许多都是他生病中坚持完成的。甚至在他临终前两天,他还支撑着垂危的病体,给暂时外出的儿子正在进行的一项植物试验作了观察与记录。1882年4月19日,达尔文逝世于唐思,终年73岁。在他死后,人们为了表示尊敬与纪念,将他安葬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国家公墓中,旁边是英国另一位伟大科学家牛顿的墓,予其一个自然科学家的最高荣誉。他以自己的成就树立了一座无形的丰碑,实践了他自己的一句话:"我曾不断地追随科学,并把我的一生都献给了科学。"生物进化论犹如一道惊雷划破长空,震醒了人们长期被宗教神学禁锢的思想,彻底推翻了上帝造物论和物种不变论。在生物学领域、思想界以及农业生产和园艺实践中都产生了划时代的巨大影响。人们把它同能量转化与守恒定律、细胞学说并称为19世纪的三大发现,达尔文因此而名垂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