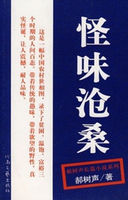张龙叹了口气:“你说几句软话,哄哄她吧。”
“还是你去吧。”老安把烟头扔在地上,用鞋底碾碎,“让她回来炒菜,咱哥俩喝两盅。”
张龙回家,走到吴爱云身边:“你也有不对的地方,怎么连饭都不做了?”
“你去哪儿吃的饭?”吴爱云看着张龙,“有人给你介绍对象了?”
“你胡扯什么?”张龙苦笑了一下,“我也不能天天跟你们两口子腻歪着啊。”
“我就要你天天跟我们腻歪着,”吴爱云把头埋进他怀里,搂着他的腰,“看不见你人影儿,我一分钟也活不下去。”
天阴得邪乎,黑云蘸了水,大巴掌似的从天上摁下来,矿工们黑蛆般在山坡煤洞口处,进进出出,蠕动不休。
吃午饭时,张龙拿着饭盒独自走到煤堆顶上坐下,煤洞周围的杂草两个月前还是青葱水嫩,娇滴滴的,现在绿火燃遍山坡,绿色也娇柔不复,变得泼辣,阴气十足。
矿工们在井口的木垛上分散坐着,抱着饭盒吃饭,话头儿三下两下又扯到女人身上。
“女人都一样。”
“那哪能?”
“有啥不能?不都是那一亩三分地儿。”
“可不是。”
“有啥不是?你们家吴爱云镶了金还是戴了银?”
“反正——”老安嘿嘿一笑,“区别可大了。”
“还区别?你区别过?”
“他没区别,吴爱云有。”
矿工们笑起来。
“放屁!”老安拉下脸来,“吴爱云真敢龇牙,我打不死她!”
“你打吴爱云?你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
“张龙——”老安扭头朝上面喊,“他们不相信我打了吴爱云。”
矿工们的头向日葵似的,全都仰了起来。
张龙盖上饭盒盖,往下斜睨了他们一眼:“我也不相信。”
“就你个熊样儿,”矿工们哄笑起来,有人把手里的半块馒头朝老安扔过去,“早晚把自己煮了,当供品供你们家吴爱云!”
老安对别人的话充耳不闻,他盯着张龙,目光像条毯子,一直铺到他跟前。
“嘴皮子磨够了吧?”工长看看表,招呼大家开工,“干活儿!”
张龙从煤堆上走下来,老安紧盯着他的眼睛:“你为什么不说实话?!”
张龙径自下了井,老安没跟上来。
张龙推了几趟煤,出来找老安,发现他已经不在了。
张龙回家时,吴爱云听见门响,从屋里出来,两只手沾满了面粉:“老安呢?”
“没回来?”张龙反问。
“看喷泉去了吧。”吴爱云看看身后,沾着面粉的手在张龙鼻子下面抹了两道,低声说,“给你包饺子呢,洗洗就过来吃吧。”
憋了一天的雨在他们吃饺子时下了起来,鞭子似的抽打着,仿佛十字街镇是个什么疙里疙瘩的脏东西,非得仔细冲刷清洗干净不行。
饺子吃完了老安也没回来,雨势倒是弱下来了。
“我找找他去。”
“死在外面才好呢。”吴爱云拉住张龙,“抱抱我。”
张龙用胳膊圈住吴爱云,被她在脸上拍了一巴掌。
“像饺子皮儿包饺子馅儿那样抱!”
后半夜的时候,雨停了一个多小时了,张龙听见隔壁大门门铃叮叮当当地响起来,老安在院子里面走动的声音,仿佛什么巨型动物撞了进来。
“吴爱云——”他声嘶力竭地叫,好像跟她隔着千山万水。
“大半夜你鬼哭狼嚎——”
噗的一声,吴爱云的话没了,被人吞掉了似的。
张龙从炕上弹起来,趿拉着鞋窜出门,隔着木板障墙,他看到老安手里握着一块砖头,脚底下躺着吴爱云。
张龙不知道老安喝的是什么酒,但这个酒显然跟往日不同,平常的酒像蚂蚁蚀骨,一口口,不只把老安的骨头啃成了渣子,他的目光、笑容、言语,也都被蛀得拿不成个儿;这个夜晚被老安喝下肚去的酒,是硬的、冷的,像把刀揣进了老安的身子。
“老虎不发威,”老安晃晃手里的砖头,斜睨着张龙,随着老安的笑容,刀刃的寒气从他的眼睛、嘴巴、脸上的皱纹,密密麻麻地扩散开来,“你们当我是病猫?!”
“你是不是男人?”吴爱云问,“是男人你现在就去宰了他!”
老安的砖头是对着吴爱云的脸拍下去的,她皮肤细嫩,脸颊处擦破了皮,这其实不算什么,皮肤下面的打击才是动真格儿的,几个小时之后,她的半边脸会肿成水蜜桃。
“哑巴了?怕了?”吴爱云盯着张龙,拂开他拿来的冷毛巾,“不用担心,你杀人,我偿命!”
“闭嘴!”张龙把手里的毛巾往地上一摔,他的心、肝、肺瞬间像烧红的煤块,把胸腔里面烘得热辣辣的,“你懂什么叫杀人?!什么叫偿命?!”
吴爱云怔住了。
“滚回家去吧!”张龙捡起毛巾,离老远朝洗脸盆里一掷,“你们两口子的事儿,我管不了!”
吴爱云把外衣的纽扣解开,她的手抖得厉害,纽扣解得很费力。
“你干什么?!”
“我检查检查自己,哪儿出毛病了,这么讨人厌。”吴爱云把衣服脱了下来,扔到地上,伸手去解胸罩后面的挂钩。
“抽什么风?让邻居看见——”张龙捡起衣服往她身上披,吴爱云在他的手底下挣扎着,把胸罩扯掉了,胸前白嫩的两坨弹跳出来。
张龙的火直窜上头,扬手给了她一个耳光。
“你打我?!”吴爱云泪水薄冰似的凝结在眼睛里,她的目光从冰后面射出来,“老安打我,你也打我?!”
“你不走我走!”张龙把衣服朝她身上一扔,推门出去。
老安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背倚着张龙家大门,嘴里咬着烟,但火柴盒在他手里变成块湿了水的肥皂。
张龙从他手里抢过火柴盒,擦出火花时,火光映照出老安的脸,皱缩得像个核桃。张龙把火直接塞到了老安的嘴里,他烫得跳了起来,噗噗、噗噗地吐个不停。
“好男不和女斗,”张龙盯着老安的眼睛,“有种你******找男人单挑啊。”
张龙把外衣往身上一搭,去十字街找了个烧烤摊,喝酒喝到半夜,然后去澡堂子洗澡,在那里找了个床睡了。
第二天张龙直接去了井口。
“衣服怎么没换?”工长叫了他一声,追到井口里面,“帽子呢?”
张龙抄起铁锹干活儿。
工头把安全帽硬塞给他。
老安随后也来了,他去“老马家的牛肉汤”吃的早饭,还喝了酒。他把这两样味道都带进了井下。
“想拉你一起去的。”老安冲张龙打招呼,他的笑容也仿佛经过长时间的炖煮,“一个人喝酒,就像一根筷子夹菜似的。”
张龙没吭声。
老安倒也没像张龙想的,跟其他矿工们吹嘘打老婆如何如何。他把支巷木的工人拉下来,自己站在木桩上面。
“你行吗?”那个矿工问他,“酒气比瓦斯味儿还大呢。”
“井底下的活儿,”老安笑起来,“我闭着眼睛都比你们干得好!”
张龙和往常一样在掌子面儿倒堆儿,到了吃午饭的钟点儿,他推完最后一手推车煤,正要上去,“兄弟——”
张龙停下了脚步。整个上午,老安就忙活那几根木桩子了,张龙不想搭理老安,但这会儿除了他也没别人了。
“你站远点儿,”老安站在木桩上,手里拎着把斧头,他指了指井口的方向,那儿有光透过来,“我想看着你的脸说话。”
张龙没动。
“你不敢站在光下面?!”
张龙走过去,竖井上面的光像束追光打在他的头上。
“你跟吴爱云,”老安有些哽咽,“以后好好过日子吧。”
“你说的什么屁话?!”
“你为我坐了20年的牢,别说老婆,”老安笑得脸上沟壑纵横,手里的斧头画着弧线抡起来,“我的命早就是你的。”
斧头砍下去的声音像深海处的涛声,黑暗如潮,迅疾扑上来,淹没了他们。
老安被救上来,得了什么寒症似的,刚立秋的节气,他把棉袄穿在身上还发抖。棉袄外面,他披麻戴孝。
吴爱云也披麻戴孝。她的脸颊肿胀消了不少,但青紫泛了出来,面相泛出股凄厉。她几天不吃不睡,瘦得脸颊都塌了,嘴角起了一片水泡。
张龙埋在西山下面的煤洞里面。矿主工长找老安商量了几次,尸体不是不能挖,一是成本太高,二是有没有这个必要。这些钱,还不如省下来给他父母妹妹。最后一次商谈前,矿主和工长替张龙算了一卦,卦上说,张龙已经入土为安了,再挖出来恐怕不吉利。
吴爱云冷笑了一声。
三个男人顿住话头儿,看向她,她推门出去了。
月亮当空,又大又圆。吴爱云的心也变成了月亮,虚白的一口井,没着没落儿。
老安夜里睡不踏实。两个月内,连着被埋了两次,他怕黑怕得厉害。
吴爱云半夜醒来,看见老安缩在墙角,用大棉被把自己包得像个馄饨。
“张龙在这儿。”老安盯着房间里面的暗黑,“我一睡着,他就来,就坐在炕边儿看着我,要么就站在那儿。”老安指指窗帘,“一站站半宿,也不说话。”
“来了好啊,”吴爱云笑了,“我去烫壶酒,炒几个菜,咱仨喝几盅。”
“祸水,”老安看着吴爱云,骂了一声,“女人都是祸水。”
“你们在井底下,”吴爱云盯着老安的眼睛,“发生了什么事儿?”
老安没吭声。
吴爱云拿起枕头砸过去。
“我们被埋在井底下,”老安把枕头甩到一边,“能发生什么事儿?!”
吴爱云僵住了:“这日子没法儿过了。”
他们替张龙卖了房子,加上抚恤金,一起寄给他父母。他们接到通知后,没来认尸。当年张龙坐牢的时候,他父亲就放过话:“就当没这个儿子。”
吴爱云离开的那天,新邻居正好搬进来。人声喧嚷,噼里啪啦放了两阵子鞭炮。
吴爱云只带走了自己的衣服,一个大提包就装下了。出门的时候,隔壁搬家的人都出去吃午饭了。大门外爆竹皮剖肠破肚地堆着,吴爱云往张龙院里面看,房门开着,黑洞洞的一张嘴,房门口同样堆着爆竹皮,一撮红色,像是房子咯出的血。
(原载《民族文学》2013年第3期)
透明
蒋一谈
这个男孩叫我爸爸,我不是他的亲爸爸。他这样叫我,希望我能像对待亲生儿子那样对待他,可是我现在做不到,不知道以后能不能做到。我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她今年五岁,和我前妻生活在一起。
男孩比我女儿大两个月,帮我点过烟、倒过茶,还帮我系过鞋带。我心里挺高兴,对他却亲近不起来。我对他说谢谢,他会摆摆手,说不客气。我在想,他以前也是这样对待爸爸的吗?我最终没有问他,还是找机会问问他的妈妈吧。
他的妈妈,也就是我现在的情人杜若,三年前和朋友一起创办了一家西式茶餐厅。我们在一次朋友聚会上相识,后来开始交往,彼此之间也有了好感。
一段时间之后,她主动向我表白,希望能生活在一起。可是我对婚姻生活有了恐惧。我的前妻曾这样评价我:“你不适合结婚,应该一个人生活,你还没有成熟。”
我知道女人需要什么样的成熟男人。我承认,我对现实生活有种恐惧和虚弱感,害怕去社会上闯荡,不愿意去竞争。每周总有那么一两天,我拿着公文包上班,走进地铁站,被潮水般的人流拥挤,恐惧和虚弱感会增强很多。
我每天按时上下班,在家里负责做饭、洗碗、打扫卫生。我喜欢待在家里上网、看书、看电视,不喜欢和朋友同事交往。我还是一名文学爱好者,喜欢写小说,写给自己,从不投稿。每到周末,我会带着女儿去公园或者图书馆。
我喜欢这样的家庭生活,平平淡淡的居家日子才能让我有踏实感和安全感。
有一点真实却又奇怪,我爱女儿,可是在女儿四岁大的时候,我才有做父亲的微弱感受。看着眼前这个小女孩,我的亲生女儿,她是真实的,可靠的,千真万确的,没有一丁点水分,可是对我而言,“父亲”这个身份,或者说这个词汇轻飘飘的,我伸手能抓住,又能看见它从我的指缝间飘出去。或许我还没有成熟吧。我希望自己成熟起来,坚强起来,但是这一天还没到,我第一次的婚姻生活就结束了。
我不怨恨前妻,一点都不。我知道问题所在,没有资格去抱怨她。我希望她离开我之后,不再怨恨我,忘了我。在她眼里,我在家里扮演一位丈夫和父亲的角色——我没有家庭的长远规划,没有自己的事业规划,没有女儿未来的成长规划。我承认这是事实。当她说我是一个胆怯的男人,没有生活的勇气时,我反驳过她。后来关于勇气的话题,我们之间又争吵过两次。每个人对勇气的理解不一样。我认为,这些年我在做一份自己不喜欢的工作,为了薪水工作,看上司的眼色工作,为了家庭生活工作,这本身就是我的勇气。或许她理解的男人勇气,就是能追着梦想去生活,即使头破血流也是好样的。我没有她需要的那种勇气和梦想,我梦想待在家里,可我没有经济能力去选择。
我对杜若的好感也源自这里。她理解并接受我平平淡淡的生活理念,对我的事业没有苛求。最重要的一点,她从未把话题转向婚姻层面,也没有探寻我的第一次婚史。她越是这样,我越是对她充满好感。她看过我的写作笔记,说我有写作天赋,应该试着去投稿。有一天,她对我说:“我爱我的儿子,希望你也能对他好。我们在一起生活,可以不结婚,你也可以不用上班,就在家里看看书、写写东西,照顾我们,我能养活你。你认可这个孩子,认可他叫你爸爸就可以了。”我点点头。杜若也没有给我多讲过去的生活经历,只说叮当的爸爸是她过去的情人,叮当从没见过他的爸爸。杜若对我很好,我能实实在在感知到。我知道,她希望我能把她对我的好,通过我的身体再传递给她的儿子。我希望自己能够做好。
离婚后我把房产留给了前妻,自己租了一套家具电器齐备的一居室。我接受了杜若的建议,提前解除了租房合约,然后辞职待在杜若的家里。每天早晨,我拿着菜篮子去早市买新鲜蔬菜、鸡鸭鱼肉,和卖菜的砍价,回家的路上和大爷大妈聊天,顺便帮他们抬抬重物。我翻看从书店买来的菜谱书籍,学会了二十几道新菜肴的做法,看着杜若和叮当有滋有味地吃饭,我心里很有成就感。我每天擦洗马桶两次,马桶和洗面盆一样洁净。杜若和叮当的衣服每天换一次,我洗好后熨好、叠好。我还买了最新型的樟脑丸,放在衣橱里。我发觉自己比以前更会学习了,站在镜子面前,我好像重新发现了自己的价值。我在想,如果前妻能够这样理解我、对待我,我不会主动提出离婚,而且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试图改变自己的性情和对待生活的心态,可是她没有体察到。
我们两个人只是被生活拖疲了,在现实面前妥协了,前妻对生活的忍受力超过我,是我首先选择了逃避,在离婚的问题上她没有太多的责任。
和杜若生活了几个月之后,我对自己还不太满意。叮当叫我爸爸,我脸上挂着笑,心里还是对他亲近不起来,不过他提什么要求我都会尽可能满足,比如他把我当马骑,在屋里爬来爬去;他还喜欢把脚丫子放在我脸上蹭来蹭去,那个时候,我会想到女儿的小脚丫。有一天晚上,我正在淋浴,叮当推门进来,非要和我一起洗澡。我想拒绝,却没有说出口。我背对叮当,叮当嘻嘻笑着,小手在我身上抓挠,我非常紧张,全身起了满满的鸡皮疙瘩。躺在床上的时候,杜若搂着我,说我真是个居家好男人,她很知足。我也第一次说出了心里话,我说:“我不是什么居家好男人,只是不想和社会多接触,我喜欢待在家里,待在一个感觉安全的空间里面。”杜若没有说话,只是紧紧地抱着我。
杜若对我身体的需求大于我对她身体的渴望,但我总是竭尽全力满足她。
杜若心思细密,体察到了我在家里的微妙尴尬。有一次,我听见她在客厅和儿子说话:“叮当,叔叔和妈妈生活在一起,他就是你的爸爸。妈妈说过,见到爸爸你要叫他,多叫他,你做得很好。今天,妈妈想对你说,以后不要叫得太勤,一天叫几声就可以了。”
“为什么?”
“爸爸有点害羞。”
“哈哈!哈哈!哈哈!”叮当大声笑起来。
“小点声,爸爸在睡午觉。”
“爸爸会害羞。”
“你喜欢他吗?”
“喜欢。”
“喜欢他什么?”
“喜欢他和我一起搭积木……喜欢他在地上爬让我骑……喜欢他……对了妈妈,他还说要带我去海洋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