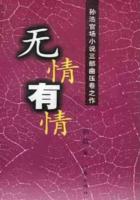在桑走后的第三个春天,一家大型刊物的编辑向我约稿,我考虑了一周后,决定将写给桑的信寄去发表。所有的读者和朋友都在问:“桑是谁?你们爱了多久?”我用平和的眼神环顾一下四周,然后笑笑:“不知道。”那棵老树依然在,似乎没怎么老,红丝带依然在,谁也无以了悟我的回答,包括我。
袁朗娶了那女孩,一年后,就离婚了,他给了那女人一笔钱。给桑的信发表的第一天,有一个电话,什么都没有说,足足沉默了十秒钟,挂了。但我知道,是他。我又打了过去,这是三年来,我第一次主动打电话给他。
袁朗,刚才是你吗?
是。
袁朗,水合老师现在好吗?你一直没有回答我。我不经意地问了一个遥远的问题。
他娶了那个维吾尔族姑娘,为此,他和父母的关系彻底崩裂了。他提议去沙漠走走,感受一下大漠风情,或许能找到一些创作灵感。我们便随同探险队进入沙漠,他们俩却莫名其妙地掉队了,我们几乎找遍了整个沙漠。他们神秘地失踪了。好几年过去了,再也没有出现。也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里?袁朗蹙起眉头,依旧满腹伤感地说。
他们失踪了?在沙漠里?我的脑海中立刻浮现出在沙漠里见到的那两具纠缠在一起的骨架,还有那个风化的画夹。天呵!是他们?我几乎惊叫出来。
你说什么?袁朗的声音明显紧张起来,他以为我又将变空。
哦,没什么。我赶紧说,我不愿向任何人再道出沙漠里埋藏的那个秘密,不愿让任何人去惊扰那两个相爱的人。
老谢依旧会抽空来看看我,和我那两个忠实的伙伴“望”和“风”。老谢每次道别都会说:“好好活着,我们活一天,就少一天。”
我说:“那我们就拼命多活一天吧。”
这个世界,有太多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也有太多令人肝肠寸断的情感,你想到远离。你为自己建筑一个王国,或者寻找另一个国度,也许,那只是一小片花园一小座古墓一小片森林和湖泊,也许,那是一间遮风避雨的小屋一个婴儿睡的摇篮一片沙漠一个孤岛。在那里,你永远都如一个面色红润、娇嫩的孩童,吃着天然鲜嫩的野果,顶着顽皮的小草帽,和着芬芳的泥土,一路跳着唱着循着,不懂忧伤,不懂衰老和死亡。你在明白:一种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