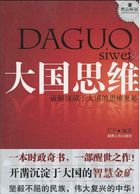(美)埃德加·斯诺
作者简介
埃德加·斯诺(1905-1972),美国新闻记者。出生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市,年轻时当过农民、铁路工人和印刷学徒。大学毕业以后,他开始从事新闻工作,在堪萨斯城的《星报》和纽约的《太阳报》上初露头角。往后他在开往外洋的货船上当了一名海员,历游中美洲,最后到了夏威夷,仍然为美国的一些报纸供稿。1928年,在中国大革命陷入低潮的时候,他来到了上海,担任《密勒氏评论报》的助理编辑,以后兼任纽约《太阳报》和伦敦《每日先驱报》的特约通讯员。1930年以后,他为采写新闻,访遍中国主要城市,包括东三省、内蒙古、台湾等地,以及日本、朝鲜等国。他在中国西南各省长时间奔波,徒步经过云南省西部,到达缅甸和印度,访问了甘地和其他印度革命领袖。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斯诺目睹了1932年的淞沪战争和1933年的热河战争。在这以后,他在北平燕京大学担任新闻系教授两年,同时学习中文。在这一时期,他认识了美国著名的进步新闻记者史沫特莱,还和鲁迅、宋庆龄以及一些中共地下党员有所接触。
1936年6月,在宋庆龄的联系与帮助下,斯诺与在上海行医的马海德医生冒着生命危险,经西安前往陕北苏区访问。在延安他和毛泽东进行了长谈,搜集了关于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手资料。然后长途跋涉,到边区各地采访。次年写成驰名全球的杰作《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抗日战争爆发后,斯诺担任英美报纸的驻华战地记者。1939年,他又一次到了延安,同毛泽东进行了谈话,并详细调查了根据地的政权组织等各方面的情况,又一次向全世界作了报道。1941年,他对皖南事变作了如实的报道,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打击,被迫离开中国。其主要著作有《远东前线》《被烧焦的大地》《为亚洲而战》《中国在抵抗》《复始之旅》《大河彼岸》《漫长的革命》等。
新中国成立后,斯诺曾先后三次来华进行访问。1970年10月,斯诺偕夫人一同访华,参加了我国国庆观礼,在天安门上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见。毛泽东与他进行了谈话,对后来的中美两个大国的接近产生了重要影响。
斯诺于1972年2月在日内瓦病逝。按照其遗嘱,斯诺的一部分骨灰安葬在北京大学校园内一个小花园中。他在遗嘱中写道:“我爱中国,我愿在死后把我的一部分留在那里,就像我活着时那样。”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是20世纪30年代采访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外国记者中的第一人。
事件背景
斯诺来到中国的几年里,耳闻到了许多关于“红色中国”的说法。1936年5月,斯诺到了上海宋庆龄的住所。宋庆龄接受了这位异国朋友的热切求助,通过设在外国友人艾黎处的秘密电台将他的愿望转达给了陕北。毛泽东作出决策,同意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延安作如实报道,并委托宋庆龄同时找一位高明的外国医生同来陕北,以改进根据地的医疗水平。回北平后约半月,埃德加·斯诺就收到了北平地下党徐冰送来的介绍信。1936年6月3日深夜,埃德加·斯诺登上了西去的火车,开始了他记者生涯中神秘的“红色中国”之行。按宋庆龄的叮嘱,斯诺到郑州下车,与美国同乡马海德医生会面,然后换乘直达西安的火车,到西安后入住南京招待所。
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受宋庆龄委托,乘火车自上海赶赴西安,以宋庆龄给他的半张名片,与斯诺身上的半张拼对相符,接上了关系。随行的王牧师随即约见名为西北“剿总”副司令的张学良将军的秘书、实为中共派驻东北军内的联络员刘鼎,请刘鼎随即电告中共中央,外国客人已到西安,望尽快派人来西安接应。第二天,王牧师出现在西安金家巷1号张学良的公馆。他从上海出发时,宋庆龄就交代“此事可向汉卿求助”。随即他向张学良说明来意,转达了宋庆龄的话。两人商定,由少帅出具特别通行证,调拨一辆东北军内的“道奇”卡车,护送埃德加·斯诺和马海德医生北上,途经东北军的防区,直到国统区的最前沿城市肤施(即今延安)。
在接到刘鼎“外国友人已到西安”的电报后,毛泽东亲自指示对外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即派邓发尽快前往西安接应。邓发来到西安后,由王牧师领着见了埃德加·斯诺和马海德医生,转达了中共中央对他们的欢迎,并随即告知了他们要北去的路线,说明一路上应该怎样走。斯诺和马海德医生从西安出发,因有张学良签发的特别通行证护驾,又有刘鼎秘书陪同及邓发引路,一路畅通无阻,连例行的检查都被免去。第二天下午,到达国统区边缘的肤施城,住在一个东北军团长的家里,休息了一晚上。次日早上起床后,吃过饭,刘鼎把他们送出城门外,由事先安排好的骡夫将他们送到了红区边上的一个小村庄,由村庄里的贫农协会主席刘龙火接待他们,把他们安排到村公所休息。不一会儿,村里来了很多人,争相看外国友人,男女老幼七嘴八舌地问这问那,胆子大一些的人,随手摸着客人的照相机、手电筒、皮鞋等,对客人身着的咔叽布上衣的拉链赞不绝口。一位大婶兴高采烈地端来香喷喷的小米饭、炒鸡蛋、煮白菜和烤猪肉。斯诺他们吃过饭后,整理了随身携带的东西,在刘龙火指派的向导带领下,向陕北安塞县进发。在我中央红军通讯部队一班人护送下,他们一路安全到达中共中央临时所在地陕北保安县。当地军民与老百姓得知消息,倾巢而出欢迎新来的外国客人。除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亲自接见外,中共中央还专门召开了“欢迎国际友人大会”,表示对埃德加·斯诺、马海德这两位国际友人的热情欢迎。埃德加·斯诺在大会上激动地说:“自己享受国宾般的待遇,一生中还是第一次,荣幸之至!”
此后,埃德加·斯诺开始了他“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采访工作,随后写出了令世界震惊的名著,陕北红都采访录---《红星照耀中国》。在出版中译文本时,为防国统区查禁,以利发行传播,改名为《西行漫记》。从此后,斯诺的名字深深地印在了中国人民的心中。
报道原文
……
1936年6月,我听到了中国西北出现了使人惊讶的政治局面的消息。在西安府指挥“剿总”的张学良元帅,与共产党达成秘密的停战协议。一位朋友告诉我,在他的帮助下,有可能到陕北和甘肃省去旅行一次,当时红军主力正由全国各地向那里集中。
……
一天午夜,乘上了一列破旧不堪的火车,去“红色中国”。我离开北平,身上只带一封用密写墨水写的致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的介绍信。这个人的头颅里装着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脑,是蒋介石悬赏二十五万元银洋不论死活都要缉拿的人物。第二天早晨,我观察一下我的旅伴,看见对面坐着一个青年和一个面目端正,留着一绺花白胡子的老人。那个青年要回四川老家去。据说他家乡附近有土匪在活动。
“你是说红军吗?”
“哦,不,不是红军,虽然四川也有红军。我是说土匪。”
“可是红军不就是土匪吗?”我出于好奇心问他,“报纸上总是把他们称为赤匪或共匪的。”
“啊,可是你一定知道,报纸编辑不能不把他们称做土匪,因为南京命令他们这样做。”他解释说,“他们要是用共产党或革命者的称呼,那就证明他们自己也是共产党了。”
“但是在四川,大家害怕红军不是像害怕土匪一样吗?”
“有钱人是怕他们的。地主、做官的和收税的,都是怕的。可是农民并不怕他们。有时候他们还欢迎他们呢。”
那老人坐在那里留心地听着,却又显得并不在听的样子。
“你知道,”他接着说,“农民太无知了。他们以为红军说话是当真的。我父亲写信给我,说红军在四川取缔了高利贷和鸦片,重新分配土地。所以,你看,他们并不完全是土匪。他们有主义,这没有问题。但是他们是坏人。他们杀人太多了。”
这时,那花白胡子忽然抬起他那温和的脸孔,十分心平气和地说出一句惊人的话来:“杀得不够!”我们两人听了都不禁目瞪口呆地望着他。不巧,我得在那里换乘陇海路的车,因而不得不中断讨论。可是从那时起,我心里一直在纳闷,这位模样儒雅的老先生有什么确凿的证据来支持他那骇人听闻的观点呢。火车终于开进西安府新建的漂亮车站,我却整天都在纳闷这件事。
……
在旅馆外面有一辆挂着窗帘的汽车等候着我们,我看到车里坐着一位戴墨镜,身穿国民党军官服装的人。我们驱车前往汉朝的汉武帝“君临天下”的旧皇宫的金銮宝殿。这个国民党官员坐在汽车里一言不发。他取下墨镜,摘掉白帽,青铜色的脸上露出了恶作剧的笑容,你一眼就可以看出,他并不是个坐办公室的官僚,而是个常在户外活动的人。
他把脸凑近我,向我眨着眼。“瞧瞧我!”他低声说,好像一个有什么秘密的孩子一样高兴。
“瞧瞧我!瞧瞧我!你认出我来了吗?我以为你可能在什么地方见过我的照片。”他说,“我是邓发。”他的脑袋一仰,看着我对这个炸弹的反应。邓发?哦,邓发是中国共产党秘密警察的头子!邓发对目前这样的情况感到好玩。他看到我这个自告奋勇到“匪”区去的美国人感到很高兴。我要他的马吗?啊,他的马好极了,红色中国最好的马!我要他的照片和日记吗?他会带信到仍在苏区的妻子,把这一切都给我。他后来真的没有食言。
邓发是香港海员大罢工的一个领导人。他接着就成了共产党员,进了黄埔军校,参加了国民革命。1927年以后到江西参加了红军。“你不怕丢掉脑袋吗?”我们坐车回城时,我问他。“不比张学良更怕,”他笑道,“我同他住在一起。”
我们在黎明之前离开西安府,那一度是“金城汤池”的高大的木头城门在我们的军事通行证魔力前面霍地打了开来,拖着门上的链条铛铛作响。在半明半暗的晨光中,军用大卡车隆隆驶过飞机场,当时每天都有飞机从那个机场起飞,到红军防线上空去侦察和轰炸。在那条新修的汽车路上,沿途的罂粟摇摆着肿涨的脑袋,等待收割。新修的路面经过水冲车压,到处是深沟浅辙,因而我们那部载重六吨的卡车,有时也甚至无法通行。这一令人惊叹的黄土地带,雨量充分的时候异常肥沃,因为这种黄土提供了无穷无尽的、有几十英尺深的多孔表土层。地质学家认为,这种黄土是有机物质,是许多世纪以来被中亚细亚的大风从蒙古、从西方吹过来的。
我如愿以偿,安然通过最后一个岗哨,进入无人地带---我要是如实地把这一经历叙述出来,就可能给那些帮助我前去的国民党方面的人造成严重困难。现在我只消说,我的经历再次证明,在中国,只要照中国的方式去办,任何事情都可能办到。
……
周恩来是我穿过红军防线后遇见的第一个共产党重要领导人。他在延安以北的一个窑洞小村里指挥东路红军。我刚刚走进营房,一个身穿旧棉制服的瘦长的人出来见我,把他穿着布鞋的双脚一并,把手举到他那顶褪了色的红星帽檐边,表示敬礼。他用浓眉下面的一双乌黑的大眼睛细细地打量了我一番。他的脸上蓄着茂密的胡子,一笑就露出洁白的牙齿。
“哈啰,你想找什么人吗?”他说,“我是这里的指挥员。”他是用英语讲的。“我叫周恩来。”
“我接到报告,说你是一个可靠的新闻记者,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并且说可以信任你会如实报道。”周恩来说。
“我们知道这一些就够了。你不是共产主义者,这对于我们是没有关系的。任何一个新闻记者要来苏区访问,我们都欢迎。不许新闻记者到苏区来的,不是我们,是国民党。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要给你一切帮助考察苏区。”他告诉我,红军想要结束内战,与国民党联合抗日。这并不意味着放弃革命。他说这样做是推动革命。他声称:“抗日战争的第一天就是蒋介石走向末路的开始。”
第一次访问结束前,周恩来在他的手绘地图上动手替我起草旅程,并注明我在每个地方会见的人名和机构名称。这个旅程一共九十二天(步行和骑马),事后证明这是低估了。然后他送我出来,我在一队红军战士的陪同下,到保安访问三天,我在那里要会见毛泽东。
……
我到保安后不久,就见到了毛泽东,他是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他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甚至在说到自己的时候和苏维埃的缺点的时候也笑得厉害。他说话平易,生活俭朴。他把天真质朴的好奇品质同锐利的机智和老练的世故结合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