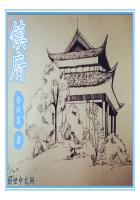三个小孩在桌子后面瞪着眼睛,聆听着外面的动静,阳光从小型的天窗透进来,比起外面的明媚,屋里显得格外黑。爷爷蹲在三个小孩旁边静观其变,老伴儿出去一会儿了,而街上的慌乱的跑步声和叫喊声也渐渐低了下去,相比早些时候,现在显得相当安静,但哗啦啦房屋倒塌的声音预示着严重的不祥,而上方有什么大型动物正在靠近。他思索着会是什么动物不走地上,专走人家房子,他想到的只有壁虎,如果是壁虎,该有多大呀。
小水感受着周围的气息,她本能地认为危险来自她的天敌,她的心扑通扑通跳起来,源自害怕,更来自跃跃欲试的兴奋,她的手心因为紧张冒出很多汗来,而指端如有很多小虫蠕动般痒痒的。随着噗咚一声巨响,有什么东西撞破青瓦落了进来,三个小孩看去,那是一条腿,悬在半空中挥动着又被抽了出去。又是一声更大的巨响,屋瓦哗啦啦掉落下来,荡起的浓厚的灰尘。然后他们的面前突然出现一座山,扁平的小山,就像面前的地表突然升高一样,倾盆而下阳光照在它身上,鲜红的小山折射出一片很漂亮的红光,照在几个人脸上。他们都没看清发生了什么。然后小山被抬起,下面出现四根柱子,小山开始移动,蹭着一片废墟,突然有根柱子猛地戳向桌子这边,将桌子像投掷一个玩具一样从几人头顶扔了出去,探过头来。爷爷吓得将三个小孩护在自己的臂膀下,露出视死如归的表情。小水抽出自己的右臂,照着来回摸索的柱子打下去,她的食指尖水流如注,但被小凡及时抓住了,脱落的水滴躲过柱子滴到爷爷的袖子和地上。
“毛小梳,你看,我就说不对,本体...本体...本体怎么会出现?”这个突如其来的意外让琴音很担心,她不确定小水能否应付得来,因此而结巴起来。
“别担心,别担心”毛小梳端着咖啡,离开弯月状的办公桌,走到角落里,避开落地玻璃墙外的同事的目光,“53区45号...红色接近8度,oh,god,GFL相当高...”正在讲的过程中,琴音突然说了声“住嘴”,他便停下了。
“不是说你,我家牛冲我叫,最近可能感染什么菌了。你也别说那么多,现在小水应付得来吗?”
“有点危险,没有判断清楚状况...”
“住嘴!怎么办?怎么办?”
“冷静点,最好远离危险。”
“我冷静一下。”琴音捏下耳垂,随即又捏一下继续通话,“就算小水暂时没事,但本体小水怎么对付的了……”
“不要连续通话两次,很容易被暴露。”
“又一个村庄要遭殃了…小凡可以吗?你觉得?”
“小水用了我们很多心血,我们已经考虑的足够周全,她有无穷的潜力,相信她,也相信我们自己。”毛小梳,20出头,除热衷脑科学外,还出任某公司高级顾问,空闲时去那里溜达两圈。他外表看起来还只是一个孩子,但此刻如一名智慧的老者般说。
“小水,目前你还不能应对这个大家火,不到迫不得已,不可以动手,知道吗?”虽然刚才情绪激动,但对小水,她保持着缓和的语气,如果她都火急火燎,小水更按耐不住了。
“那什么时候是迫不得已呢?”小水问。
几人齐刷刷看向她。
爷爷紧张地做了个嘘的手势。
“你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
“那小凡、牛牛...”小水压低了声音。
没等小水说完,爷爷直接用大手掌捂住了她的嘴。
琴音沉默了,她自然不希望小水拿自己的性命换取“无关紧要”的人的性命,但却不能够这样讲,她思索了一下,说:“妈妈希望你要记住,任何时候你都要保护好自己。”
小水不能说话,便重重点了点头。
巨蛛爬了过去,火盆中的炭被拖了一地,火苗奄奄一息。它听到了声音,但此刻对此不懈,它的网络完成后,这些人便都是它的玩物。
中午时分,春禾躺在木屋前晒太阳——现在他已经适应了沙漠的气候,况且前两天这里还有一场降雪,又出来的太阳很是温暖。远处有人走动的声音让他不得不坐起来。他眯着眼睛看去,发现又是一个戴毡皮帽的中年人,比之前那个人胖不少,矮一点,老一点。他看到春禾,辨别了一会儿,快走上前来,二话不说,揪住春禾的耳朵:“啪咕噜嘟啪哇唏嗨呦啊?!”(臭小子,来了就不走了。”
“你谁呀?揪我耳朵干嘛?你丫有病,小草、小草。”屋内正在休息的小草扑腾着翅膀飞过来,因为紧张飞的不平衡,飘上跌下的。小草使劲拍打着草草蝶的窝们,很快草草蝶破门而出,扑腾腾飞扑在矮胖的中年人身上。
中年人一下松开了手,被动退后了很远。“囌嘞嘚嘿咆呦(快叫它们停手)中年人大叫,“舞狮吾塔(我是你爸爸)。”
春禾觉得这人的发音跟他的样貌一样无法忍受,“你丫叽里咕噜的说什么呢?哪个星球的?不会说地球话呀?”
“啪咕噜嘟,吾塔咵嘀呦呞呗?!(臭小子,你连老爸都不认识了?)。”
春禾觉得这个“是”的发音其实更像三声那个字,嫌恶心,换了个字翻译。
“小草。”春禾叫了一声,觉得这个鬼哭狼嚎的人可能是个流浪汉,叫停了小草。草草蝶齐齐飞回春禾身边,火红的一片非常壮观,“给他一些蜂蜜赶紧送走吧。”春禾说,然后到屋里,从木杯里很大方的挖出一大勺扣在一个破瓦片中,把瓦片放在坐在地上哭丧着脸的矮胖中年人面前。谁知矮胖中年人两腿一蹬倒在滚热的沙土中。“饿成这样子啊,小草先抬我屋里吧。”草草蝶刚一飞动,中年人又坐了起来,“热出喂他啪,是该努哈。”中午时分,春禾躺在木屋前晒太阳——现在他已经适应了沙漠的气候,况且前两天这里还有一场降雪,又出来的太阳很是温暖。远处有人走动的声音让他不得不坐起来。他眯着眼睛看去,发现又是一个戴毡皮帽的中年人,比之前那个人胖不少,矮一点,看上去比之前那个年轻。他看到春禾,辨别了一会儿,快步走上前来,二话不说,揪住春禾的耳朵:“啪咕噜度,帕瓦西嗨呦啊?!”(臭小子,来了就不走了。”“你谁呀?揪我耳朵干嘛?你丫有病,小草、小草。”屋内正在休息的小草扑腾着翅膀飞过来,因为紧张飞的不平衡,飘上跌下的。小草使劲拍打着草草蝶的窝们,很快草草蝶破门而出,扑腾腾飞扑在矮胖的中年人身上。中年人一下松开了手,被动退后了很远。“输了的黑袍有。”(快叫他们停手)中年人大叫到,春禾觉得还是这样翻译比较简单,“舞狮吾塔。”(我是你爸爸)“你丫叽里咕噜的说什么呢?哪个星球的?不会说地球话呀?”“啪咕噜度,吾塔夸地有事呗?!”(臭小子,你连老爸都不认识了?)春禾觉得这个“是”的发音其实更像三声那个字,嫌恶心,换了个字翻译。“小草。”春禾叫了一声,觉得这个鬼哭狼嚎的人可能是个流浪汉,叫停了小草。草草蝶齐齐飞回春禾身边,火红的一片非常壮观,“给他一些蜂蜜赶紧走吧。”春禾说,然后到屋里,从木杯里很大方的挖出一大勺扣在一个破瓦片中,把瓦片放在坐在地上哭丧着脸的矮胖中年人面前。谁知矮胖中年人两腿一蹬倒在滚热的沙土中。“饿成这样子啊,小草先把抬我屋里吧。”草草蝶刚一飞动,中年人又坐了起来,“热出喂他啪,是该努哈(下来一趟,忘根了)。”
春禾发现找个象声字太难了,于是想象着更简单的字。
那人又面红耳赤得咕哝一句,“假哇呀,夸舞么费噢(我还会回来的,你是我儿子)。”
“莫名其妙”春禾看着那个走路像老太太但很快的人,皱了皱眉头,觉得眼熟,但想不起来,自己走了这么多地,见过也不为怪,但没印象,应该不是什么重要的人,于是等他走远后,继续躺下晒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