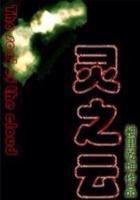十分钟后,童越已经走进了大厦的电梯,正是上班高峰期,他像一个可怜的三明治一样挤进了那个已经布满十几个脑袋的狭小的空间里。
而早晨那个本该让人心情阴翳的梦已经从他的意识里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上班会不会迟到会不会被扣掉三十块的担心。
童越已经习惯了那个梦。因为从他有意识开始,那个梦就已经不时在他睡觉的时候倾扰他,它就像热带雨林的大蟒蛇一直缠绕着他,这个梦的后半段是:
那些像石头一样的人影朝童越走来,如同饥饿的蚂蚁走向他们的巢穴。他们走路的姿势很怪异,像一只只浮在水上的浮萍,顺着流水晃晃悠悠地漂了过来。
这时候,童越通常已经醒来,毫无置疑,是被吓醒的,那些人大多长得歪瓜裂枣,或者缺胳膊少腿,他们的嘴里原来在小声地念叨着什么,就像在对童越集体进行着一场诡异的诅咒……从小学到初中,从初中到高中,从高中到大学,从大学到童越现在在一家公司实习,到了后来甚至连他自己都已经麻木,他已经不再对梦里的场景感觉害怕,他甚至会随着自己的视觉细心地观察梦里的情景,那些人的身材,姿势,还有那些人身后那些像干枯的手指一样的树枝,他甚至很期待他们走近他,这样,他就可以和他们聊上几句,但是每次他都失败,因为在他们的脸靠近他的时候,他总会醒来,那个故事,或者说是他自己,就像一个被阉割的太监,下面空荡荡的,很不爽。
被阉割的梦境。呵呵,这个比喻很不错,非常适合。童越自嘲地笑了一声。
叮!该死的电梯,在这个时候总是像犯了腿病的老太太,每走几步就要停一下,真不明白它的胃口有多大,为什么停了这么多层,进来那么多人它还没吃饱。
在电梯门开开合合的过程中,童越见到很多陌生的面孔,有大人,有小孩,有亚洲人,当然也有欧洲人,美洲人——这并不奇怪,这幢大厦的裙楼共六层,是一家五星级的酒店,市里有交易会什么的活动时,不少客人会选择住在这里。所以,就算是忽然多了一位自称是来自卢森堡的客人,也不必大惊小怪。所以,平时他肯定连瞄都不会特别瞄一眼,但这一次,他有些激动,因为他们的进进出出让他的全勤奖就要泡汤了。
进来的是一个美国人,一身笔挺的黑色西服,深邃的五官,高挺的鹰钩鼻,白皙的皮肤,高大魁梧得让男人妒忌让女人心神荡漾的身材。唯一让人感觉不爽的,是他们身上总是带着一股怪味,童越以前还以为那是他们身上原有的味道,后来才知道是古龙香水的味道,他们因为体味太重所以喜欢把古龙水往自己的身上洒,结果欲盖弥彰。
看看表,童越松了一口气,离8:30分还有2分钟,时间足够——他上班的公司跟他住的地方是在同一幢大厦的,只要乘电梯往下走20层就可以了。定了定神,他整了整雪白的衬衫的衣领——这该死的衬衫,童越从学校出来最不适应的就是它挺括的领子,它总让他的脖子很不舒服,让他感觉透不过气来。
显示楼层的红色数字在一个一个地往下递减,在变到第14楼的时候,童越整理衣领的动作停住了,因为他看见一个身影,瘦而小,有些单薄,他的心咯噔一跳,随即纠结起来,想喊,却因为紧张喉咙被什么哽住似的,发不了声。
小年!在电梯门关闭的最后一秒钟,他终于让那两个字蹦出喉咙。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