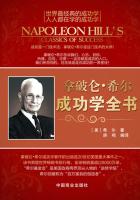班主任的高跟鞋依旧,一路咚咚到了讲台,面带微笑地开讲:今天这节班会课呢,我们就把新座位排一下,现在我念一念我的安排,如果对我安排有意见的可以找我,第一次排位置我尽量尊重你们的意见,但是……她话锋一转,语气也随之变得严厉:要是谁被我发现上课的时候讲话,我随时有权利让你坐最后面,不管是谁,一视同仁!
其实我对这种的一视同仁完全不感冒。脑子好使一点的都知道,老师心里的天平会不自觉的倒向成绩表单靠前的那些名字。嗯,很荣幸,从小到大我都是属于被特殊照顾的那类,我觉得接下来的这三年也大致不会变。
第一排,余阳,于洋,诶?老师想了想又说:不对不对,应该是余大,于二,然后是何璐,文超……
原来这座位完全就是按成绩一路排下来的,要是说在之前老师在我心里的形象还只是讨厌,那么现在就真的算是一文不值了。
嗨!于洋把她的桌子拖到了一组一位说:你好啊余二傻。
这明摆着是要抢座位啊,为了个外号值得么,心里虽是这么想,但我还是憋着了:你好啊!于大哈,我微笑着挥手问好。
然后,接下来几堂课就把我累的够呛……
诶,你头长那么大干嘛,挡着我看黑板了……
诶呀,那边黑板反光看不见,你给我念念那公式是怎么写的……
烦死了烦死了,这连黑板都看不到,怎么听讲啊……
……
闹腾了一个上午,她似乎也知道了这样的抱怨只会换来我一个又一个白眼,于是,下午上课的时候她就开始扯我的笔记,翻我的书了……
笔记拿来我看看!她厚颜无耻的第十一次拿我的笔记本。
啪的一声,我一手镇住了正滑向她的我的笔记本。
你们两个在干嘛?数学张老师瞪着眼看着我们:课都差不多上了半节了,一直在搞,没完没了了是不是。
她这才有所收敛,小心翼翼的推过来一张小纸条:被抓到了怎么办?
没事没事,张老师还是很好说话的。我想安慰她,但这也是事实,起码在我看起来张老师还是挺和蔼可亲的。
可亲个屁,她好像又忘了这里是课堂,抓着我略显丰满的脸上捏啊捏。
于洋你给我站出去!
被吓的不轻的我也跟着她一起灰溜溜的站了出去。
擦肩而过的瞬间,我捕捉到张老师脸上的一丝疑惑。我当时被吓到没敢多想,弄得我好几个月都不好意思去粘着他问问题。
我们俩接到传指,蒋老师请喝茶。我们俩哪敢懈怠,一路琢磨着措辞就往办公室赶。
办公室里,班主任蒋金毛笑眯眯的在跟一家子谈着什么。蒋金毛我们给爱烫黄卷头班主任的爱称,爱称俩字得打个引号。
于是我俩小心翼翼的挤在门口,看着一个个考试不及格的好学生们面色阴暗的进进出出……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还真是不错,刚刚还和蔼的金毛老师在说笑着送走那对家长之后,立马面色铁青得如包公审案,翻脸比翻书还快的这个真理在她的脸上展现得淋漓精致。
都知道是什么原因吧,从老师这平静的语气看得出来,老师把肚子里的那些粗陋的话都憋在了心里,只是低声地叹了口气:你们心里应该都清楚,自己在班级,甚至是学校里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位,你们两个在我心里是掌中宝知道么?上课还打打闹闹……
我已经记不太清那次谈话有多么深刻,只是在出门的那一刻起,我们和班主任的关系,从严苛的师生关系,变到了能够一起打闹的队友。
为了防止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班主任把我的位置调到了八组一位,让原来只有六排的第八组扩充到了七排,让一个有五十四个人的教室变得整齐精神了不少。
我以为我还不算最惨,起码还有她也跟我一样过着没有同桌的生活,然而我还是太天真,下午的化学课,班主任像踩着云一样飘到了讲台:
有请我们的新同学做自我介绍。
掌声啪啪啪的响起来,一个身着校服的女生走上了讲台:大家好,我叫廖林婧,不是安静的静,是女青婧。说完还把婧字大大的写在了黑板上,整个动作做得大气而又不失风度。
按常理来说,这个时候我应该是在埋头做推断书或者望着窗外发呆的。这次我没有不但没有那样,反而还仔仔细细的听完了她说的每一个字。因为她的声音让我想起了儿时的一个玩伴……
放学路上,我特意把准备回寝室的玲童和舞动在球场的泽西叫到一起。
你有没有觉得新来的那个特别像一个人?我说。
你把我叫着回家就是为了这个?泽西一整脸的不乐意:像谁啊,蔡依林么?
不,声音,还是童玲懂我:声音像可可。
可可?泽西一脸懵逼:洛可可?
我们俩瞟了他一眼,默契的选择冷落他……
可可那个可怜的姑娘,从小在孤儿院长大,他貌似是有点过意不去,开始回忆起来:不过也是挺羡慕她的,一路努力考到了我们初中,还得到了好心人的资助,不过最重要的,还是她遇到了我们。
其实这个新同学也不容易,在她初二的时候失忆过一场,在她之前的事情全给忘得一干二净,只知道醒来的时候是在躺医院的病床上。童玲说。
你怎么会知道这么多?
她被安排的我们寝室,趁她出门的时候,寝室里的聂子蓉偷偷翻她的日记本看到的。
聂子蓉我认识,就是那个肥嘟嘟还任性的妹子,那天下午还被我的球砸的不轻。泽西哈哈的笑道。
你还好意思说,搞得那天晚上我们寝室的姐妹们都没睡着……
我有些感叹,感叹他们能这么快的融入着里而自己却连室友的名字还叫不出来,别看我表面上表现的那么平易近人,内心里对陌生的友好却处处设防。我有时候真的特别感谢他们俩,还有其他的儿时的玩伴们,感谢他们能有一种不畏一切的跟我站在一起的豪迈情怀。但我的朋友圈子似乎仅限于此,他们都说是我懒,也许我真的是懒吧,懒得再在复杂的人堆里寻找更合自己胃口的家伙,懒得再去花大把的时候去培养感情。一直都是孤独而高傲的生活着,简单,但也很乏味。
喂,在想什么呢?童玲看我好像有点不对劲。
肯定在想那个妹子啦,长的那么正,肯定是阳哥的菜。强行添油加醋的泽西。
没,我在想可可。我没太老实,只是不想再接泽西的话题聊下去。
自从那次事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她了,泽西收起了脸上的春光,气氛也变得些许沉重:去了趟医院就举家蒸发了,连最后一眼逗没有看到。
童玲,她出事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到的时候只有你在她身边。我问童玲。
所以你还是在怀疑我?怀疑我害了她?
没有,我还是那句话,我只是想知道真相。
我不知道!
……
停停停,泽西用宽大的胸怀挡住我们:都是高中生了,怎么还跟以前一样,动不动就吵……
每每面对关于可可的话题,我和童玲那种亲如兄妹的信任总会土崩瓦解。也许是可可真的对我们很重要吧。
我以前确实怀疑过童玲,因为在可可出事的时候只有童玲一人,而且每每问到她的时候却总是遮遮掩掩。重新让我信任她,很简单,当我想清楚童玲没有任何的动机去做有损可可的事的时候,我顿时释然了。只是一年多过去了,我依旧还是不知道真相,真相依旧被她压在心底,用一句我不知道来作为条件反射。
每个人都不容易,我们有时候还是看好自己的路吧,别人的很多事,我们都无能为力。童玲发话了。
是啊,每个人都不容易啊!
可可,希望你在世界的某个角落,前程似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