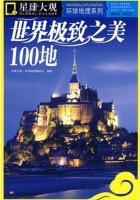这闹闹腾腾的人生。这不断冒着热气的人生。这处处透着薄凉的人生。每一个人,都在各自的舞台上,依依呀呀地唱着、舞着,甩着长袖,都试图弄出一些声响。只是这声响,有的人听到了,关注了,声响,就成其为声响;有的人闭着耳朵,望向窗外,台上的人弄出再大的声响,也白白弄出了。每一个舞台上的人,都在想,我是要弄出一些声响的。声响,带给人的或许是一层光环,或许是更深重的灰头土脸。所有的声响,到最后,一一地,都要落幕。像是这世界上从不曾有过声响。有些人的声响,在世时,可以隐隐约约地听到,或许明明白白地听到,比如毕加索。毕加索在世时即亲眼看到自己的作品被收藏进卢浮宫;有些人,却在死后千年,才得以被人弹奏。
一壶闲情
“一壶闲情”,是茶叶盒子上印的。也有的是“清风玉露”、“一壶天下”。都是些好听的话,就像是带着露水去采茶的二八女子一样,清新曼妙。这都是厂家为更好地销售他们的茶叶,打出他们的品牌,而精心挑选的。不是写在水上的,也不是写在月光中的,更不是写在梦中的,却让人有这样的感觉。读着这句子,便让人感觉云里雾里的美好,朦胧。我喜欢这些字。我喜欢这些字里面裹着的清香。我喜欢清香的背后鸟鸣的气息,兰花的气息,露水的气息,云雾的气息。它们,总是轻易地便将我俘虏,让我溃不成军。
在茶叶的气息里,我只能沦陷。
有时,我会恍然感觉,我是茶叶的女儿。我身上,是木质的气息,茶叶的气息,怎么掸也掸不掉的。
年少的时候,总是喜欢跟着母亲去地里采茶。或许潜意识里,并不一定是为了帮助母亲,只是喜欢沾满双手的茶苗的香。喜欢那茶苗,一叶一叶,在微风里,在艳阳里的招摇。茶叶一直采着,采了许多年。前些年,我还是每年都要回山里老家采茶的。我采茶,专拣最鲜嫩、品相最佳的采,害得母亲总要跟在我的身后,为我修棵。近几年没有采过茶了,但向往仍在。
父母亲到现在为止,还是在做着手工的茶,传统的炒青。清明前夕,也做为数极少的毛峰,同样是手工的。他们做的茶叶,清香馥郁。或许是渗入了感情的因素,总感觉乡间许多的人,怎么做,都做不出我父母做的茶叶的味道。这么些年来,我也就一直迷恋着父母制作的茶叶。
我最爱看母亲在杀青时的那一刻。我常常感觉那一刻是极富诗意的。
浓雾缭绕——不是浓雾,是荼叶雾,茶叶的绒毛,以极快的速度,在空气中弥散,纷披在母亲的头发上,衣服上,血脉里,无孔不入。那一刻,真是香成一片海。是的,就是海。使劲地闻,也闻不够。
现在大多是机制茶叶,手工制作的茶叶是越来越少了。那种天然的浓郁香气,是越来越趋近于无了。许多的茶叶,泡在杯子里,好看是好看极了,两叶一芽,嫩生生的,好像回到了它的前生。又绿回到树上了。只是这回是绿在杯子里,杯子是茶叶的树。喝到嘴里,却只有一时半会儿的甘甜,并无多少回味。香气,也确乎没有。机器的气息,代替了人的气息。
我这个人,喝茶是不太讲究的,但不对胃口的,绝对不喝。这几年,喝铁观音多。铁观音介于红茶与绿茶之间,滋味香高醇厚。绿茶,我则基本只喝炒青。毛峰,大多只是中看,却并不中吃。那种茶叶,泡在杯子里,根根茶叶婷婷玉立,像是一个个妙龄女子,散发着馥郁的香气,却并不十分好喝。味道清清淡淡的。我喜欢喝到嘴里那种浓稠的味道,让人久久回味的味道。就像一个历练人生的女子,她有着成熟、圆融、宽厚、豁达的气韵,经得起久久回味,她的心里肺里,都是散文,都是诗。一杯铁观音,一杯炒青,可以慢慢地消灭掉一个冗长的下午,或一整个寂寥的雨天,是一种妙不可言的饮品。到最后,茶叶完全成渣了,还是余味未消。品茶,也就是在同一个美好的女子在作倾心的交谈。
我感觉更多时候我喝茶并非是体内需要,而是骨头需要,灵魂需要。我的骨头,我的灵魂,需要一种安抚,安顿。一杯清茶入骨,灵魂就得到很好的安抚、安顿了。一瞬间,人也变得澄明起来,心也变得如洗过一般。如果仅仅是肉体需要,那喝水,喝果汁,都可以解渴的,但茶不同。“不可一日无此君”。是也。记得有次出差,宾馆房间里备用的茶叶,竟然是荞麦粉茶,饮后极为畅快。这样的茶,与我有着相通的气息,像是前世的姐妹一样的。此生,茶,是附着在灵魂里的。
我喝得最多的,是我父母手工制作的炒青。这种茶叶,也不知是否是因为里面有了他们的气息、温度,还是别的原因,反正,我是爱极了那味道的。喝着,喝着,我就会回到儿时,回到曾经青葱的过往,回到故乡的怀抱。斯时,鸟声稠密,兰花吐香,溪水潺潺。茶叶地里的庄稼疯长。一些思绪,穿越四月的麦地,抵达恒久、绵长。我指头上的青,转瞬变黑,变灰,变凉。浓浓的茶香,却挥之不去。
喝着喝着这些茶叶,我已喝成个面带茶色的中年女子了。人,是越来越憔悴,心,却更深地沉入到茶叶的澄明里去。这是宿命的。壶里乾坤大,杯中日月长呀。也许是茶叶多年的浸润、清洗吧?是真的感觉体内没有太多的浮尘,人世再多的喧嚣,似与我无关。我的血脉里,流淌着的是一条清澈的小溪,浸透了茶香的小溪。在一杯一杯的清茶里,翻开书页,细数着光阴,与古人、今人,说些灵魂的絮语。头顶上,总是一瓣又一瓣的花,纷纷落下。
有一日,几个朋友一块闲坐,清谈。其中一位就说,现在能像我们这样安静地坐在一块,说说话的,真是不多啊。说话的当儿,窗外的微风,衔来一声一声的鸟啼,各自面前一杯清茶,冒着丝丝缕缕的热气,腾腾的,香雾缭绕。
清风玉露,一壶闲情。
春天·蛙鸣
也许没有哪一个春天的到来,能够根本改变人的嗅觉与气味。
一些春天,早已逝去。
万物勃发的春天,“东风无力百花残”的春天。生与死永远是孪生兄弟,相依相伴。一朵花,还未来得及看清它的明艳,未来得及嗅出它的香气,它已零落成泥。这就是春天。这个春天,我没有去看桃花,也没有看见一枝梨花。它们来过,一夜之间,就没有了。被风吹凉了,被雨打残了。这就是春天。
春天是一条壮阔的河流。人,是不能两次踏人同一条河流的,所有的春天,都不是一样的。没有谁会踏人同一个春天。
许多事物,一点一点地长大。新生的绿,一点点注满枝头。而我的关节,在春天里,却是隐隐地疼的。时时刻刻地疼。
蛙声疼吗?或者,蛙们是不是因为某种疼而大声叫喊?
我又一次沦陷在如潮的蛙声里了。
这些蛙,不是我童年里的蛙,不是那些躲在稻秧里倾听春夜的蛙,不是踩着农事韵律的蛙。是寄身在城市里一弯池塘里的。它们,在城市的一隅,在楼房与楼房的缝隙里,高亢地歌唱着,呐喊着,兴奋地舞动着鼓槌——蛙们如果有疼痛,那么,它们的疼痛并不让它们痛苦?它们甚至等不及水草蔓生,便开始清唱起来。
不知道它们是不是背井离乡,迁徙到了这里,还是它的故乡一直就在这里?它们的声调是清越的,高亢的。
仔细听听,一些黑,一些冷,一些嶙峋,一些峻峭,都唱出来了。天地亮了,暧了,宽阔了,敞亮了。一些影像丰满了。花儿也就真的开了出来。一枚枚小小的音符,像火苗,跳跃着,升腾着。真想是一只蛙,守着它的园地。在它自己的园地里,谛听、谱曲、欢唱,剔净园内的虫子,生在园地,老于园地。
渐渐地,绿色辽阔。我的忧伤辽阔。
暖风,一直熏啊,柔柔地熏,熏疼一些陈旧的伤口。
一列火车,疾驰而过。驮着如潮的蛙声;驮着千里万里的桃花与莺啼。
“草熏风暧摇征辔”,我的马儿呢?是否锈迹斑斑?是否消失在时光的深处了?我要打马,我要打马,回到童年的蛙声里去。我要回去。
一只落满灰尘的木马,依偎在春风里,长满了芽苞。
最后的冷
一个人在池塘边漫步。只有无边的寒风,牵着我的衣襟。往日唱歌的,跳舞的,漫步的,小跑的,练胳膊练腿的,全都不见了踪影。是冷啊,最后的冷。这样想的时候,我将围巾拉了拉,裹住脸。
所有的树,都安静地站着。坚挺的沉默,光秃秃的。很清痩,很单薄,很坚硬。“在寂静之处,有翩翩之舞”。走着,走着,闻到了芽苞的气息了。我的骨头里,也似在长着芽苞,吱吱地长着。池塘边没有青草,更没有蛙鸣。但我却听到了它们。听到了它们强劲的呼喊,与清香的气息。
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清粼粼的水,在反射着寒冷的光。我却分明感觉到:星星在头顶上闪烁;月亮,在一笔一画地勾勒出圆意;水上面,是一望无际的,粉红的、洁净的莲。
轻轻地,唱起一支歌:鸿雁。“天苍茫,雁何往?心中是北方家乡。鸿雁向苍天,天空有多遥远。酒喝干,再斟满,今夜不醉不还。”反复地唱。尤其最后几句:酒喝干,再斟满,今夜不醉不还。
唱着,唱着,像是去奔赴一场盛宴声首有些高亢起来,今夜不醉不还!我唱给我一个人听呢。或许周围,也有无数在听着的耳朵吧。
忧伤,豪迈,悲壮,苍茫。无边的空旷,亘古的寂寞。
泪水潸然。
这多像我们的人生,永远都没有停靠的站台。我们也是不断飞行的鸿雁,永远不知道天空有多遥远,永远不知道故乡在何方。总是在不断地飞行着,永远不知疲倦。最后的站台,总等在那儿。有一天,上帝让你休息了,就休息了吧。不要试图留下痕迹,我已飞过。
冷,快落幕了,到了剧终。啊,最后的冷。忽然感觉“大寒”这两个字,无限地明媚与温暖。
总有些什么东西,在最后的冷中孕育;总有些什么事物,在冷中被反复淬火。经过了最后的冷,便是春的河流——恣意的奔腾;便是漫天漫地的绿的手指在生长。
暮春
春天呼啸而过。我去寻访,春已迟暮。采撷些剩余的春色,聊作纪念。
留春住?这只是个梦想罢了。春,只长住在人们心里吧。季节的春,总是那样的短,那样的短。人生的春,比季节的春,那是更短了。每一年的春天都是不一样的。寻访春天的人,是不一样的。去看春天的脚步,是不一样的。心境,是不一样的。便是同样的人,同样的风和日丽,同样的春雨绵绵,看到的春天也不是一样的。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春天里的万物,也不是一样的。去年的,只是去年的。而今年的,只是今年的。绝不是轮回。
春光里的人,也只能是年复一年地,一寸寸地老去。老去的,却不再回来。
我怀念在春天里走远了的人。我相信她一定揣着满袖的花香与阳光,走在芬芳的路上。她,曾经和我们,一起走在无边的秋光、秋气里,如今,却不知道到哪里去寻觅她的芳踪。我怀念,一些朋友曾经和我一起在春天的草地上小坐的时光,我怀念那些潺潺的絮语,与斯时天地之间的气息。那些,都是一去永不再回来。
由此,我想起许多的聚会。每一次聚会,都是不一样的。聚会的人不一样,主题不一样,意义不一样,留下的味道也是不一样的。聚会再美,也总是瞬间即散。我珍惜所有的聚会。那些聚会里面,一定有我们看得见和没有看见的珠子。
紫英。每一朵,都是一个响壳的语词。许多朵在一起,便婉转成明丽的诗行了。
忽然想起格非的小说:《山河入梦》。那一大片紫云英花地,永远都只是一个踏不进的乌托邦。
那大朵大朵的云的阴影,就要砸下,就要砸下。每一个人,真的都是一座孤岛吗?别人走不进吗?应该是可以摆渡过去的。
我此刻是徜徉在一片紫云英花地里,与我的好友一起。没有乌云砸下来。阳光很好。河水很清亮。紫云英开得不计其数。
看见那些无边的绿色,她说:想吃。我却是想要拥着它们,睡去。她说:一想到明天没有这么好的阳光,真是忧伤。我对她笑:明天也还是有阳光的,只是决不会是和今天一样的。一定会更老一些。
斯时,树上的鸟儿,像镶在空中的珠帘,被风吹响,发出一阵又一阵的翠鸣。
风住尘定
外面,雨纷纷扬扬。雨丝飘进窗来,微凉。间或,有一只鸟儿,在铁灰色的天宇上,飞着,唱着歌儿。远方一抹青山,雾气蒙蒙。一些绿,若隐若现。
恍惚之间,我也成了一滴雨,在天地之间飘洒。是的,我也是一滴雨。落到大地上,是我的宿命,亦是我的宗教。等这一场雨,似乎已等得太长。似乎只有这雨,才契合了我此时的心境,才能洗刷我体内积聚的灰尘。
不知是否年岁渐长,总是无由地喜欢听雨。总是希望自己,也化作一滴随意飘洒的雨,在天地之间,舞蹈。
对面,是无数双眼睛。不是眼睛,是窗户。每一扇窗户,都是一双眼睛。无论白天黑夜,这些眼睛都是睁开着的。无数的铁栅栏。我们不能越过铁栅栏去看到更多的真相。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独立的单元。有着各自的痛苦与欢欣。窗户外的眼睛,是不可能看得分明的。哪怕你有一双再锐利的眼睛。
与侄女儿在一起呆着,挺安静的。看看书,上上网,到母亲的地里去摘摘菜,逛逛商场,给她看看作业,听她说说话。她总是出些急转弯的问题要我回答,而我总是被她套进去了,成了傻瓜。跟小孩在一起,自己就成小孩儿了。餐餐都得为她做爱吃的。每日每晚,都得为她着想。
先生每每与侄女儿絮絮叨叨地说着话,建议她将来要学生物学。先生说,生物学是一门非常有趣的学科,大自然是生生不息的。我们如果研究生物学,也自然会融入到那一种生机勃勃之中。大自然中,有太多的谜语,有待我们去揭开。
生物学我不懂的,但我知道生物大都在门外面,即使是这样的天气,傍晚时分散步在微雨中,看看雨中的各种生物,也是十分惬意的。
我与侄女儿又买了各自需要的书。雨中读书,亦是令人愉悦的,是晴天比不上的感觉。
越来越满足于自己这样的现状。各方面,都还是满意的。也就只能这样,知足常乐吧。是不可能比这更好的了。就这样吧,这样安静地到老。
父亲打了电话来,说是母亲今天回不来了。我说不急不急的,把家里的事情做妥帖了再回来不迟,父亲说,得再劳你照顾一下一凡啊。很抱歉的样子。一凡就是我的侄女儿,她在我这里住了快一个月了,因为母亲回家摘茶与照顾父亲。我的父亲总是这样——永远怕麻烦别人,连自己的女儿都是。
春已净了。像红颜尽失的妇人,却有着些渐渐成熟的丰腴。当然,这大地会越来越丰腴的。街道两旁的樟树,全是米粒般大小碎碎的花,清香扑鼻;柿子树上,已结了些亮晶晶的小柿子了,毛茸茸的,可爱极了;我们家院子里的枇杷,也一球一球的,满树;母亲种的豌豆,已是豆荚饱满,喜人得很。
得知一个朋友,与她的爱人,在走山走水,人生的大乐趣也。愿他们越走越远,走出天高地阔来。人生的至爱也不过如此,最大的幸福也不过如此。到老了走不动了,就坐下来,跟爱人一起,坐着说话,说那些行走,说那些看过的风景,走过的路。并记录下来。祝福他们!
纪伯伦说:“当你背向太阳时,你只能找到自己的影子。倘若你想拥有,就切莫苛求。”
风住尘定。但也许是风不住尘不定,或者风不住尘定。
月白的影子
斑鸠,在我的脚边惬意地走着,慢慢悠悠地走着,一点都不怕人的,身上有斑驳的花纹。微风吹起它的羽毛,像是在吹弹一个轻轻的梦幻。—只胖墩墩的狗儿,一次又一次跳起,总想去抓住它,但总也抓不住,空扑腾而已。这实在让人欢喜:斑鸠的肥美与笨拙,实堪一看;而狗儿的空扑腾,更让人捧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