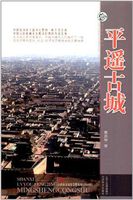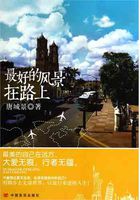想象一朵花开的时间
想象一朵花开的时间,是我常常做着的事情。却一直没有做好,也永远都不会做好。我永远都不会知道,一朵花开需要多长时间,它又能开多久。不知道。
花儿,它一直在开,或者说一直在试图盛开。只要它是花儿,它便要试图盛开。从种子深埋,到发出嫩芽,到郁郁葱葱,到含着露珠、亭亭玉立,我不知道这需要多久。更不知道,花儿到底是开在什么时候,是哪一瞬间。它总是在不经意的时候,在我们根本不知道它始自何时,它就盛开了,悄悄地。盛开了,或细小,或硕大;或淡雅,或浓烈。总之,它是盛开了,香气氤氲。我却常常怕它盛开。我也明明知道,是花,它总是要盛开的。但总处在深深的焦虑之中。我怕盛开之后的寂寥。
日思夜想的,是盛开。日夜焦虑的,是盛开。
会不会有一种花儿,永远都在半睡半醒、半开未开的状态?或者,只在萌芽状态?萌芽状态,也是有着一种超凡的美丽的。只是这到底,是被雾罩了。人,到底还是喜欢花开,盼望花开的。
一朵花能开多久?有没有不老的时光——为一朵花儿,永远遮风挡雨,永远不让它消痩?或许是有的吧?
院子里的米兰,开了又谢,谢了又开,香味极细极淡,声息若有若无。我喜欢这种香气。闻着这种香气,总感觉岁月静好,风住尘定,一切都在阳光下。
所有的野草野花,吸吮天地之精华,宇宙之灵气,开得春意盎然,蓬蓬勃勃,却不太需要人类的关照。一枯一荣,恬淡自在。这是天与地之间的精灵。
客厅甩的杜鹃,却到底是枯萎了。没有阳光普照,没有雨露滋润,它就那样默默地,悄无声息地枯萎了。是一点一点地萎去的。我每天总看到它在蹦着新的粉嫩的芽苞,总以为它会开得地久天长。前不久,刚刚给它剪过枝,也时不时地给它浇水、施肥,它还是萎去了。这段时间,由于父亲的病,我没有跟它说过话。匆匆出去,匆匆回来。能够偶尔记起它,就是它的幸运。
“你来了,花儿就开了;花儿开了,你就来了。”你不来,花儿不开(你不来,你怎么知道花儿是开着的呢);你不来,花儿萎去了(你不来,花儿开了,也等于是萎去了)。请原谅,亲爱的,这段时间,我真的没有跟你说话,这是我的错。我小心翼翼地将枝叶已完全萎去的花盆,搬到院子里,心里满是愧疚。
并不是所有的花儿,都能如米兰,开在阳光下啊。像这盆杜鹃,它只能在温室里开着,谢着,静静地数着它的逝去的风华。当初盛开时,是怎么样一番惊艳,将一室所有的事物照亮。却到底因了没人陪它说话,萎去。
再如昙花,却只开在静夜,在无人知晓的静夜,一个人默默地疼痛,默默地哭泣,默默地欢喜,默默地分娩,开出一朵盛世的奇葩,盛开之后,瞬间老去。也没有几个人,能守得它盛开的刹那。那是一种慢。谁愿意守着一种慢呢?谁都在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奔跑。至于到底要跑去哪里,则是没有几个能明白。它积蓄了一生的力气,就为盛开的一刹那。那是一朵硕大的烟花。瞬时,照亮夜空,照亮守着的人的心。一座庙宇,就此升起,永不凋落。只是,守着的人,是多么的少啊。静夜里,所有的花儿都差不多睡去了,人也睡去了,独它,在开。在慢慢地,一点一点打开自己,让一世所有的疼痛、馨香与美丽都打幵,只为守着它的人。之后,它安然离去,没有一声叹息。是有人守着的,昙花自是明白。生命的极致,是刹那间,绽放尽所有的光芒。
想起母亲常常说的一句话:每一朵花,都有一滴露珠滋养着。原来是这样的吗?世间千千万万的花儿,便有千千万万滴露珠滋养着吗?守着的人,那肯定是一滴最清最亮的露珠。
想象一朵花开的时间,是我常常做着的事情。这件事情,无始无终。谁是真正的爱花、惜花之人呢?莫若,将心爱之花朵,放在天地之间,让它经受风吹雨打,自在荣枯。
一张照片浮上来,一支永不凋谢的花,上面浮着暖暧的旧日时光。我爱着的人,爱着的花朵,都在照片里,散发着香气。无边无涯。
读鸟
鸟儿在窗前的柿子树上啁嗽。一声,接着一声。
柿子树的叶子,早已被秋风收净了。树枝,是光秃秃的,像无数的痩手。鸟儿,就在这些痩手与痩手之间被传递着——腾挪,跳跃。欢快不已。起先,只是听见鸟声,见不到鸟的身影。鸟是灰色的,树枝是灰色的,天是灰色的,冬的帘子是灰色的。许多灰色混合在一块,看不出鸟究竟在哪里。要仔细地看,啊,不是一只,有好多只的。
树上的柿子一个不剩了。它们吃什么呢?在哪里栖居呢?鸟窝,确实未见。这样小的小鸟,它们的窝必定是在草丛里,或粽叶林里,或山上的柴禾上吧。
一天,又一天,它们都在这棵柿子树上啁啾着。它们当真有那么多的快乐吗?叫声细碎而圆润。我总想象它们是珠子。是珍珠,是露珠。清亮而温暧。
它们让我在枯燥乏味的公务之余,总是听到清澈的泉声。
也许,人是不如一只鸟活得透彻吧?它们想觅食就觅食,想恋爱就恋爱,想唱歌就唱歌,想开会就开会,想迁徙就迁徙。它们是无拘无束的。它们有集体主义精神。它们,总是一群一群的。最少也有两只在一块。在树上,在地面上,在天空下,在人的视野里。
鸟儿是越来越胆大了,也越来越多了。它们不忌讳人类的眼神。是嫉妒也好,呵斥也好,不屑也好,它们乐它们的,唱它们的,舞它们的。这叫旁若无人吧。是叫人类真的要嫉恨的。人类,总是你看不惯我,我看不惯你。你不服我,我不服你。甚至明枪暗箭地防备着,厮杀着。看得见或看不见的血痕,总在起伏。我很少看见鸟儿们拼命争斗。或许,也有。只是我没有看见罢了。
种庄稼的人越来越少了,生态环境却是越来越好了。野果子日渐地多起来。这也许是鸟类得以繁衍下来的重要原因吧。只是一些已经消逝的鸟类,如果再出现,那就近乎奇迹了。比如我小时候,在乡间看到的野鸡或鹞鹰们,已好多年不见它们的踪影。
开发来开发去,城边的林子没有了,地没有了,总还有乡下的林子,乡下的地。鸟儿们总还是能找到它们的家园。天是灭不了鸟类的,人也是灭不了鸟类的。
绿叶婆娑时,鸟儿在叶子与叶子的缝隙里穿梭;果子稠密时,鸟儿在果子与果子之间跳跃;而所有的叶子与果子全部落净,鸟儿也并未见得萎靡,仍然这么快乐、无忧。岂不是叫人类要嫉妒的么?又何况,人日日里奔波在社会与自然之间。自然性已愈来愈少了,愈来愈多的是社会的人,世俗的人,日子的人。为生活忧,为日子忧,为地位忧,为福利忧,为前程忧,为爱情婚姻忧,为子孙忧,为灵魂的皈依忧。日日不得安宁。鸟儿才不管这些呢。我有时会想,鸟儿的逻辑是:我在,故我在。这样,多好!人类,要思什么呢?是真的要思,才在么?
雨,一直下
雨,一直下,一直下。许多的事物,都沦陷在雨里了。它们,在雨的途中呼吸、奔跑、发芽。也在雨中渐渐枯萎。一些气息,总是在雨中氤我是喜欢下雨的。雨的清凉,雨的晶亮。尤其是冬天的雨,淋淋漓漓,清寒,似在说着无尽的絮语,而又隐隐地带着些春天的气息。
雨总是把我带到最初的地方。雨,顺着瓦楞沟,倾泻下来。屋檐下总是滴着水,一直滴,一直滴。滴下来的雨水,将墙角打得湿透,斑斑驳驳,如一个个显眼的疤痕。被雨滴着的地面,一个又一个的小水珠,溅着。像是一个又一个小小的梦,积攒好,又迅速地破碎了。小时候,常常就这样看着雨滴发呆。雨声,是说不出的清脆。像是一个不绝地唱着歌儿的女子。那歌喉永远地清亮,如山泉,如竹露。袅袅如烟。
母亲总会在这样的雨天里,在雨声一下一下的节奏里,纳着鞋底,补着旧衣,磨着麦粉。也常常有邻家的女人来串门,谈天,说笑。只有雨天,才这样清闲。
而父亲,往往会在雨声里,纳笤帚,劈柴火,磨菜刀;或卷起一本线装书,依依呀呀地念起小说来。有《秦雪梅吊孝》、《薛仁贵征西》,还有……我也不甚记得了。那声音,真是有板有眼,很是好听。不是念,竟然是唱。在那样落后闭塞的山村,父亲算是识得几个字的。唱着,唱着,有时候,会有屋场里的人来听他唱。一会儿,家里就会聚拢来许多人。都是我父辈的,可也都是精壮的青年或中年男子。家里就烧起树根来。彤红的火苗窜着,冒着丝丝的热气。人们在秦雪梅的悲情或薛仁贵的惨烈里,取暖。这也是一种极好的食粮吧?那是个极其贫乏的年代。他们的脸,在火苗的映衬下,彤红彤红,像是完全沉浸在小说的丧事或战事里了。只是,那些线装书,如今不知藏身何处?如果还在,它还会不会记得当时的温度?当时的雨声?我那时,多半是坐在暧火桶边,听他们唱着,念着,说笑着。
父亲在雨天也格外关注我的学习。常常会抽我背课文,写生字。那时,也真怪——课文上的字,能倒背如流。反着背,顺着背,都是不能丝毫难倒我了。生字,那是更不会难倒我的。父亲,也常常摸摸我的脑袋:毛儿乖,毛儿聪明,我的毛儿还有点用呢。当然,我们那时的课本,是非常容易的。几句话,就是一篇课文。甚至一句语录,也是。如果背不来,那就是不正常了。有时候,父亲会教我背诵毛主席诗词。直到现在,我还是能记得毛主席的大部分诗词的。初中时,每每上到毛主席诗词的课文,我都能比别的同学先背上来。老师叹为奇异。岂知,我已早早预习过呀。有段时间,我会常常拿着毛笔,临摹毛泽东诗词里的那些龙飞凤舞的草书。尤其“毛泽东”三个字,是临摹过无数遍的,只是怎么学,也还是不像。临摹得最多的一首是《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但是,成效不大。就像“我儿练了三缸水,只有一笔像羲之”里羲之邻居家的小孩那样愚笨,怎么练,都没有毛主席草书的一丝神韵。后来上了中学没有毛笔课,就慢慢气馁了,没有再练了。
后来,后来的雨声里,上中学后的雨声里,父亲也不再抽我背课文了。也不知他是相信了我用功了,还是不再关注我的学习。我却总在隐隐地期待着,期待着他有一天,又会突然地抽我背课文。但是,一直没有。后来的雨声里,父亲不仅再也没有抽我背过课文,也没有让我默写过生字了,他也不让我背毛主席诗词。在漫漫的时光中,我也在日渐一日地长大,长成小姑娘的模样,长成大姑娘的模样。那些少时的雨声,总还是记得的,总还是在滴滴答答地流淌。下雨时,他唱线装小说的依呀声,也再没有听见过。但却总是听见。在雨声里,分外分明。它们,总是以一种老旧的步速,慢慢,慢慢地踱过来。像一段老时光,带着老旧的喘息;像一张老唱片,裹着些嘶哑。慢慢,慢慢地踱过来。
“妈妈,天上怎么不安个开关啊?老落雨。”这是儿子两岁半的时候,在一个梅雨天问我的。我当时哑然。
是呀,天上为何不安个开关呢?或许,有些雨,是没有幵关的。它就那么一直下,一直下,不停地下,永远在下。
雨水,从屋檐上滴下来,溅着大大小小的水珠。冬天的雨,尤其亮而脆,闪着清寒的光。在雨声里的那些声音,却已消逝很久了。又总是于某个不经意的时刻,慢慢、慢慢地踱过来,踱过来。
山坡上奔跑的童年
我的童年,一直都在山坡上奔跑。
不知道,弟弟是否还记得,我们那一次醉卧山坡,吃野草莓。有鲜红的,有紫黑的,有粉红的,也有黛青的;有带刺的,也有光滑的不带刺的。那一大片向阳的山坡,长着许多麻砂石头,却有星星一样多的野草莓。我们拼了命的吃,怎么吃也吃不完。衣裳都拉得裂了口子,手也多处划破。吃得舌头、嘴唇发紫,吃得牙齿发酸、发软。吃得日头明晃晃的在头顶上一寸寸碎落,终于滑入到暮色里去。父母在田野里劳作,我和弟弟在山坡上饕餮。吃了那餐野草莓后,有好多天都不能吃硬的东西,诸如蚕豆、花生,是嚼不动的。
不知道我的那些表兄弟姐妹们,是否还记得,我曾经与他们南征北战过的山野,以及山野里的风与虫鸣,还有那些追逐我们的绿草与红花。是太多场次的征战了,身上滚了太多的泥尘。事隔几十年,都没有把它们拍落,也是永远不想把它们拍落的,也是拍落不去的。我们的笑与汗水,都撒落在山坡上。一瓣瓣,在山坡上的泥土里,开花、结实,长成参天大树。
常常地,跟同屋里的孩子去打猪草,拾柴火,捡茶籽。这些,都要爬山上岭,才能够做到。作为孩子,我们最想的,并非为家里做多少事情,更欢喜的是,大家总在一起,永远在一起,玩着乐着。而如果因为在玩着乐着的当儿,也为家里分了一点忧愁,并且被父母夸奖,那肯定便是拾得额外的一份快乐了。我们的童年,好像永远有打不完的猪草,拾不完的柴火,捡不完的茶籽。有时是去挖菖蒲。那种清香的药味儿,总是要一闻再闻的,太好闻了。或许我们的童年,便是在那种清香的药味里泡大的吧。
谁家的孩子感冒了,谁家的母亲便会用我们挖来的菖蒲加艾叶烧水,给他洗脚去寒。
有一块山坡,住着我最卩钟爱的一株幽兰。我一直在想着,这样一株幽兰,只有我一个人认识寻访它的道路。它永远都在那里等着我,等着我去寻访。永远。从来没有别人去采摘过它,去闻过它的芳香。任何时候去,它都在那里。是那样的一个上午,阳光暧暧地照着。我母亲在挖地整墒,种东西。我在靠近我们家自留地的山坡上瞎跑。跑着跑着,就闻到兰花的香味儿了。去寻,果然就寻着了。它,躲在一大蓬荆棘丛里。背倚着一块丑陋的石头。兰花的旁边,全是落下来的旧年的松针与杉刺,一些陈腐的气息弥漫开来——破败的叶子的气息,更显出兰花的香。我是想把兰花悉数摘下来的。一共有五朵。是那种小小的春兰,修长的茎,袅娜的花。一枝一朵的。很青葱的颜色,不带一点杂质。想了一分钟,却并没有摘下,让它仍留在那里。第二年春天,再去看,它还在那里,又开了新的一轮花朵儿了,仍是没有摘下。如是,接着好几年,去看它,都没有采摘。直到小学毕业,我每年春天都要专门去看它的,每次都舍不得摘下一朵。我想过许多次,这株兰花,为何一直就没有人采摘过呢?它是否专为我而生,专为与我的遇见而生?既是这样,我如何舍得去摘它。至于小小的我,为何一次又一次去看它,没有忍心将它摘下,到底是如何想的,我现在是一点都不记得了。现在回过头去想,或许冥冥中,我有一种感觉吧?花,是开给爱花惜花的人看的。只是我当时太小,并无文字记载,亦无史料可查。但我一次都没有摘下一朵花,这,我却记得非常清楚。也许,我是这样想的:我不摘下它,它就是我的,它只是我的,它只开给我一个人看。我不告诉任何人,别人就都找不着它,它只是我的。我的堂姐堂妹们,是爱极了兰花的,一到春天,她们漫山遍野的采摘兰花,回家放瓶子里养着,放头上插着。香则香矣,但总香不了几天,花儿就萎谢了去。连一声叹息都听不见。而我的花儿,却永远开在山野,永远清香着。以至于许多年后的今天,这株幽兰还是常常会跑到我的梦里,来与我相聚。我曾经想过,要把它挖到城里来,栽在我的小院里,好日日相伴。想想作罢。城里的泥土,是必养不活它的性灵的。它也必不会在城里的泥土里,开出烂漫的花朵儿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