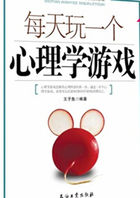“啊!”
皇宫里的夜,是如无人穿梭般的寂寥凄清。
流水烛光的长街,交错纵横的楼宇,猛然被一声女子凄厉的尖叫打破了如往常的沉寂,骤然灯火通明,映彻了整座皇宫内院。
在芳仪宫的内殿,跪满了一众泪痕楚楚的宫人,平躺于软榻之上的素衣女子,身下的猩红刺目。
“芳仪娘娘,您支撑住,奴婢已经打发太医来了,娘娘……”
夏梓妆如同梦魇一般的双眸空洞而迷茫,任凭宫人如何呼唤也不曾给予半点回应。
璞贤和邵家墨急匆匆的自昭仪宫赶来,只是不曾进去而是先在外殿等候,太医也紧随其后赶了来,把脉、屏诊、针灸,一一用过仍是不见起色,几人面面相觑,眉宇紧锁,其中一人看似为首的太医起身来到外殿,语气忐忑。
“皇上,芳仪娘娘误食了红花与麻七,引发了孕前的血崩,失血过多,恐怕……无力回天了。”
璞贤原本平静的脸蓦然闪过一丝惊诧,“孕前?你是说夏芳仪有了身孕么?”
太医亦是惊愕,“怎么,芳仪娘娘不曾禀告皇上么?半月前芳仪派了宫人请微臣到宫中诊脉,确为喜脉,已有两月有余,皇上忙于政事故而子嗣不多,这一天大喜事微臣本想立刻告知皇上,却因为太医院诸事繁忙,耽搁至今,皇上恕罪。”
已有两月的身孕……璞贤蹙眉凝思,两月前自己只在芳仪宫宿过一夜,之后便再无召幸,莫非只是那一夜便有了身孕么?一月前……一月前自己撞破昭王与夏梓妆深夜在殿内独处,且衣不蔽体,难道?
璞贤一扬眉,“你确定是两个月的身孕么?”
太医伏首,“微臣服侍宫中娘娘从先帝至今已有三十余年,不曾诊错过一次脉象,故而微臣愿以项上人头担保,芳仪娘娘确有两个月的身孕,绝无差错。”
璞贤在得到太医的再三肯定后方才舒缓了脸色,佩儿此时突然从殿内跑出来,跪在地上又是哭又是急,“皇上!芳仪娘娘不好了……”
此夜,除却芳仪宫一片混乱,更为焦灼的便是郑浣娆的月娆宫了。
昨日午膳后,郑苑侍奉了一盏红枣枸杞茶到月娆宫进献,之后未曾逗留便碍着郑浣娆要午睡早早的带着侍女离去了,生于川陕一代尤其喜爱辣食的郑浣娆厌恶红枣的甜腻,正欲让宫人倒掉之际,却被贴身的六品女官暖琢拦了下来,她因早前到太医院取暖身子的药汤而无意间瞥见放在抽匣最上层的夏梓妆的安胎汤药记录,这才知道夏梓妆竟然已经怀有身孕,她于是进言郑浣娆。
郑浣娆虽然贵为五夫人,却因早年掉落冰湖之中伤寒侵体始终不得有孕,自然心急如焚,眼看着邵家墨母凭子贵跃为中宫之首,夏梓妆若是再一举得男,自己的地位难保不会岌岌可危,暖琢说倘若以红花代替红枣,以麻七代替枸杞,因二者相近,不细细观察自然无法发觉,使夏梓妆落胎必能如愿以偿。
郑浣娆素来有勇无谋,酷擅冲动,一时间答允做了这样的事情,虽然送药的宫人是最不起眼的司膳府的一个刚进宫做事的小丫头,连个备案也是方才送进司婢府的,可是抽丝剥茧也极有可能查到自己的头上,所以自然急火攻心,坐立难安,暖琢心知自己犯了大错,还未等郑浣娆出言怪罪,自己则先脱去了官服跪在大殿之内。
“华仪娘娘恕罪,微臣只是忠心念主,本以为能为娘娘排忧解难,不想竟然心急做了错事,使娘娘身陷泥沼之中,不过娘娘放心,无论什么后果微臣一力承担就是,绝不拖累娘娘半分!”
郑浣娆不知道外面的情势如何,不安的在殿内踱着步子,本就心绪不宁,再经暖琢的一番扛罪不扛罪的话,更加气血沸腾。
“只看身边的人就知道自己将来会有什么样的下场!本宫不该信你们这些下人的话,你以为你揽下罪责皇上就会信么?刚得到了协理后宫之权的邵家墨她又会信么?本宫无子,真出了事情没有依靠,病急乱投医也就罢了,倒是便宜了邵家墨上演一出借刀杀人的好戏!”
郑浣娆恨得咬牙切齿,美目狰狞。
“齐昭王对夏梓妆有什么心思谁不知道?不过是嘴上不提心知肚明罢了,夏梓妆若是生下一个皇子,手握兵权的昭王纵然如今交出了兵权也是尽得军心,他会不让夏梓妆的儿子做太子么?本宫横插一手,正好合了邵家墨的心思!既料理了太子之位的有力竞争者,又将本宫一并打压了下去。”
郑浣娆一边说着一边坐回了凤椅之上,看得出她此时果然心惧忧思,一张素来红润的粉面竟然也泛起了苍白之色。
“事到如今多说无益,本宫从不后悔,只是看皇上如何处置了,能否再因顾念旧情而饶过本宫了。”
正说着,门帘经人一挑,走进来一位年纪轻轻的小公公,面色无悸,俯身道。
“华仪娘娘,皇上请您往芳仪宫去一趟。”
郑浣娆深吸一口气,不禁面色扭曲起来,“夏芳仪……怎样了?”
那位公公略微以沉吟,语气悲切了些许,“夏芳仪怎样,奴才实在不知,奴才只是在外面伺候,连主子什么样也不了解,听人议论恐怕不容乐观,华仪娘娘去了便知道了。”
郑浣娆与暖琢走到芳仪宫殿外时,里面灯火彻亮却一片寂静,唯有隐隐约约的哭泣之声在暗夜之中传来,闻者悲切,不禁头皮一阵发麻。
璞贤面色沉重,一言不发的居于正中,邵家墨站于一侧,众人皆是默默无语。
郑浣娆一袭青白色裙衫低着头走进殿内,不曾开口先是一跪。
“你知道朕叫你来,所为何事?”
沉寂多时之后璞贤终于说话了,只是言辞犀利,语气疏漠,全然没有一丝情意。
“臣妾知道。”
郑浣娆四字话落已是泪眼朦胧,“臣妾疏忽,红花与红枣皆是浓稠似火,且掺了其他的东西闻上去也是无法分辨,臣妾……不知怎的就将本想给夏芳仪的红枣汤送错了,可是臣妾并非存心。”
“并非存心?”
璞贤话定剑眉一扬,额上青筋顿起,让人见之生惧。
“你自己怎么不曾将红花错食为红枣?你可知道,因为你的毒妇心肠,夏芳仪连同她腹中之子,一并做了冤魂么?”
璞贤此话一出,内殿之上忽然传出宫人悲痛不已的哭声,秉台之上的两枚红烛不知何时被换成了白烛,仓促的光灼让一屋子的人不禁叹息连连。
郑浣娆身子瘫软在地上,一行泪水瞬间喷涌而出,她只是想害了夏梓妆的腹中胎儿,却不想竟然作下了一尸两命的孽债。
璞贤闭上眼睛,记得初见她时,郑浣娆不过十四五岁的年纪,明媚艳丽,灵动活泼,她是叶赫木佳氏一族最风华绝代的出生贵重,举世无双。
她说她要嫁世间最潇洒的男子,也唯有这样的男子,才能配的上她。
十八岁的璞贤立志要做举世无双的男儿,他为她学骑马射箭,吹笛下棋,精修兵法,诗词和政事,弱不禁风玉梦郎,一朝竟君临天下,世人皆讶异于他是从母妃的冤死悲痛众浴火重生,刻骨涅槃,却不想这一切的一切,都只是为着能让她亲口承认,自己就是配的上她的男子。
这么多年后宫的妃嫔如同开不败的花朵,一批未曾凋谢便有新的一批争先恐后的在这无情的后宫之中绽放盈盈,只是那样多的过眼云烟昙花一现,无论如何国色天香家世显赫,在璞贤的心中不过皆是云泥之别,唯有郑浣娆,曾在他最年少好胜的时光,让他奋不顾身的爱过一次,或许也唯有这一次。
“月娆宫华仪叶赫木佳郑氏,残害嫔妃,毒死皇嗣,手段毒辣,念入宫侍奉良久,无不尽心尽力,朕特恩诏下,立刻打入冷宫南苑,五日后黄昏赐郑氏自尽,一切身后事从简,不得按五夫人之规格繁办。”
一抹珠帘摇摇落下,哭声戛然而止,洁白的玉布挂满了整座芳仪宫,风华不及,岁月苍凉,当年谁家女,美艳世无双,昔日少年郎,情痴源流长。
晋元年330年七月,御嫔之首夏梓妆殁于芳仪宫,追封夏妃,葬入洛阳妃冢,时年二十一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