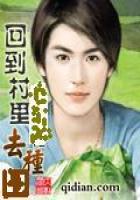鲁智深是水浒传中的一位人物,看似莽撞无知,其实是一种智慧高超的表现。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要不然也不会有最后的“今日方知我是我”的一番大彻大悟的言语。自古:“非常之人做非常之事。”若我们以此种眼光来看待他所做的事情,那么他所做的事也就变得正常了。
鲁智深看似莽撞,其实是一种富含大智慧的表现,作者不会无缘无故给一个“智深”的法号,与智真长老是一个辈分(按金圣叹之说法,其实不一定是平辈,六祖慧能的弟子就叫慧明。),在这里,有必要说一例佛学常识,古时候的僧,代表的不是一个僧人,而是一个三十人组成的僧团。和尚最初的意思也不是对于僧人的别称,而是寺院主持的专用称号。
他的莽撞不同于铁牛不问缘由的蛮打蛮干,身先士卒,甚至不问青红皂白就是一顿砍杀,瑕疵必杀人,而是一种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的表现,后来许多武侠小说也借助了这种表现手法,比如杨过手中的玄铁重剑,还有武侠派的“在绝对的力量面前,技巧毫无作用”的理念,以此看来,他的莽撞却成为了一种可爱的表现。
鲁智深上梁山之前干过几件大事,一:拳打镇关西。二:大闹五台山。三:大闹桃花村。四:火烧瓦罐寺。五:倒拔垂杨柳。六:大闹野猪林。七:花和尚单打二龙山。八:三山聚义打青州。
在第五十八回:三山聚义打青州众虎同心归水泊中,鲁智深归附梁山了,打虎将李忠也归附梁山了,令人发笑的是李忠这个小气鬼一上梁山宋江就这样对他:“问李忠,周通讨这匹踢雪乌骓马送将军骑坐”,李忠是一个见血不要命的蚊子,连给鲁智深盘缠都舍不的给,才刚上了梁山,自己心爱的坐骑却被宋江送给了呼延灼,你说他心疼不心疼。不过这也合理,因为他只是一个小小的地僻星,而呼延灼却是一个天威星,在梁山上排名第八,周易不是这样说吗: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天与地还是有区别的。
鲁智深的归附并不是一个人归附,而是一个小集团向一个大集团的归附,这过程中,一如他往常的刚决果断,快刀斩乱麻。“鲁智深也使施恩,曹正回二龙山,与张青,孙二娘收拾人马钱粮,也烧了宝珠寺寨栅。”鲁智深把寺院烧了,这可是一件轻谩佛法的大事,其实不然,在那个动荡的时代,与其留着寺院给强人做嫁衣,使其更方便害人,还不如一把火烧的干净。
但是后人万不可学习鲁智深的这种佛法,因为佛法需要自证,“酒肉穿肠过,佛向心头坐。他人若学我?必定坠魔道。”
鲁智深上了梁山后的待遇要比别的好一点,梁山上好多人的归附都是一个人单枪匹马前来报到,最多就是带了些家丁家眷。而鲁智深则带来了一个山寨,你说他厉害不厉害?因为他带来了一个山寨,虽然他不再是寨主,但他同样还尽着寨主的责任,他必须对施恩,曹正(林冲的徒弟),张青,孙二娘的前途命运负责,所以听到要招安,他就必须好好考虑一下。后来金圣叹不想水浒中的人物各个都落得个悲剧的下场,于是做主将招安后的情节全盘删除,所以出了一本只有七十回的水浒传。可是悲剧本来就是悲剧,怎样修改也不可能将荡气回肠改为一种消化不良。
鲁智深好像天生就和寺院过不去,以是他两次入寺又两次出寺,后来又烧了宝珠寺,有人说这是禅宗思想在他身上的体现。要知道在元末明初,人们渐渐开始怀疑经典的作用,对于宗教,也不是如同往日那样严肃,转向了直指人心的一种追求。“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烧佛像取暖”“坐如何能成佛”等故事比比皆是。有人将之归比为市民宗教,认为是市民意识对于艺术的影响,这个说法也对,通俗与高雅,本就没有一个界限。
这样的修炼方式是极好的,因为更注重一种心灵的历练,比如徐渭的{四声猿}就讲述了一个清白女子学佛,虽则十分用苦,但是最终毫无成就。后来的一个**,反而得证大道。但是这种高境界的思想,一旦让恶徒利用,流毒千里,所以明清小说中的坏和尚也是比比皆是,让人怵目惊心。
鲁智深原本就不属于一种能享受安逸的人,他要证果就必须不断地行走,不断自我发现,所以他一生都在孤独的行走之中度过,从西安到延安到山西到东京到浙江,几乎一直在行走。再者明清的寺院名声也不是特别的好,本来是佛门清净场合却成了藏污纳垢的地方,那些和尚们不知清修,只知做淫媒以图赚几个黑心钱,打着佛法密修的幌子,教人阴阳采补之法,甚至自己的色心也不知克制,以是犯戒之事常有发生。这些在明清的一些其它小说中也可以看出来。所以留在寺院也不一定能当一个好和尚,因为他的今生已经注定是天孤星。
我个人最喜欢鲁智深说的一句话:“俺便不及关王?他也只是一个人!”凭什么关羽能用八十一斤的青龙偃月刀,我就不能用一百斤的禅杖。或者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俺便不及李白?他也只是一个人!”凭什么李白写的古自由诗被人们奉若神明,而我们写的古自由却被专家批评为格式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