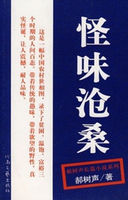到租住的小一居里,子辰似乎安静多了,但他还是问了房租,并要来合同确认了一下,防止冯余有意报低。他又要了一支笔,开始计算这些天的花销,合计的数字让他稍微松了口气,说:“冯老师,我差不多一年可以还清。我给您写张借条。”
卧室不大,只有一张双人床,冯余说:“我睡外面,免得你半夜掉下来。”
子辰上床之后,冯余又叮嘱道“:你要是起夜告诉我一声,我扶你去。”子辰也笑,齿如编贝:“冯老师,您要是我爸爸就好了。”“那就喊我爸爸呗。”
子辰嗯了一声,不知为何没有喊。冯余觉得他身体有些烫,搂紧了些,说:“有时候我不大理解,你这么年轻,怎么会懂得照顾孩子呢?可你把孩子们照顾得很好。”
子辰抬起眼睛看着冯余,认真地说“:我想成为自己梦想的那种父亲。”人过中年,常常会午夜惊醒,有什么渺远的声浪点拨心尖似的,冯余骤然间睁开眼睛,周身燥热,但并非完全出自体内,旁边的子辰烫得像温泉的热源,热气不绝溢出,衣服尽湿。
冯余拧了把冷毛巾,将子辰湿漉漉的脸擦了一遍,理了理散落在额头的乱发。卫生间的光带着寒气从背后漫过床头,微光中子辰昏迷的脸庞无比孤单,如果说每条生命都注定孤单,那么他这种孤单是最遥远的一种。
打开窗帘,夜色如海,这座中型城市既没有凶恶的霓虹,也没有痴情的星月,看不到人间也看不到天空,寂静、昏黑,无边无际,连时间也抛弃这里。
子辰父亲从事的艺术品投资,其实是贩卖时间的生意,给时间估价、投资,除却艺术品本身的材质、手工、产地之外,至关重要的就是它们距离我们的时代是否够远。这算不算在证明,世上最昂贵的唯有时间?
在子辰的青春中,他起码有5年时间是和冯余朝夕相处的,这5年的每个日夜和瞬间,冯余都记得很清楚。他回到床边拿起子辰手机,查找舜茵的号码,有个电话进来,他按了接听键。
“如果不想以卵击石,就立刻回北京来!”里面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语调平稳,却有种凛冽的锐气。
冯余说:“他现在必须回去了,他病得很重。”那边没有回复。
冯余屏住泪,低声说:“我想,他活不了多久了,请你对他仁慈些吧。”时昕鸰说:“他错误的价值取向白白浪费了他的天赋,使他的人生注定一败涂地。不要拿他的病来威胁我,没有好的身体就不能成为好的工具。我对这样的儿子已经没有挽留的兴趣了,他唯一的价值就是把时家的血脉延续下去,在没咽气之前,他的作用已经不多了。”
“要是这样的话,我不能把他交给你。”冯余说,“我想,他现在的身体也没办法给你延续血脉,就算生出来也不会健康。那样你又要说不是个好工具了。”“我最讨厌没有自知之明的人,你们这种人都像挑战风车的堂吉诃德一样只能落个笑柄,好吧你守着他吧,我看你们有多少钱往医院里填,他在你们手上,只会比在我手上死得更快。”
冯余挂断电话,给舜茵拨过去。天还没亮的时候,舜茵和安安就一起出现在冯余面前。冯余没看到舜茵的孩子,询问之后才知道临时托付给叶未奇媳妇了。子辰的情况肯定得送医院,他们商量了一下医疗费的问题。冯余已经没有积蓄了,舜茵还有不到20万,她建议先住院,不够再去和姑姑借,安安没有加入讨论,站在床边看着昏睡的子辰,说:“你们不用凑钱了,让他跟我回家。我已经叫司机开车下来了。”
舜茵说:“他不能跟你回去。”“他的病怎么回事你不清楚吗?无法根治!只会越来越严重。”安安用前所未有的严厉口气说,“在美国那段日子他好好的,自从娶了你就开始和我们作对,心甘情愿过一种下等人的生活,还自我蛊惑,被自己感动,认为自己高尚,你已经被贫穷的生活折磨成了一个疯女人,即使后来衣食丰足也找不回清醒的神智,现在你又把我哥哥害得几乎没命,他高贵的血统注定不可能习惯劣质的生活,非要那样就一定会被毁灭。也许你们相爱,但现在是时候分开了,我哥只是发高烧昏了头,一旦清醒就不会再和你这历史复杂的女人搅和在一起!”
“你不用针对我,我们在商量救你哥哥的方案,请你不要扯那些与主题无关的内容。”
“我讨厌你!”安安怨毒地咬住牙,“只要看见你对我哥哥动手动脚我就怒火中烧!我永远搞不懂你们这些已婚女人,凭借对男人的了解你们总是无往不胜,可是上帝有眼,你们实在太龌龊了!天知道你用了什么下流的手段!”
舜茵把子辰的身体从床上扶起来,接过冯余递来的勺子给他喂水,子辰烧得厉害,嘴唇上全是水泡,嘴角挂着几绺干涸的血迹。急救中心的车来得很快,趁医生给子辰检查的时候,舜茵匆忙收拾了些洗漱用具,跟着担架下楼。
安安重重跺了两下脚,薄底皮靴震得她足心生疼,不由对着沙发踢了一脚,靴子是尖头,撞在坚硬的框架上,蹭下一层漆皮,赫然出现一块难看的疤痕。
不知世上会不会有人记得,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再问“为什么”,不再试图追溯未知的侵袭,而是默默前行,只在意外到来时努力抵挡。渐渐的,不再有雄心壮志去征服,而仅仅努力咬紧牙关不被打倒。
在医院里,除了照顾成天昏睡的子辰,冯余还时刻注意着舜茵,舜茵没有哭,也没有惊慌,到银行取钱,到医院收款处交钱,有时也会打电话。
她打的这个电话是冯余必须出面阻止的。因为她和子辰预料的一模一样,预备卖她在北京的房产,好在不是全卖,只是卖其中一幢,这是为了以后做预备,所以价格上她不肯让步,坚持要按市场价出手。卖房子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她能这样沉得住气,是因为目前她手头的钱还够支撑一阵。
业务员说:“你到底要租还是要卖?上次给你找到买家你又不卖了,然后我们给你付了一年租金,不到半年你又要卖,你这样属于违约知道吗?你先交违约金,把正式手续办了再进入卖房程序!”
舜茵说:“你们先帮我在网上发布一条信息,我半个月以后就回北京了。”
对方没有让步,舜茵叹口气,看到冯余站在面前,突然来了劲头:“您先回去帮我办吧,我把家里钥匙给您,房产证就在大衣柜右边第一个抽屉,包在一件蓝色睡衣里。”
冯余面无表情:“房子你不能卖,这是子辰买的。”“他已经送给我了。”舜茵解释,接着纠正了用词,“法律上属于赠予,已经是我的了。我有权利处置。”“你必须和他商量一下,没得到他同意之前你不能动。你的世界里是不是除了你老公就没第二个人了?你知道他的病有多严重吗?你知道这些钱和往水里扔没区别吗?等你把钱挥霍一空的时候,你拿什么抚养孩子们?”冯余看了看表,“我今晚的火车,该走了。钱的事我来想办法,子辰交给你。”
舜茵跟他一起往外走,冯余说:“不用送了。”舜茵说道:“不是送你,我去买苹果。”
医院门口有很多水果摊,舜茵挑了些苹果和梨子,往冯余包里装,给他火车上吃。往病房走的时候给周雯打了个电话,说:“你晚上在家干吗?没事就到医院找我玩吧,我家大宝贝住院了,我一个人挺无聊的。”
周雯问:“不是传染病吧?”“爱来不来!”
“不是,要不是传染病我就把我女儿一块抱来。”周雯的女儿长得不像周雯,更像小吴。舜茵刮了些苹果泥喂周雯女儿吃,周雯看见床上的子辰,使劲用手捂住嘴,好半天才挪开,依然是大张着,不过好歹把那声惊叫咽回去了。
“什刹海的神仙哥哥啊!”她有些口吃地说,“上次在黄山见你时怎么没提到他?你怎么把他拐回来的?还战胜了叶蓁蓁这个强敌,那女人居然没毁你容?”
“因为我艳压群芳,神仙哥哥看见我就丧失理智狼性大发,叶蓁蓁看见我自惭形秽羞愧而逃。”舜茵说,“你给我个卡号,那1万块现在可以还你了,这么多年加起来有不少利息呢,请你们全家去最好的饭店吃饭吧。”
周雯从女儿的小背包里掏出一只圆珠笔,凑到床头写。舜茵说:“干吗靠我们家大宝贝那么近啊?图谋不轨吗?”
周雯点头:“是的,借机一亲香泽。”交谈声甚微,但还是惊扰了睡梦中的子辰,半梦半醒之间看到床边伏着个女子,便伸手去摸那女子的头发,手刚到发顶,被另外一只手凭空拿住,舜茵喝道:“当着我的面就乱抓,皮痒了吧!”
周雯不满地白她一眼:“太小气了你!”子辰受了惊吓,半天才憋出一句话:“哦,周雯啊,好久没见了,你好。”
周雯满脸堆笑:“你好你好,病好了别急着走,我带你们四处转转,城里有不少名胜古迹呢,李鸿章故居、包公祠、逍遥津什么的。”
舜茵给子辰喂苹果,子辰把她拉近耳语:“你叫周雯出去,我要方便。”舜茵问:“要帮忙吗?”子辰摇头。
舜茵抱起周雯女儿,喊周雯到走廊说话。周雯边走边回头对子辰笑,又说:“不打扰你休息了,改天再聊。”
送走周雯,舜茵把病房打扫了一下,在床头收拾苹果皮的时候,摸了摸子辰的下巴,觉得有些扎手,她将垃圾袋拢起来绕了几绕,丢进走廊的垃圾桶里,洗了手,从抽屉里取出电动剃须刀来:“你一躺下,咱们的欧洲市场就完了。现在网店冷清了不少,出货慢多了,未奇临时帮忙发货,不过也不是长久之计。我想,网店做起来太慢,我还是去找工作吧,你在家带孩子们就行,家务事能做就做,不能做等我回来。”
“网店照这样下去,一个月一两万很正常,你找什么工作比这工资还高?”
“广告。”舜茵说,“钱越多越好。来得快。”“不行,拉广告怎么回事我太清楚了。人家凭什么把单子给你,我不能因为自己生病就卖老婆。”子辰夺过剃须刀自己在脸上推,“想都别想!”
“我问过医生了,你这个病不能说一点希望都没有,只要补充营养,是可以维持基本健康水平的,再说了,好多癌症病人还康复了呢,你这个总比癌症好多了。”舜茵说,“我保证不出卖自己,让我试试吧宝贝!”
子辰喷上须后水,舜茵说:“你瞧你吧,整天收拾自己,哪样不花钱啊!还不让我出去挣,你太不讲道理了。”
子辰把须后水往舜茵怀里一丢:“我不用就是了,这个比你那些东西便宜多了,我每次都给你买正装法国货!”
“谁让你买的!我用超市货就行!”“你用超市货,过几年再看看你的脸!那能一样吗!”“反正我要出去工作!”“行。”子辰说,“咱们算一下现在每个月的平均收入,如果你工作3个月以后低于这个平均收入,那你就辞职回家,继续做网店。”“拉广告有个铺垫过程,3个月太短了!半年吧!”省会的报社很有限,舜茵给每家都投递了简历,广告业务员是常年招收的,门槛也低,如果不要求保底工资的话,几乎是个身体健全能说话的都会得到试用机会。正因为如此,所以舜茵有些大意,虽然面试时做了准备,还是没料到广告部主任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你原来在北京的单位很好啊,首都的广告肯定比我们这里好做得多,你为什么不留在北京回省会了?是不是在单位犯什么错误了?像我们这种部门,最忌讳经济上有问题,你因为什么离开的?”
舜茵说:“是因为我结婚生孩子了,所以被原单位劝退的。”部门主任将信将疑,挠了会儿头皮,又问:“那现在孩子多大了?不需要你照顾吗?对了,你既然是因为结婚生孩子被劝退,老公应该是北京的吧?怎么跟你来安徽了?”
舜茵脱口而出:“我离婚了。”“那你现在上班,孩子谁照顾?”“我亲戚。”
“我觉得你形象气质都很好,而且见过大场面,特别适合我们这种工作。”主任说,“我想把你好好培养一下,成为合肥富人圈的名女人,你可别小看这个职业啊,这对个人综合素质要求特别高,我是看得起你才往这上面培养你。你可要努力学习业务啊,敬酒、唱歌、猜拳、按摩、打麻将,很多知识的,不过只要刻苦,我想你会胜任的,那时候你肯定会为自己自豪,而且,全合肥市的女人都会羡慕死你。”
舜茵说:“您太抬举我了,我肯定不是那块料,我也只能做个小业务员拉拉小广告什么的,3个月不出成绩,还得卷铺盖走人。”
“你太没远见啦!纸上的生意是看得见的小生意,真正大生意是看不见的,只要维护好客户关系,多少钱都不是问题,我也不会拿业务员的业绩考核指标来要求你。我俩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只要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
按现在的行情来说,如果这位主任句句是实话,那他确实还算是仗义的。业务员拉到广告后被部门借故开除,该得的提成拿不到,几乎是见怪不怪的事。这年头,别说是法外施恩了,只要事先承诺的能兑现,就算意外之财。
她说:“这行当吧,估计每家都差不多,我觉得您这人挺爽快,我也不去别的报社试了,就在您这儿先干着吧。我就是做业务员,您一切按规章制度来,拉不到广告我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