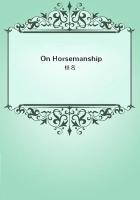下午和沈飞去了海洋馆,走在海底世界一样的高阔到直接穹顶的水族箱前,湛碧的水色映得人脸都微泛出蓝意,仿佛人在水间。
我和一条五彩斑斓的海鱼面面相觑一会儿后,正要走开,那条鱼居然先我一步甩给我一尾背影。
“啊!你这死鱼!到底是谁看谁啊啊啊啊!”拽的人是见得多了,阮清越、沈飞、卫凡,没有一个是好角色,欺软怕硬的天性让我不得不忍,可这鱼——
这鱼……
我的手还搁在水族箱的外沿上,冰凉的塑钢外壳像是突然有了粘性,让我收回也不是,不收更不是——
谁能想到阮清越竟然也会在这里呢?
就两个水族箱的距离,我和阮清越之间像是隔了透明的水带,谁也不能上前一步,却也不容退后。
肩膀忽然被人圈住,我下意识地回头——沈飞的衣扣正硌在我肩侧。
只差一点点,我竟然忘了身边还有另一个人。
“你还真找来了。”沈飞对着阮清越笑。
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努力镇定地假装自己其实很懂,心却一直一直地沉下去:不要,不要又是这样——商筱羽不能永远都这么惨,每一次都铁定了站错边……
“别拿筱羽当你的挡箭牌。”
“别拿你自己当别人的救世主。”
话说完了,两个人冷冷地互看。
三个人就这么不远不近地站着,海洋馆里的人来来往往,都像是不存在了,他们是鱼,是水草,是流动的水,而我们三个站成了水底的石子,站成了不透明的柱子,站成了可以无视却偶尔会被碰触到的玻璃箱壁。
别让我再错一次了。
手指不知道碰到什么东西,柔软的,清晰的——捉住了,是沈飞的衣角。
他低头看了我一眼,“别怕。”
我没法不怕:太失败了,原来爷爷根本不要我。用眼光就能让我自卑至死的姐姐、优雅温柔的孪生姐妹,我连她们的一根小手指都比不上。如果沈飞不是真的——阮家也不再要我,我要去流落街头吗?不管成为谁的游戏,其实我都玩不起……
眼睛看到一双鞋子,雪白雪白,在海洋馆黑晶色的水磨石地面几乎自己都要发出光来的样子,离我越来越近,一步,一步,再一步,最终停在距离我正前方一米不到的位置。
我的头几乎要坠到那鞋子上去。
“筱羽,”阮清越的声音从来没有这么轻软过,我的名字被他叫得好像真只是一片羽毛那样轻,让我几乎直觉地就想抬头看他,“跟我回去好不好?”
“小孩子都不会这么容易被拐走。”
阮清越突然捉住我手,不等我和沈飞反应过来,飞快地往我手里塞了一样东西。硬的,凉的,弯的——只凭手感,也隐约能知道形状。
我不可置信地抬头。
阮清越望着我,“离得太近了,东西掉下来没有声音。明明已经都在你手上了,我还要过了好几天才发现。”声音轻柔得让我像是飘在梦境。
近水楼台……
真的这么容易就可以得到了吗?
摊开手,安静卧在掌心的果然是一枚弯月,剔透、晶莹,微棱的弧线并不柔软,却美丽安静得让人心间仿佛有花朵缓缓绽开。
离得太近了。
太近了,太近了……
我扑过去时,阮清越全无防备,被我抱个正着,“这次不是我乱猜的……”
“嗯,家里的每一面镜子都是不说谎的。”
“哎?”
阮清越抬手摸了摸我的头发,“刚刚欺负你的是哪条鱼?我们一起看死它。”
最常欺负我的人,居然要和我站在同一阵线上了。鱼气我的程度,哪里有他厉害啊?
如果,这是梦,就让我一直睡着,永远不要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