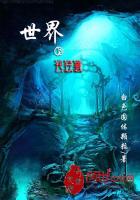现在扶苏身边一个人也没有了,而且神药也没有拿到,易铭又生死未卜。辅怡、辅以翔、扶苏商量里一下,再去试一次,若还不行,那就只有放弃了。
易铭躺在花城里,绿茸茸的草地软绵绵的,他的伤口已经被包扎好了。他站起来,环顾四周,寻找玭的身影。玭站在一棵松树旁,松针已绣了一地。
“玭姑娘。”
玭转身看易铭,问:“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字适合你。”
“你帮过我,我也救了你。我们两不相欠。”玭转身背对着易铭,似乎在下逐客令。
“我……,对你们学派的主张略有所闻,我能理解,但我不认同。”
“理解”,他居然敢说他理解,玭看着他,听听他还有什么花言巧语。
“你们把自己从这个世界分离了出去,认为自己不必对这个世界负任何责任。可是你们吃的、穿的、用的,都由这个世界供给。你们不是想修心,而是想逃避,逃避应该分担的责任。……如果你的心真能静下来,就吹不出那么动情的曲子。你宁愿把你的热情给这些草木,也不愿意把你的热情给人吗?”
“你说了这么多,不就是想要神药吗?”
“公子拿不到神药,秦王一定会杀了他。扶苏是万民眼中的希望,他若死了,老百姓就没好日子过了。你救了扶苏,就等于救了天下。当然,如果你真的做得到,不闻、不问,那我也尊重你,毕竟,师训如此。”
玭看着易铭,他的话没有惊涛骇浪般慷慨激昂,可是滴水穿石,才叫刻骨铭心。
流陌女扮男装,化名“莫弗”,卧底在兴隆客栈等待扶苏出现。可是,因为辅以翔的干涉,使这位手起刀落的杀手执行起任务来变得如此艰巨。
她回到了云岫,向中行无穷汇报工作。
流陌的女装,一如女性的丰姿。云岫的女人,都是飘逸的穿着。
这间石洞,摆设如若牢房,空气中有股莫名的寒气,令人心栗。
中行无穷走到流陌身边,低头看着她的双眼,除了怀疑,还有怜惜。
“你从来没有失过手,告诉我,这次失手的原因。”
面对中行无穷的质问,流陌显得很不安。她不会撒谎,很多事情,她会用沉默来掩饰。可是有时候,沉默并不能掩饰什么,相反,会吐露更多。
流陌的一举一动,都在中行无穷的掌握之中,是因为——辅以翔?
不是!流陌很快否决了中行无穷的假设,她的语速快得连她自己都惊呆了。一个冷血杀手,不应该有恐惧的时候。这证明,她撒谎了。
对着圣主撒谎,下场只有一个:中行无穷一巴掌狠狠地打在流陌的脸上,流陌趴在地上,指印鲜明,嘴角也破了。中行无穷扯下石墙上的鞭子,使劲地抽在流陌身上。
流陌是女儿身,哪受得了这般毒打?可是她的心,比钢铁还要坚硬,她从不会叫痛,哪怕皮开肉绽。
江氏兄弟进来,跪下给流陌求情。
“别管!”这是圣主的命令。
江乙和江丙挡在流陌面前,一鞭下来,江乙的脸上多了一道血痕,江丙的胸前也多了一道血痕。
流陌不懂,这与圣主对她的教诲背道而驰。这两个陌生人,为什么会在云岫?为什么会成为圣主的手下?为什么对她这么好?辅以翔也是。
中行无穷看这两个傻兄弟,怒火全消,把鞭子抛向身后,走出了石洞。
冰雪站在铁窗外,看着江氏兄弟,他们去找姝泉给流陌治伤,对流陌说话的语气像对中行无穷一样恭敬。
扶苏三人来到山脚下,须臾,易铭也来到了山脚下。看见易铭平安无恙,三人也舒了一口气。不过其中原委,并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的。求药一事,还得从长计议。四人便先回去,再定此事。
四人坐在屋子里,辅怡、辅以翔和扶苏你一眼我一眼,禁不住笑出声来。看来,易铭你是因祸得福啊!这是辅以翔的推测,也是辅怡和扶苏的想法。易铭老是被辅以翔取笑,又不肯承认,岔开话题,也是言归正传。扶苏会给玭姑娘一些时间,也是给他父王一些时间。
冰雪手捧着一瓶药向流陌走来,这是个陌生人,却又很亲切。流陌躺在铺着银狐皮的石床上,缓缓坐起身来。
冰雪坐到床边,先自报家门,免去流陌的戒心。
冰雪是一个办事妥帖的女人,她的言语使流陌温顺地解下自己的腰带,轻轻地脱下自己的上衣,袒露出伤痕累累的肌肤。冰雪从怀里掏出一块蕾丝,倒上点药粉,搽在伤口上。她的手法很娴熟,时而吹吹伤口,以至于流陌一点也不觉得痛。或许是有些痛的,可对于流陌而言,这算不了什么。
姝泉捧着托盘,上面是一些药瓶和绷带。她站在洞口,是嫉妒,是不甘,冰雪笼络人心的手段,令她讨厌。
她回到卧室,将托盘砸在石桌上。中行无穷正在挂剑对姝泉的做法甚感不解。
姝泉坐在石凳上,气得脸都红了,像涂了胭脂一般。
中行无穷走到姝泉面前,蹲下来拉着她的手,眉开眼笑地说:“谁惹你生气了?”
姝泉伸回手,摆在桌上,扭过头去,不理中行无穷。
姝泉好端端的发起脾气来,中行无穷也懒得哄她,站起来,两手背在身后,侧身对姝泉说:“你要是不怕长皱纹,就一直这样好了。”
姝泉一听,火气更大了。她一拍石桌,站起来,手拽过中行无穷的胳膊,说:“我问你,冰雪怎么在云岫?”
原来是因为这个,中行无穷一点惊讶,又觉得好笑。姝泉要他说清楚,理由很简单。
“她无家可归,怪可怜的。何况,她的家人是江氏兄弟杀的。”说到这里,中行无穷一脸的严肃,是同情冰雪,也带着怜爱。
中行无穷看姝泉怒色渐退,又嬉皮笑脸地问:“你不会这都吃醋吧?”
姝泉看着中行无穷嬉皮笑脸的样子,也只有在她的面前,中行无穷会表现出男人浪漫的一面。
“那你——什么时候让她走?”
“走?我没打算让她走啊!”
中行无穷对姝泉实话实说,从不做作,不知该奖该罚。稍微拐点弯,还是直接回答,一直是恋人之间的鸿沟。中行无穷却能永远都坚守这个准则,从不对另一半隐瞒什么。这是他犯的最大的错误,错得令人肃然起敬。
“你是不是喜欢上她了!”姝泉的声音很严厉,这挑战了中行无穷的极限,他不想再解释什么。
“你不要再无理取闹了。”中行无穷忘了,同样的话,同样的语气,他也对姝泉说过,原因是一样的。可是他也是大男子主义,女人的质问,只会令他反感。
“我无理取闹?”姝泉显得有些焦急,“你究竟让不让她走!”
中行无穷最恨被人威胁,他用从没有对姝泉说话的命令的口气,说:“我告诉你!她不会走的,要走,你自己走好了。”
中行无穷有男人的通病,情急之下,说话从不过脑子。他的心忐忑不安,怕姝泉真的会离开。
姝泉的泪珠在眼眶里打转,说:“好,这是你说的。”
姝泉走的时候,中行无穷呆若木鸡,没有采取任何补救的措施。
姝泉走出洞口,中行无穷打翻了石桌上的药、绷带、茶杯。七零八碎掉了一地。他恨姝泉不念旧情,但更恨自己。
江丙来找中行无穷,看见姝泉哭花了脸。
“姝姑娘,”江丙拉住姝泉的胳膊,问,“你怎么哭了?是不是和圣主吵架了?”
中行无穷听出江丙的声音,大声喊:“她要走,就让她走好了,你不要拦着她!”
打肿脸充胖子,是中行无穷最大的败笔。
姝泉挣开江丙的手,快步离开。她并非铁石心肠,因为她走的时候,在不停地抹眼泪。
玭下山了,她在渡口看老百姓如何受这些官吏的摧残,动不动就拳脚相加,根本没把他们当人看。才十三四岁的男孩子,被打得体无完肤,还得咬牙做苦力;已经是六七十岁的老人家,还得驼着背拄着拐杖背粮食,一不小心摔倒了,还得充当人面兽心的官吏的出气筒;妇人给自己的丈夫送来午饭,那些官吏不仅扣下妇人的饭菜,还对她毛手毛脚,他的丈夫忍无可忍,被官吏们群殴,活活打死,妇人哭天喊地,声震霄汉……
明明人手不够,还如此草菅人命,这些官吏若没有上司默许,哪敢如此嚣张?秦王暴政,人人有目共睹。众目睽睽之下残害无辜也屡见不鲜,明哲保身者见而言之;稍微有点良心的人欲伸张正义,往往也把自己的命都搭进去。
这就是世道的颓凉。
人皆以为是嬴政一手造成的风气。一代帝王,有责任,有义务,即使毫不知情,也必须承担这个罪名。
玭捏紧拳头,她做不到置身事外,做不到视若无睹。可是她人单力薄,根本改变不了什么。想到这儿,她怪自己的软弱,怪自己的无能……
易铭出现得很及时,他给玭指引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交出神药,帮助扶苏。
玭一下子陷入了进退维谷的绝境,一方面是不管世事的师训,一方面是生死皆悲的贫民。她做出艰难的抉择,感动了上苍。
天雨骤急,“沙沙”落地,湿了尘土,也湿了人心。
百姓冒着暴雨,依然来回搬运粮食。玭摘下兰花型的翠玉项链,重重地扔在地上。
项链碎了,“兰花”谢了,一颗药丸在接受瑞雨的洗礼。
玭离开了这里,她本来就不该来这儿。她帮了扶苏,于自己无益,而且犯了门规……
盛夏的雨说来就来,说走就走。莫弗在绿茵草原,湿漉漉的草坪像婴儿的肌肤一样润滑。辅以翔来了,见到莫弗,他很高兴。
莫弗看他的眼神,使他想起黑衣女子的双目。
他两手搭着莫弗的肩膀,莫弗的身子有意地避开。
“你怎么了?”辅以翔抓着莫弗的胳膊,没轻没重的,“你又被客人打了?”
辅以翔问莫弗,莫弗没说话。
“很严重吗?让我看看!”
辅以翔说着要脱莫弗的衣服。莫弗是女人,自然是不能给他看的。可辅以翔一再坚持,莫弗摇头晃脑,头巾掉下来,黑发也散下来。
听啾啾的虫鸣,看油油的绿树,辅以翔忘记了,他抓着的是一个女人。
辅以翔慢慢伸回手,莫弗很美,可是他不敢太靠近,他怕这个女扮男装的莫弗,是他一直在寻找的流陌。
他没有问,莫弗已经承认,她是一个女人。
“‘莫弗’,是不是你的真名?”
“不是。”莫弗回答的时候,辅以翔的身躯颤动了一下。他不敢再问下去,那就让这个问题永远留在心中吧。
“中行无穷灭了天蝶岛,实力大增,你觉得,流陌还会不会来杀扶苏?”
“不会。”
“谢谢。”
辅以翔与莫弗疏远了。
莫弗低下头,长发飞扬,令人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