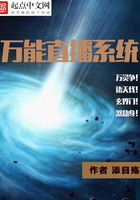先前,蒙蔽双眸,之后,背对而出,即便是独处在宗祠那俩时辰,由于搞不清状况,动不敢动,言不敢言,愣是杵着小憩到流哈喇子都无人“问津”,可以说,这糗事算是破了前二十三年的“清白”记录。
懒散到一思及此,古宓不觉便会脸红脖子粗,尴尬到有种无地自容之感,心中一个劲在叨唠“罪过啊罪过”这五个字眼,几遍重复下来,反倒觉得自个染上了某种啰嗦絮叨之瘾。
原本,身处这好山好水之境,面对的是好风好光好景好情,古宓对于这个一时疏忽所犯下的小小失误深感愧疚,加之甚有自知之明晓得自己本就一冒名顶替者,心下更是虚惶。
篡了这个位子,貌似也间接性承接了其旧主人本性上的某些缺陷,譬如脾性,现在的古宓,难明缘由的,一改了昔日那份果断干脆,自从被摄来这犄角旮旯之地,一而再的三番屡次优柔寡断,末了方别无它径迫于无奈痛下决心,暂时挑起这一谷之长的破差事。
依现状断来,无怪乎当初那么难以抉择,而今的混沌局势,愈发上演的难以预料,越来越含糊超乎所能意料之及。
话说,要虔沐,偶依照谷规去了那禁地,顶着月光泡了足足一个时辰;要跪拜,偶遵循祖制来了这犄角,忍受这披挂那包裹,遭受非正常级别待遇,权当风俗可以挨,这些繁琐周折可不值得一提,白捡一个席位自然须得付出些许。
那个,虽然,这跪拜行的有些牵强,到目前这一时刻为止,既没屈膝也没叩头,倒是一不留神跟周公约了个小半响的迷糊会,也已汗颜地默默在心底比划过十字架,做过间接性祈祷表明自谴悔意,常言道,那什么还有打盹的时候,何况古宓向来自认自个只是一个简单到只想过活之人。
大典在即,以上通通不足多做计较,相较之下也不值得加以追究,现下,刺激神经的是那突兀赫然之字——巫。既是宗祠,单揣测字面意思,应该是比较郑重之所,何以冠之于如此一非褒义之词?据自身所知所解,与之流传至今的相关词藻,貌似无一不多贬义,谈及色变者不乏少数,仔细回顾一番,不管哪个朝代亦或年代,与之沾边的物与事好像都没什么好下场,怎的还敢如此明目张胆无半点隐讳工笔正规纂刻?难不成,超凡只是假象,脱俗只是幌子,这,方是其掩盖的本质所在?
径自沉陷在浮想联翩的思维纠结之中,古宓还在搅这扰那的犯嘀咕,正在忧心,倘若真如自个所猜测那般,那自己这会身兼这一谷之主高帽子,岂不变相的成为巫合之主,甚难想象那该是怎样的一个烫手山芋般头衔,矛盾着如题之类的问题,她根本没留意到周遭与此同时发生的一系列进展与变化。
那边,西北方向,穿插着的一根根火把,由自一个圆点处,一一点燃蔓延,逐渐环绕成一个线条柔和的巨大阵势,形状,比三角形圆润些,比椭圆形分明些,融合了线条上的柔与刚。
噼里啪啦地木屑声,随着飞舞的零散火星不间断作响,待得那阵低缓冗长的角号声过后,清一色伏地的青衣齐刷刷高举起衣袖,就地一连做了三个跪拜,而后,渐渐明朗地拉开了一幅甚为清晰的画卷。
从宗祠入槛点稍俯首看过去,片片青衣汇集而成的,是一个不甚熟悉的图案,确切的讲,是一滴缓缓流动的青泪。
长衣袖一挥,抛向半空的那一刹那,好似泪滴滚落前一秒,终极一线的膨胀之态,那感觉,正应了“只可意会”一词。
恰似凌晨叶脉上徒留的点点晶莹,迎着东方迸射的第一缕光线,浮动着流淌凝结的一刻,交集成一颗无暇的剔透盈亮,随风倾斜的那一瞬,划过的一道绝美弧线。
眼见那边虞侍首紧随祠中三方长老入了殿内,雉儿瞅着依旧丝毫无反应,尚在面无表情杵着的自家主祀,藏在袖内的小手不由得冒冷汗,不明了为何自家主祀这两日总是在莫名其妙的溜神,没事时开开小差也就罢了,这关键时刻,神思怎的可以一次又一次晃了又晃。
干着急于事无补,雉儿便心急如燎地暗拉暗扯了不下十几次,最后实在是忍不住,便把持着加大了些气力掐了两下那倍感僵硬的藕臂,使个眼色,紧压着嗓子提醒道:“谷主,回魂了。”
这一语,虽没能完全惊醒迷糊着的古宓,跑路的大脑也有了分恍然,胳膊被牵引着,古宓人也已经被雉儿拽着向前迈开步子,第二次跨过那道木槛,返回至了那间所谓的宗祠内间。
一柄方形烛台,映亮着一张古朴的红木方桌,有分眼熟,似乎在哪里见过,只是,乍一见,古宓却一时找不到头绪,但十分肯定自个的确有见过那两样东西。
“古谷第七代谷主,西,宓主祀,接印石。”
苍老而富有魄力的语调,一触及耳膜,古宓身心同一刻俱颤,脑海残存着的种种余念顿时清除的无影无踪,脖颈迅急转向声源处。
灰暗的角落,倾注而撒的黯淡月光下,一双矍铄的眼睛,凹陷在一张略微瘦削的脸孔上,花白的发丝,梳散着,长及两侧至腰身,即便是相隔着五六步远的距离,依旧可见那满布的条条皱纹,以及,隐含的那份复杂之容。
这个声音,当真的不甚陌生,曾经,夜夜纠缠过,曾经,日日冥想过,时时为之烦恼过,刻刻为之焦躁过,毋庸质疑的确定,她,就是那个人,那个始终疲倦搅扰者,那个挑动猩红血管节拍者,就是她,那个召唤者。
“主祀,族长传印石,行承袭之礼。”眼角窥一眼着那又开始发直的细眸,雉儿忍不住使劲捏了捏自家主祀的腕臂,一张小脸也因过于激动和紧张一会发青儿一会发白。
以往,不曾有机会没见过这种大场面,雉儿心底本就没谱,本来还以为自家主祀该比自己知礼节的多,没想到一环环走过来,才发现···幸亏提前有私底下向虞侍首请教了几点,不然,就冲自家主祀目前这股子难预料的出窍劲儿,指不定会搞出多少乱糟事儿。
庆幸归庆幸,担忧归担忧,不过,雉儿个人总觉得哪里有些怪怪的,自从自己主祀遵照已逝老谷主遗嘱,一行水谷涧竞选,神佑归来之后,很多方面,貌似均有所改变。较之他人,雉儿自认更了解这个一直陪伴侍奉在左右的主祀是怎样一人,可是,归来的谷主,却摸不透了。
有时,自觉连她这个近身女侍都甚是难以理解的会冒出些微生疏之感,音貌没有半点改变,连右耳垂际被预言为印记的黑痣胎记均无异样,那种感觉是怪异的,想破脑袋也理不清,莫非当应那句谷语,凡入得涧,出得涧者,皆脱胎换骨?
惟有熟悉之人,方可于细节有所作疑,但是,也仅能限于这一点,因为雉儿根本难猜到,她眼前的主祀,已不是原来之人。
丝丝的疼痛,抽离回遣失的感性,古宓手脚不带半点知觉的同步向前,似被某种莫名的潜意识使唤着,颔首,低眉,打揖,一气呵成之际,眉梢却斜睨到一束一晃而闪的光泽。
纯白的吊坠,底端悬挂着的,是那枚跟印迹中相吻合无误的水琉璃。
记忆的潮水,当即一波波袭来,红头绳,瑟残阳,钢齿桥,古榕树,地下吧,石级,拱门,面具,白衣,木盒,廊桥,包房···
心头一抽搐,古宓手指一滞,再转向那方桌、烛台,顿时有了一丝释然,怪不得,何止是见过,在那所网吧,有坐过好几个小时。
“古相坊。”思索着,这三个字随即喃喃出口,古宓心头添了一分喜悦,总算忆起这个名字,就是在那,被莫名其妙摄来此处,成了迷迷糊糊的穿越女。
穿越?
古宓张嘴深舒口气,堵塞在胸口的那股憋闷勉强减缓两分,此时,恐怕再难百分百坚持这个说法。
先前以为的现实,忽然觉得没了真实可追寻,信以为虚的此刻,蓦地加重了太多深切的齿轮,到底,哪一个是幻,哪一个是影,孰为真,孰为假,何原,何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