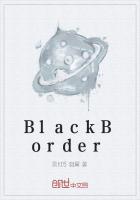一路的原人木屋门前皆堆叠了好多积雪,还有些精神遭受冷冬连累的晚起原人们,还在病恹恹地扫除冻住门框的冰霜。牧仁经过时,这些原人们仿佛视而不见,甚至他皮袄的一角被路边的手撩碰,也像是一道空气被忽略。
不受人耳目所闻,是“蜘蛛”的素养。也看不出牧仁对此是否满意,他的表情暗沉,也当原人们是空气,径直走过他们。又快步走过古祷房和兽场,终于来到卜筹轮放置的二层平台正下方,一个那钦手下的战士将他领向部落大门,但直到临近门口被一个莽夫撞到前,两人都一言不发。
若不是这个莽夫是胡和鲁的鬣狗,牧仁也想像假装失语的残废一样,悄然规避一起冲突。只见鬣狗抓住密使的肩膀说道:“门口的赤豺快饿疯了,七个原人被它们咬伤,扎昆·那钦都不管吗?”那傲慢的模样就好像在说“你的主人也只配给我的主人鞍前马后”。
这位莽夫身上破烂的模样已经形同一个野外与野兽争食的拾荒者,穿着一件千疮百孔被虫蛀的皮袄子,原本紧束的头发垂挂在耳边,头上的骨盔缺了一半。
“我险些成为第八个人。”后怕令他此刻声音里带着愠怒。
牧仁知道鬣狗是一直坚持出猎的战士,哪怕是初冬后部落明令的禁猎也从不遵守,他认为在这个大型聚落尚未建造前,原人可没有忌惮过那么多规矩和禁忌。
“请问扎昆·那钦在哪里,我要求一个说法!”牧仁没有立刻理会,他便显得更加愤怒了。
“大雪后的半月内是禁猎期,你和那七个原人没有被抓起来严罚,反而被作为兴师问罪的借口,也太胡作非为了吧?”边上的战士忍不住说道:“你是不懂部落的规矩,还是刻意透过那钦藐视拟定规矩的苏日勒和克及五位金乌?”
“我是奉胡和鲁的命令沿部落接连的水渠外出寻找问题,和狩猎有什么关系?”
“水渠会有什么问题?”那战士嗤之以鼻,一条人造的小河罢了。
“流量,畅通,决口,污染,是否影响母源大泽,哪一个不是问题?”
“这——”
鬣狗牵起上唇的肌肉,勒出一个丑陋的笑,像一张畸形的虎脸。“我为金乌们尽职尽责,那钦和他底下一群战士却仗着与尊敬的苏日勒和克关系亲密,疏于职守,留着门外的赤豺群和土墙上的积雪而在这里偷闲。我想恐怕是你们更加怠慢了部落的信任吧?”
那战士一听,急了,鬣狗的话分明是打算向尚留在部落的胡和鲁和长风参上他们的罪状,而士倌扎昆·那钦近日确实没有来得及吩咐事宜便匆匆离去,若金乌们责问,他们有口难辩。
“扎昆·那钦大人不在部落,因此扫雪驱兽的工程延缓了。”牧仁接过话茬:“这是我的失职。”
“我还想问你是谁?是扎昆·那钦的手下吗?”
“我是他的朋友,他将事宜暂时委托给我,我却忘得一干二净。”牧仁大方地把所有过错揽到自己身上,毕竟对于大多数原人而言,自己只是一只“蜘蛛”,而谁也无法从暗影里将自己揪出。“那钦大人外出约摸五日时间,所以这件事情与他完全无关。”
果然鬣狗再没有什么话好倚仗,看着那钦手下的战士和这个所谓那钦的朋友直发愣,然而对于莽夫而言,眼珠子无论转多少圈,也转不出另一个好对策。只听他嘟嘟囔囔道:“见鬼的初冬,万能的有事外出。四个金乌,两个士倌都不在,还包括我们尊敬的领袖苏日勒和克。可要是出了大事,该怎么办?”
“尊敬的阿拉图德·胡和鲁不是还在领袖大殿里?”他声音一顿,一个披着兜帽的男人擦着身边走过去,那家伙似乎没有头发,白蓝色的面容一见他的眼睛便连忙垂下头去,不经意间加快脚步拐入小巷中。
可鬣狗没有注意到男人,他被牧仁的话所吸引,于是凑了上来,恰好挡住兜帽男人的行踪。“是啊,没他坐镇,其他人怎敢这时放心外出,阿拉图德·胡和鲁——部落的中流砥柱。”他不遗余力地赞颂自己主子,把身后的猎到的动物毛皮给不小心露了出来也没发觉。见那钦的人忽然嗤嗤偷笑,赶紧严肃道:“我要去回禀胡和鲁大人有关水渠的问题了,你还是快点吧,别等尊敬的胡和鲁大人亲自接管这档子破事。”
我应该告诉你,以后该披一件大些的皮袍子藏匿猎物,而不是穿着皮袄害得自己整个上身塞得鼓鼓囊囊。只一眨眼的工夫,牧仁就寻不到那个兜帽男人,这让他大为光火,而胡和鲁的鬣狗也如斗胜的莫古鸟在他的注视下昂首阔步向内离去。
那钦的战士疑惑地见他原地转了一圈,脑袋却像是要挣脱脖子的束缚般伸得极远,接着又奔到几步路外的小巷口,口子里的一张脏兮兮的破布、一罐酸酒和一只死鸟都没有逃过他的检视。可惜一无所获,这些不过是“原人所为”。他放弃了显得行为怪异的追查,也没有告诉战士有关兜帽男人的事情,即使那身不属于原人的装扮实属可疑,但这类事并不算在他的职责范围内。“蜘蛛”归“蜘蛛”,就该藏匿风声,而那钦的战士们才是“猎豹”,既然“猎豹”们的鼻子没有嗅到异味,就代表着天下太平。
战士赶上牧仁,他们的目的地不在这里,应该在远处的部落大门。
“有什么问题吗?和胡和鲁的手下有关?”战士自然还是会问,然而只要不是图图赫之流,想要从牧仁吝啬的嘴里抠出情报,基本是妄谈。“我们不该给他好脸色看,作为领袖的忠实助手,那钦的手下不该对胡和鲁的手下笑脸相迎,谁都知道,最近胡和鲁似乎想要弹劾尊敬的苏日勒和克。”战士又说,对牧仁方才没有为那钦挣得颜面而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