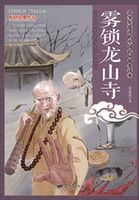现在一切都无关重要:到不到佛斯德维任斯考去,得到得不到丈夫的离婚——一切都不需要了。需要的只有一件——处罚他。
当她倒出平常服量的鸦片膏,并且想到只要喝完这一瓶就可以死的时候,她仿佛觉得这是那么容易而简单,因此她又欣喜地开始想到,他将怎样地痛苦,追悔,爱她的亡灵,可是太迟了。她躺在床上,睁开眼睛,在一支快要点完的蜡烛光里,望着天花板的雕刻的凸出线条,和遮蔽着一部分天花板的屏风影子,她生动地想象着,在她不复存在,而她对于他只是回忆的时候,他将感觉到什么。“我怎么能够向她说了这些残忍的话呢?”他将这么说,“我怎能够什么话也不向她说,就走出了房间呢?但现在她已经不在了。她永远离开我们了。她在那边……”忽然屏风影子动摇了,遮蔽了全部的凸出线条,全部的天花板,别的一些影子从另一方面向它奔去;顷刻之间影子都跑开了;然后更加迅速地向前冲,动摇,合并,一切都黑暗了。“死!”她想。她感觉到那么大的恐怖,以致她好久不能够明白她在什么地方,好久不能够用颤抖的手找到火柴,点着另一支蜡烛来代替那支点完的熄灭的。“不,无论怎样——只要活着!我爱他呀!他爱我呀!过去是这样。就会过去的。”她说,觉得回生的喜悦之泪在她的腮上流了。于是,为了脱离自己的恐怖,她连忙走进他的书房。
他在书房里酣熟地睡着了。她走到他身边,打上边照着他的脸,久久地望着他。现在,当他睡觉时,她那么爱他,她一看见他就不能够制止温柔的泪;但是她知道,假若他醒来,他便要用冷淡的自以为是的目光望着她,而她在向他说到自己的爱情之前,会向他证明他是多么对她不起。她没有弄醒他,回到了自己的房里,在第二次吞服鸦片之后,在黎明之前,她睡了不舒服的不酣熟的觉,在全部睡觉时间里她不断地半醒着。
早晨,那可怕的噩梦,在她和佛隆斯基发生关系之前就梦见过许多次的,又向她显现,把她弄醒了。一个胡须蓬乱的老人,对一块铁弯着腰在做什么,说着无意义的法语,像她一向在这个噩梦里那样(这就是它可怕的地方),她觉得,这个农人不向她注意,却用铁在她身上做着什么可怕的事情。她在冷汗中醒了。
当她起身时,她想起了好像在云雾里的昨天。
“有了一场争吵,正是发生过若干次的事情。我说我头痛,他没有进来。明天我们要走了,必须看到他,准备动身。”她向自己说。听说他在书房里,她便去看他。穿过客厅时,她听到大门口有马车停下来,从窗子看出去,看见了一辆轿车,一个戴淡紫色帽子的年轻姑娘伸出头来,向按门铃的听差吩咐什么。在前厅的谈话之后,有谁上楼来了,又听见了佛隆斯基走过客厅的脚步。他快步地下了楼梯。安娜又走到窗前。他正走上台阶,没有戴帽子,走到马车前。戴淡紫色帽子的年轻姑娘给了他包东西。佛隆斯基微笑着向她说了什么。马车走了,他迅速地又跑上楼梯。
在她心里遮掩了一切的云雾忽然消散了。昨天的情绪带着新的痛楚压痛了烦闷的心。她现在不能够明白,她怎么还可以屈辱自己,和他在他的屋子里过一整天。她走进书房去看他,向他说明她自己的决心。
“这是索罗基娜和她的女儿顺路经过这里,从maman(妈妈)那里带了钱和契约来给我。我昨天没有收到。你的头怎样,好些吗?”他镇静地说,不愿意看见也不愿意了解她脸上的愁闷而严肃的表情。
她站在房当中,默默地注意地望着他。他瞥了瞥她,皱了一下眉,继续看信。她转过身,慢慢地走出房间。他还可以使她回转,但她走到了门口,他仍然沉默着,只听见翻信纸的窸窣声。
“是的,顺便讲一下,”在她已经到门口时,他说,“明天我们一定走吗?是不是?”
“您去,我不去。”她转头向他说。
“安娜,这么过下去是不行的……”
“您去,我不去。”她重复说。
“这叫人不能忍受了!”
“您……您要懊悔这个的。”她说,走了出去。
他被她说这话时的绝望的表情所惊骇,跳了起来,想跟她跑去,但是他恢复了镇静,又坐下来,咬紧了牙齿,皱了皱眉。他认为这种有失体统的、有所举动的威胁使他愤怒了。“我试过了一切,”他想,“剩下的一件事就是不注意。”于是他开始准备到城中心去,再到他母亲那里去,要她在委托书上签字。
她听到他在书房和餐室里的脚步声。他在客室里停住了。但他没有回来看她,只吩咐了,他不在家时,可以把马让佛益托夫带去。后来她听到预备马车,开门,他又走出去。但他又走进门廊,有人跑上楼。这是侍仆跑来讨取忘了的手套。她走到窗前,看见他眼不望人就接了手套,摸了摸车夫的背,向他说了什么。后来,没有望窗子,他就照寻常的姿势坐在马车上,腿架着腿,在戴手套的时候,在转角上不见了。
二十七
“他走了!完结了!”安娜站在窗前向自己说。回答这个问题的,是蜡烛熄灭时的黑暗的印象和可怕的梦的印象,合而为一,在她心里充满了冰冷的恐怖。
“不,这是不可能的!”她叫着说,穿过房间,用劲地按铃。她现在是那么怕孤独,没有等到仆人进来,她就走去迎接他。
“去问问,伯爵到哪里去了。”她说。
仆人回答说伯爵到马房去了。
“他吩咐说,假若您要出门,马车马上就回来。”
“好。等一下。我马上写个字条。叫米哈益把字条送到马房去。赶快。”
她坐下来写了:
“我不对。回家来,必须说明。看上帝情面,来吧。我怕。”
她封了起来,交给了仆人。
她现在怕剩下她一个人,她跟着仆人走出了房间,走进了育儿室。
“呵,这个不对,这个不是他!他的蓝眼睛,可爱的羞怯的笑容哪里去了?”这是当她看到有黑鬈发的肥胖红润的小女孩,而没有看见塞饶沙时的第一个思想,她在思想混乱中原是期望在育儿室里看见塞饶沙的。小女孩坐在桌上,顽强地用力地在桌上敲塞子,用两只醋栗般的黑眼睛无意义地望着母亲。安娜回答了英国保姆说她十分好,说她明天要下乡,她便在小女孩身边坐下,开始在她面前旋转瓶塞子。但是小女孩的高声的响亮的笑和她的眉毛的动作,那么生动地使她想起佛隆斯基,她压抑着呜咽,连忙站起身走出去。“难道一切都完了吗?不,这是不可能的。”她想,“他要回来的。但是他怎么能够向我解释他和她说话以后的那笑容、那兴奋呢?但是即使他不解释,我仍然要相信。假若我不相信,那么,留待我做的只有一件事了——但我却不愿。”
她看了看表。过了十二分钟。“他现在接到了我的字条,要回来了。不久,还有十分钟……但是假若他不回来,又怎样呢?不,这是不可能的。一定不要让他看见我的哭过的眼睛。我去洗脸。是的,是的,我梳了头发没有?”她问自己。她不记得了。她用手摸摸头。“是的,我梳过了头发,但是在什么时候,简直记不得了。”她竟不相信自己的手,走到穿衣镜前;看看她是不是真梳了头发。她是梳了,但她想不起来是什么时候梳的。“这是谁?”望着镜中兴奋的脸和异样地、明亮地、惊惶地向她望着的眼睛,她想。“哦,这是我。”忽然她明白了,她望着自己周身,忽然在身上感觉到他的吻,她颤抖着,动了动肩膀。然后她把手举到唇边吻着。
“怎么回事,我发狂了。”她走进卧房,安奴施卡在里面收拾房间。
“安奴施卡。”她站在她面前望着侍女说,自己却不知道向她说什么。
“您是想去看达丽亚·阿列克三德罗芙娜?”侍女好像是明白她的意思,对她说。
“去看达丽亚·阿列克三德罗芙娜吗?是的,我要去。”
“去十五分钟,回来十五分钟。他已经来了,他马上就要到。”她掏出表看了看。“但是他怎么能够让我这个样子就走开了?他怎么能够不同我和好而生活呢?”她走到窗前,开始看街道。按照时间,他已经可以回来了。但是计算也许不准,她又开始回想他什么时候走的,并且数着分钟。
在她走到大钟那里去对表的时候,有人坐车来了。她从窗子望出去,看见了他的马车。但是没有人上楼梯,可以听到楼下的声音。这是送信的人坐车子回来了。她下去看他。
“没有找到伯爵。他到下城铁路车站去了。”
“你说什么?什么……”她向红润的、快活的、把字条递回给她的米哈益说。
“呵,他没有接到。”她想了起来。
“把这个字条送到乡下佛隆斯卡雅伯爵夫人那里去,知道吗?马上带回信回来。”她向信差说。
“我自己,我要做什么?”她想,“是了,我要去看道丽,这是真的,不然我要发疯了。是的,我还可以打电报。”于是她写了这个电报:
“我须面谈,即来。”
送出了电报,她去换衣服。她换了衣裳,戴了帽子,她又看看肥胖的安静的安奴施卡的眼睛。在那双善良的灰色的小眼睛里可以看到明显的同情。
“安奴施卡,亲爱的,我怎么办呢?”安娜呜咽地说,无能为力地坐进靠臂椅里。
“为什么这样难过呢?安娜·阿尔卡即耶芙娜!这是常有的。您出去走走,散散心,提提神。”侍女说。
“是的,我要去,”安娜提起着精神,站起来说,“我不在家时,若是有电报,就送到达丽亚·阿列克三德罗芙娜那里……不,我自己回来。”
“是的,不应该想,应该做出什么,坐车出去,最重要的,离开这个屋子。”她说,恐怖地谛听着她的心脏的可怕的跳动,连忙出门,坐上车子。
“吩咐到哪里?”彼得在爬上驾驶台之前问。
“到以那明卡街,奥不郎斯基家。”
二十八
天气明朗。密密的细雨下了一早晨,此刻晴了不久。铁屋顶,行人道上的石板,马路上的砾石,马车的轮子与皮革,铜与锡片——一切都在五月的太阳下明耀地发光。是三点钟,是街上最热闹的时候。
坐在急驰的灰马所拖的、在柔和的弹簧上微微摇簸着的舒适的轿车角落里,安娜在不息的车轮辚辚声中和户外的迅速更换的印象中,重新回想着最近几天的事件,看到她的地位和她在家里的时候所感觉的完全不同。现在死念对于她不再显得是那么可怕,那么明显,而死本身也不再显得是不可避免的。现在她为了自己所降到的屈辱而责备自己。“我请求他饶恕我。我向他屈服了。我承认了自己不对。为什么?难道我没有他不能生活么?”她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她没有了他,她将如何生活。她开始在看招牌。“事务所与仓库。牙医。是的,我要向道丽说一切。她不欢喜佛隆斯基。我会觉得羞耻的,痛苦的,但是我要向她说一切。她爱我。我要听从她的意见。我不向他屈服;我不让他教训我。非力拨夫,面包店。人说,他们把面粉团运到彼得堡去。莫斯科的水是那么好。呵,梅齐施清的井水和薄饼。”
于是她想起,很早很早以前,在她还是十七岁的时候,她和姑母到特罗伊擦修道院去。“是骑马去的。那时候还没有铁路。那个有红手的人果真是我吗?那时候我觉得是那么优美而难得的东西有许多变得没有价值,而那时候所有的东西现在是永远地得不到了!我那时候会相信我会落到这样的屈辱吗?他接到我的字条,会多么骄傲而满意啊!但我要向他表示……那个油漆气味多么难闻!为什么他们老是油漆建筑呢?时装与衣饰。”她读着。一个男人向她鞠躬。这是安奴施卡的丈夫。“我们的寄生虫。”她想起了佛隆斯基怎样地说了这话。“我们的?为什么我们的?可怕的是不能够把过去连根拔除。不能够拔除它,但可以隐藏关于它的记忆。我要隐藏它。”这时她想起了她和阿列克塞·阿列克三德罗维奇的过去,想起了她怎样地把它从她的记忆中忘去。“道丽要以为,我要离弃第二个丈夫,那么一定是我不对。就好像我想要证明我对似的?我不能够!”她说,她想要流泪了。但是她立刻想到那两个姑娘在笑什么。“大概,是爱情吧?她们不知道,那是多么无趣味,多么卑下……树荫大道和孩子们。三个小孩子在跑,在玩木马。塞饶沙!我失去了一切,我不会把他找回来的。是的,假若他不回来,我便失去一切了。他也许到火车站迟了,现在已经回来了。又想要屈辱你自己!”她向自己说,“不,我要去看道丽,直接地向她说:我不幸,我该受的,我错了,但我仍然是不幸的,帮助我吧。这些马匹,这辆马车——我在这辆马车里是多么厌恶我自己——都是他的;但是我不要再看见它们了。”
安娜想着她要向道丽说出一切时的言语,故意地激昂着自己的心情,走上了楼梯。
“有什么人吗?”她在前厅里问。
“卡切锐娜·阿列克三德罗芙娜·列文娜。”听差回答。
“吉蒂!就是佛隆斯基爱过的那个吉蒂,”安娜想,“就是他常常爱恋地想到的吉蒂。他懊悔没有娶她。但是他憎恶地想到我,并且懊悔和我结合。”
在安娜来访时,两姐妹正在商量喂养婴儿的事。道丽独自出来会见这时候打断她们谈话的客人。
“呵,你还没有走?我本想亲自去看你,”她说,“今天我接到了斯齐发的信。”
“我们也接到了电报。”安娜回答,回头望着,想看见吉蒂。
“他信上说,他不明白阿列克塞·阿列克三德罗维奇究竟想要怎么办,但是得不到回答他不会走的。”
“我想你这里有什么人。信可以看吗?”
“是的,是吉蒂,”道丽窘迫地说,“她住在育儿室里。她害了很重的病。”
“我听说。可以看信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