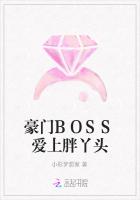躲在山中的刘邦得到陈胜吴广造反的消息,终于出山了,他大胆地来到了沛县城下,一纸劝告书攻开了城门,杀掉了县令,自己当上了沛公,终于走上了起义之途。
需卦。彔曰:需,须也,险在前也。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需有孚,光亨,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四
私塾先生给刘季取的大名,是单字一个“邦”,先生说道:
“邦也是国,国也是邦,既然这个孩子将来有出息,那就叫他刘邦吧。”
继后,人们等到刘邦得到天下之后,把那些故事与传说连了起来,有了一个编撰的说法,那就是刘邦是赤帝化成神龙,在那一个风雨交加的晌午与王含始相交而怀了孕,生下的儿子。那白帝之子欲与赤帝之子争天下,化成了一条白蛇阻于道上,却被刘邦在酒醉之中砍杀了。这故事是真是假,今人已无从考究。
然而,这个刘邦却很叫他的老爹失望。
他确比两个哥哥既聪明又淘气,却不能把聪明用在正点子上。
大哥刘伯、二哥刘仲都还如父如母,人十分老实,只懂得安分种田守家。唯独这个老三刘季有那么一点儿“混账”。开蒙之日,刘家与卢家合资共请了一个私塾先生,让这两个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的孩子一起读书。那卢绾(卢家孩子的名字)还好,也肯念书,也不调皮;而刘邦却一见书本就犯困,不是逃学就是捉弄先生。叫他务农吧,连耙犁耜锄也像是拿不动似的。他惟一的职业就是领着那帮狐朋狗友到处游荡。
最糟糕的是没过多久,他把那个卢绾也带坏了,让卢绾总是充当着他的帮凶或随从。
这时,王含始得病去世了,刘执嘉虽然怀念老妻,却又娶了一个后妻,生下了一个叫刘交的男孩,这是他们家里的老四。
―天,卢绾的老爹找到了刘执嘉的家中,对刘老爹说道:“刘兄,我听说你们家的孩子不好好念书,还把绾儿给带坏了,现在气得私塾先生不肯再教,已经卷起铺盖回家去了,你说这怎么办呀?”
“我们家季儿我看是没指望了,只得随他去吧,我。当是没生这个儿子。”
“你这样说,我也没有办法,我们家绾儿总得让他再念点书,将来图个出息。要不,咱两家还是凑点钱,一起请个先生。你有四个儿子,总不能都是这个样子吧,你就把老四送去念书吧,虽然他现在年纪小,但也是个聪明孩子,将来就指望他吧!”
“他还没到开蒙的年龄呢。”
“那怕什么,让他先读着呗。”
刘老爹觉得在这件事上有些对不起卢家,所以同意自家也出一份钱,算是对卢家的一种道歉吧!
“那敢情好,就让交儿陪卢绾去念吧!”
听说私塾先生走了,老父不再逼他念书了,那刘邦反而高兴得要命,像是过了一个年节那般痛快。
不读书,也不务农,刘邦就整天价地东游西荡,不干正事。不但如此,他还纠集了五六个半人不小的小子,自己做起了“孩子王”,领着他们到处去打抱不平,惹是生非。
一旦没有饭吃了,便到老爹这里蹭来吃,老爹不给吃,就去到大哥二哥的家里找饭吃。
不管是媳妇们如何怨声载道,只要是有大哥、二哥在,总还是看在亲兄弟的情分上,不会让刘邦空着肚子的。可惜的是大哥寿命不长,得病死了,留下了大嫂和一个叫刘信的儿子。本来大嫂就看不上这个小叔子,现在又成了孤儿寡母的,一看到刘邦每次都带着三五个汉子来白吃白喝,那大嫂就老大不愿意了。
“能这样让他白吃白喝吗,还不得把家吃穷了?我可是不能再供你这个连帮工都不做,尽吃白食的兄弟了。”是啊,这一帮子人简直像蝗虫一样,每人得吃三五碗的饭,这就是大嫂她们家五六天的粮食呀。每次只要这个小叔子前来,准得把她家的米饭扒拉一空,还得她重新做一顿。
有一次,刘邦和他的狐朋狗友共有六人,才从河里游泳回来,肚子早早饿了,就跑到了大嫂的家,在门外就喊道:
“大嫂,还有吃的吗?我们可都是饿坏了。”
那大嫂早看到刘邦一伙人张张扬扬地走过来,就想了一个法子,把煮好的饭盛到一个大木盆子里,然后拿出空锅来刷着,还弄得稀里哗啦响,并应声道:“哎呀,兄弟,我们都吃过了,今天没有剩饭······”刘邦倒无所谓,就觉得算了,扭头便走,想到其他的地方找饭吃。他的那帮狐朋狗友中也真有鬼头鬼脑的人在,其中一个人竟然不相信,悄悄躲到了一个草垛后面,见刘邦一伙人走了,大嫂就叫孩子将饭和菜搬出来吃。正好大门开着,这情况被这个刘邦的小兄弟瞧个正着。
他跑来悄悄告诉了刘邦。
刘邦大愤道:“哼,我大哥不在了,她就这样小看我,算了,长点志气,从此我们不去她家了,将来······将来,要是我成了大富翁或者是大丞相,有了很多很多的钱,我就每天用十担米做一锅饭,摆在她家的门口,气死她!”
他的那些小兄弟舔了舔嘴巴,说道:“大哥,咱们今天中午的饭都没着落呢,别说十担米,有两升米就够我们吃一顿的了。”
都是穷人家的孩子,这里面的人还算是刘邦家过得好一点,所以每次都是刘邦提供给他们吃喝。
刘邦道:“要不,还是到我老爹那里去蹭一顿吧?”
“你老爹那张碎嘴子真让人忍不了。”
“就是,这回我就塞上两个棉花球好了。”说着,刘邦真的找来了一点棉花,做成两个棉球塞到了耳朵里。
这一行人径直走到了刘公的家,正好碰上刘公、后妈和刘交弟弟在那里吃饭,于是一行人也不客气,到锅里盛来了就吃,刘邦坐到了凳子上,他的那些兄弟有的蹲在地上,有些拿到了门外,即使是没有菜,他们也无所谓,只要能填饱肚子也就算是好的了。
任何一家人都经不住如此众多的人来蹭饭,一下子锅就被盛空了,那刘邦的后妈还没有吃,她怨怒地看了看这帮子人,没有吭声,只是向刘公瞥了一眼。
刘公当然也很生气,他又唠叨开了:“季儿,你这样子瞎混总不是个事,既然不读书也不种庄稼,要不就去做买卖算了。”
“啊······什么,做买卖,好啊,咱家能给我多少本钱?”
“我有一个熟人,在丰邑开店,本来你祖父再三交代,不要去他们家要求什么。现在也顾不得了,我去向他们借去,不过,这钱是要有利息的,你挣了钱得还给他们。”
“什么,老爹,你再说一遍,我没有听清?”
老爹的话怎么会听不清呢?刘执嘉有点不相信,还是刘交眼睛尖,他说道:“爹,三哥耳朵里塞着棉花呢!”
经这一说,把刘老汉气得发昏,他一筷子就打在了刘邦的头上,“你,你是烦我数落你吗,我这是为的谁呀,还不是为你这小畜生的下半辈子有着落吗!”
这一筷子打得很重,刘邦的额头顿时起了两条红杠。刘邦跳了起来:“老爹,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儿子没答应不做生意啊,这棉球是我们去河里游水,怕水进了耳朵才塞的。”刘季把耳朵里的棉球取出来让他看。
“哼,你骗我。当我不知道?平日里说你,你就用手捂住耳朵,今天我看你没捂耳朵,以为你还能听几句话,你、你竟然想了这个办法,用棉花塞耳朵。你成心要气死你老爹吗?”
刘公越说越气,又站起身来要打他的儿子,刘邦一看不好,就叫了一声:“快逃!”自己往门外逃去,他的那帮兄弟,也跟着像兔子一样蹿了。
等这件事儿过去之后,刘公还是心痛自己的儿子,就去到魏居平开设的店里,借了十缗钱。这时,魏居平己死,是他的儿子撑着门面,但他们都知道刘叔对他们祖父有恩。也就毫不犹豫地借给了他。刘公把钱交给刘季时,再三再四地对儿子说,一定不能再瞎花了,做点正经生意。并且告诉他,可以做丝绸生意,从魏家进货,小打小闹,只要能糊口就算不错了。
谁知刘邦根本就没有做什么丝绸生意,这笔钱最后不知道被刘邦花到什么地方去了。刘邦因此好长时间再也不敢到老爹的家中去。老爹得知儿子这样不成器,也气得无法可想,父子两人的关系从此闹得很僵很值。
五
一个农民的儿子,口袋里没有几个子儿,想去大地方的赌馆妓院是去不了的,只有在乡村间的小地方充一充大头,刘邦他最常去的是两家乡间酒肆,这两家酒肆却是两个寡妇所开,农村妇人没有留下姓名,故而我们叫她为王媪、武妇(负)、王媪要比刘邦大出好几岁。对于乡村中像刘邦那样的无业游民,因为得罪不起,只得笑脸相迎,不过,比较起来,刘邦这伙人比其他的小混混还好一些。因为刘邦好夸夸其谈,对于秦朝的大小新闻都了如指掌,所以他一到酒店,就像多了个说书人,酒客明显增多,生意也十分兴隆,王媪也就不太计较,有钱无钱都端上酒来,让他们尽兴一番。
刘邦已到二十余岁的年龄了,仍然是一事无成,老爹的数落也就多了起来。这一日老爹大概是说过重了,刘邦心情不快,便顶了几句,刘执嘉拿起棍棒又想打,刘邦只得悻悻然逃了出来,到王媪的小酒馆来喝闷酒。
心情不好,酒不醉人人自醉,刘邦不久就醉倒在酒桌上了。这时已到上灯时分,农村人睡得早,小店早已没了人。
该是打烊的时候,王媪不忍心将刘季叫醒赶走,只得任他趴在桌上酣然大睡,她自己去后院将息。
到得后半夜,王媪不知是不放心店中有外人还是她难守空帐,总之是披衣起来看看刘季是否已走。却听得刘邦在睡梦里叫道:“水,水。”她端来了一碗水,给刘邦灌了下去。再想返回去睡,又担心刘邦趴在桌上容易着凉,就说道:“兄弟,要不到榻上:去睡会儿?”就将刘邦扶了起来,硬是将他弄到了后院的榻上。
你想一个寡妇人家,还会有两个房间两张榻么?王媪将刘邦放到了自己的睡榻上。岂知刘邦身高马大,倒下去时又手搂着王媪没有放开,就连带着把王媪也带倒了,她这一倒便倒在了刘邦的身上。
首先让王媪感到异样的是刘邦腰间的那个玩意儿,硬得厉害,凶得厉害,愣生生顶着了王媪的小肚子,还顶得生痛。就这一下,顶醒了一个寡妇独守空床时的梦想,也顶破了她原想坚守贞操的意志,长堤因此崩溃。
情不自禁地,王媪用手抚弄着那个坚挺的“枪尖”,渐渐地,她将这男人的裤子褪下半截,用手把弄起来。这下,原本硬实的枪尖更是怒不可遏,耀武扬威,久旷的寡妇按捺不住不断上蹿的心火,急不可耐地将全身与这汉子压在了起。
这一切对于酒醉的刘邦仍懵然无知,只当是在做着一个甜滋滋的美梦。那王媪却使出了一个寡妇早已掌握的全部手段,在这个男子的身体上纵横驰骋,把她的激情都付给了那一声声畅快的呻吟。
瀑布从万丈高处泻落潭底,王媪也从这汉子的身上跌落了下来。她十分惬意,十分满足,自然而然地温柔地搂起这个男人,就像搂着自己的丈夫一样,沉沉睡去。
第二天,红日爬上三竿,刘邦这才从酒醉和睡梦中醒来。这一醒不打紧,却发现自己睡在了这个王媪的榻上,虽然上身的衣衫还在,下身却是光溜溜的,而在他的身旁,还躺着一个裸体的女子,一眼便认得出,那就是王媪。
王媪只不过三十余岁,并不是一个难看的女人,这时候面带桃花,脸含意足,更显得她娇柔无限,而她那身子,是白白亮亮的,在光照下显得晶莹剔透。
刘邦本来就不是一个正人君子、坐怀不乱的柳下惠,只是他不像那些登徒子,执意去挑逗和强迫那些女人,强行成其好事罢了。还有一点是,刘邦虽然好色,却还是一个情窦虽开,却不知道如何放飞的处男,而这一晚,是王媼给他上了一次启蒙课,让他进入了另一个境界。
怪不得昨晚的梦做得那样的好,像登天似的。刘邦一面想着,一面看着,又感到下身燥热起来,这时他还顾得什么,一下子搂紧了王媪。王媪醒来了,见到刘季如此,也连忙配合着他涌起浪落。在王媪的辅佐之下,刘季的动作完成得很好,这回是他在王媪身上纵横捭阖,成了一个胜利者,所以感到更加愉悦。
如果说昨晚刘邦的感觉还是梦中意授,这大白天的温习让他完全懂得了床笫之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尽管刘季这个人学文不行,务农也没有天分,在这方面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这一回合之后,他竟然像上瘾似的每晚都要往这酒店里跑。王媪热乎劲一过,心里倒先不安起来了。她是一个寡妇,寡妇门前是非多,要是外人知晓了,传言出去,她的脸往哪里搁?况且她的年岁比刘邦大,长此下去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于是她慢慢冷了下来,也力劝刘季要爱护身体,多把精力用到仕途经济上去。
刘邦这时正是初尝云雨,欲罢不能而又是精力勃发的时候,看到王媪开始推三阻四,过不了瘾,心中略有不快,再说她又说些务农读书的话,跟他老爹说的一样,也令他心烦。于是他负了气,便到另一家酒店去了。
那一家酒店的老板姓武,也是一个寡妇,她年纪比王媪还轻,长得一点也不差,只是膝上有几个半大不小的孩子。
刘邦人高马大,一表人才,要说叫哪个女人嫁给他,或许因为家里穷,白丁一个,没有哪家的闺女首肯,但是若是给人家做露水丈夫,却是上上之选。何况如今他已然不同,这块处男之田已被王媪开垦,他已懂得怎么对付女人了。
武妇也是个久旷的女人,用不着花大力气,就被他勾到了手。
有意思的还不只是这两个女人,而是另外的一个女子,也成了他的俘虏。
这名女子姓曹,是武妇的表妹,由于嫁不对郎,夫妻俩长年吵架不断,加上家乡闹了水灾,便来投奔表姐。那丈夫也不管不问,不知逃到哪里要饭去了。
这一天,刘邦又来到了武妇的小店,想在这里寻找他的温存。谁知端酒上菜之时,他却看到了两只白白柔柔的小手。
那绝不是武妇的手,因为武妇长年在酒店里忙碌,粗活细活都离不开她,她的手要比这双手粗糙。
刘邦抬起头来,想看一看这双妙手所属的脸庞,这一看不打紧,让他的骨头先酥了一半。
这个女子长着一张鹅蛋似的脸,白嫩嫩的,煞是好看;她那乌黑的头发盘了一个偏髻,悬挂一侧,更让她增添了几许妩媚。刘邦不仅看呆了,还暗暗地想道,嗯,正是这样的小手才配得上这样的脸蛋哩。
这女子的长处还在于她的年轻,人的水嫩在少年,这女子比王媪和武妇都年轻了许多,自然也动人了许多。
刘邦一下子被迷住了,竟忘夹菜喝酒。
那女子冲着他嫣然一笑:“客官,酒菜都齐了,请用吧!”
嗓音也是甜甜的,刘邦还没有喝酒,心已醉了。
不过,这个刘季有一个好处,对了一火候没到的事情,他是不会霸王硬上弓乱来的。但他心里却早就下了决心,一定要把这个女子弄上手。
机会是另外一个人给他的。
这个人叫雍齿。
雍齿也是这一带的一个小混混,不过他与刘邦是两路人。
刘邦虽然混迹乡间,却不大乱来,有时还能站出来主持正义,所以乡人并不讨厌他;而这个雍齿却纯如流氓,打架斗殴、吃喝嫖赌、耍赖玩泼,样样都沾。
这一日,雍齿听说武妇的这家小店里来了一个美人,便带了三四个弟兄前来喝酒,当曹女端上酒菜时,他就捏住了曹女的小手道:“好滑嫩的手呀,比你们店里的豆腐还嫩哩。”说着,还特意拉住了这只手,弄到嘴边上做啃状。据说,后来所言吃豆腐的说法,便来源于此。
曹氏抽回了手,悄声说道:“客官休要取笑。”
到得后来,雍齿更不像话,不时要这要那,叫曹女上菜添酒,最后借着酒醉耍开了酒疯,一把搂住曹女就要强行亲嘴。
恰巧刘邦一人就在酒店里喝酒,当然,他其实也是冲着想多看几眼曹女而来的。
这时刘邦已忍耐不住了,大声喝着:“放手,青天白日调戏良家妇女,你还有脸在这地头上混吗?”
雍齿这时还顾得什么,也喝道:“要你充什么能,滚一边去!”
刘邦却迎上前来,一把揪住雍齿的后衣领,“放是不放,休怪我不客气了。”
那雍齿仗着今天带了几个人来,而刘邦却落单,所以有恃无恐,“不放便如何,你还把我吃了不成?弟兄们,上,替我教训教训他!”
还没等雍齿的小哥们走上前来,雍齿已经被刘邦拉开。那刘邦抡起馍馍大的拳头,照着雍齿的面门就是一下,把他打得一个趔趄,后腰撞在了一张桌子上。
这时,雍齿的手下也冲了上来,各施拳脚,却都不是刘邦的敌手,被刘邦打得落花流水。
雍齿一见打不过刘邦,只得赶快逃命,临到门口还要装作好汉,给刘邦扔下一句话:“等着,小子嗳,有一天我非把这账找回来!”
刘邦岂能不知这种流氓吃了亏后必定要报复的道理,因此也日夜防范。后来,他想到,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还是先给这个雍齿以致命的一击,让他服软为妥。于是就在一个小山坡上做了布置。
布置完毕,就单等那个雍齿到达武妇、曹女的小店之后,勾他们出来。
一日晌午,他手下的一个小兄弟向他报告,“大哥,我看见雍齿带着他的人到店里去了。”
“你快去通知咱们的人,到山坡上去,按计划行事。我去引蛇出洞!”刘邦道。
“大哥小心点。”
“不用嘱咐!”
刘邦晃晃悠悠地向曹妇的小店走去,到了店门口,他故意大声地喊道:
“武嫂,来一卮酒,两个小菜。”
武妇道:“噢,刘兄弟来啦。快请坐。”
这时候,刘邦仿佛才看到了雍齿这一帮子人也坐于店中,假作惊异地说道哟:“原来你店里还有几条狗在,不吃了,不吃了,我怕被狗咬。”
说着就退到了门外。
雍齿这伙人,等的就是刘邦,加上刘邦骂他们是“狗”,如何能够忍耐?立即追了出来。
刘邦假装害怕,拔腿就逃,这一逃就逃到了山坡上。
雍齿一看,刘邦的那些兄弟全都站在那里,也微微一惊:“嗬,你早已有准备,也好,省得我一个个去把你们叫全了。”接着,他喊道,“弟兄们,都给我上!”
雍齿就先向刘邦冲了过去。两帮兄弟都加入了战团。
那刘邦手下有五六个兄弟,雍齿也是,差不多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各自施展拳脚,在村郊外展开了一场厮杀。但刘邦有谋有略,懂得利用一下地形和战术,他们打了一阵,佯装败北,向一方逃去,结果雍齿和他的兄弟们都被刘邦他们引到在一个盖着浮草的陷坑里,全都跌了进去。等他们要爬上来的时候,刘邦等人早已立在了坑边,用木棒等着他们,露头一个打一个,打得这伙人哇哇乱叫,哎呀讨饶。
刘邦说道:“既然你们都求饶了,那好,让你们的大哥先上来,签个和约吧!”
“签什么和约?”
“今儿谁输谁贏,今后打与不打都得有个协定吧!”
雍齿伸上手来,刘邦一下子将他拉了上来。
没等雍齿站稳,刘邦一把将他推倒,雍齿翻过身来将背朝上,刘邦正好两腿一跨,骑了上去:“咱们先前怎么定的?谁打输了就听谁的!是不是?你们打输了,你服是不服?”
雍齿怒道:“不服,不服,你们使诈,只有正大光明打过,我们打输了我才服!”
“那我问你,事前有没有讲过不许使诈?讲过不能利用地形地物?”
雍齿一时不敢吭声了,因为的确他们没做过什么约定。
他犟着脑袋说道:“反正这个样子我就不服!”
“服是不服?服是不服?不服打你屁股!”刘邦用一根树枝儿,抽着雍齿的屁股,拍、拍、拍······抽一下问一句。
雍齿的小兄弟都还在坑中,被刘邦的人提着大棒堵在坑口,不准他们上来。
“再不服,那好,兄弟们,把我那大棍棒拿过来!”
一看大棍子拿来了,雍齿觉得好汉不能吃眼前亏,就连忙喊道:“服,服,我服了还不行吗?”
刘邦还不依,就说道:“那你叫几声大哥,就说我错了,今后绝不与大哥作对。”
雍齿只得照着刘邦的说辞,连说了几声:“对不起,刘大哥,小弟错了,我服了你了。大哥,今后兄弟再也不敢找你的麻烦了。”
刘邦见将雍齿收服了,就下了他的“马”,又让兄弟们放雍齿的人出坑。他们一伙人扛着木棍,唱着胜利的自编山歌,凯旋回“营”了。
此番风波之后,雍齿再也不敢到武妇的酒店来闹事了,武妇与曹女都感激刘邦。因此,在刘邦还没有采取对曹女的攻略行动之前,曹女反倒投怀送抱来了。
六
这里,得说一说刘邦的那个芝麻绿豆官泗水亭亭长是怎么得来的。
这还得从他老爹帮他借来的那十缗钱说起。
刘公将钱交给刘邦时,不厌其烦地嘱咐了他好几主遍,一定不要把钱瞎花了,一定要开一个小店,挣点钱好养家糊口。
刘邦也知道这些钱来得不易,是老爹用他的老面子去借的,所以在开头的时候,还是一本正经地与他的那些狐朋狗友商量了一番,说是如果拿这笔钱去做生意,该做什么样的生意为好。
在议论中,有的说要做丝绸生意,有的说最好做粮米买卖,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其中有一个人突然说道:“大哥,做什么生意都不如买个官做做强,在堂上一坐,一拍惊堂木,还不把那些老百姓吓死啊!”
“瞧你说得倒美,用十缗钱能买个什么官?有十万钱还说不定······”
出这个主意的人接着说道:“哎,人哥,你认识不认识那个萧何,萧书吏?”
“不认识,你提这个人干什么?”
“听说他是咱县里的第一刀笔吏,要是走走他的门子,弄个什么小吏当一当也说不定呢?”
“咳,你们也知道我读书没好好读,当什么吏就得替县令写文书吧!”
“那倒不一定,文吏要写,当个武吏嘛,就用不着认多少字了。”
“那个萧何真的有这个本事,你认识他?”刘邦有些上心了。
“认识,不熟,他也经常在泗水河里游泳呢。”
“怎以才能遇见他?”
“咱们往县城里走,装成游泳,说不定就能碰到他们。”
那泗水由北向南流,穿过沛县城,再折向东南,汇入了淮水,最后流向大海。每到夏天,会有不少的人到河里来游泳。
而他们讨论这事的时候,已经是初夏了。
刘邦也觉得这不失为一个好主意,便经常地往县城里跑,装成是游泳的模样,意在结识萧何他们那一帮子人。
有一日,那个出主意的人说道:
“你看,大哥,那几个人就是县里的吏掾,那个瘦瘦的,就是萧何。”
刘邦一伙人一看,都跳下了水,朝着萧何那一帮人游了过去。反正在这条河里游泳的人不少,大家各顾各的在那里游着,谁也不碍着谁。
差不多游了一个时辰,见萧何那帮人上了河滩,躺在河滩上休息,刘邦一伙也上了滩,装得十分自然模样,刘邦躺在了萧何的旁边。刘邦是有为而来的,便主动搭讪道:
“这天气真够热的,到了这傍晚还凉快不下来。”
“唔。”萧何只是支了一声,并没有多话。
“这位仁兄也是经常来游泳的吗?”
“是,”萧何答道:“兄台不是城里的吧?怎么眼生得很?”
“是,我是丰邑中阳里的,上城里来办点事。”
“唔。”萧何又没有话了。
“仁兄贵姓?”
“姓萧,在下是萧何。”
“噢,失敬失敬,原来是本县第吏椽,听说阁下文书论辩俱绝,我们乡下人都晓得你呢!”
听了这几句捧,萧何也不能冷淡了,随口问道:“这位兄台贵姓?”“在下姓刘,单名邦,字季。乡下人,仁兄肯定没听说过。”
“哪里,哪里,我真还听说过你哩。说你是金龙梦合降生的,还有人说你的腿上有七十二颗黑痣”
“不错,正是在下!”
“有这等事?腿上真的有那么多的痣?”
“你瞧么,都生在这里。”
萧何坐了起来,仔细地瞧着刘邦的左腿。看了一会儿,他对那两个躺着的人说道:“曹参、夏侯婴,你们来看看,这位就是刘季,他腿上真的有七十二颗黑痣哩。”
那两人也都一齐坐了起来,围过来看,“不错,真的是那么多痣呢!看来是所传非虚。”
在他们看痣的时候,萧何却在注意着刘邦的面相,“嗯,兄台说不定真是个贵人呢?”
“仁兄说笑了,一个乡下人,何贵之有?”
“这乱世之中,是很难说的。”萧何道:“最近有人传,说秦朝之东南方向有天子之气,还不知道会应在谁人身上,说不定阁下也在星座之列哩。”
“一介贫民,何敢有此非分之想,仁兄这是宽慰人吧!”
就这样,萧何一伙人与刘邦就认识了,自此之后,刘邦就经常到这泗水河来,与萧何等人一起游泳,一起说笑。
尽管萧何等人事务繁忙,不得不隔三差五地在傍晚时节来游,那刘邦则是无所事事的,尽可以随时陪伴。
一来二去,他们竟成了熟人,有一次,两个躺倒在河滩之后,萧何却显得意态索然,提不起精神来。
“萧兄难道有什么不快之事么?”
“哎,不瞒你说,我们县衙里有一个叫童铬的书吏,人虽然年轻,却是个很动心计的人,他最近常常在县令面前说我的坏话,现在县令愈来愈疏远我,看来······”
那曹参插言道:“本来论萧兄的才学人品,县丞一职非他莫属,现在那童铬竟想争抢,县令又十分宠幸于他。不知事态如何,真要两说了。”
原来,县丞犹如尚今的副县长,是县令之下的第一人,县丞缺额,应当补充,县令的推荐意见是十分重要的。
刘邦道:“萧先生何必为此事烦恼,不出一个月,我刘邦就能摆平他!”
听了刘邦的这句大话,让萧何吃了一惊,忙道:“兄台可不能乱来!违法的事咱不能干!”
“哪能干那些没屁股眼的事呢?萧兄把这事交给在下,我保证不让这小子得逞便是了。”
萧何还是有些不放心,问道:“兄台想采取何法?”
刘邦说道:“目前尚不知晓,但凡是人,必都有死穴所在,等我摸到了他的死穴,即可让他致命。”
刘邦告别萧何,往回走的时候,便吩咐他的那帮子兄弟,要他们调查这个童铬的一切情况。
尚然,要调查就得有花费,刘邦的这十缗钱。全都用在这上面了。他们探知,这个童铬经常到一个赌场中去,去后不久就出来了,好像并不是真的去赌。他让兄弟跟踪童铬,回报是他还常到一个年轻女子那里去。刘邦问他们这女子生得如何,这位见到过的兄弟咽着口水说道:“太妙啦,与乡下女子根本不能比。”
“怎么个不能比法?”
“她的头是摇的,脖子是歪的,手指是勾的,腰是扭的,脚尖是翘的。”
“胡说八道,她的脚尖翘与不翘你也能看得到?”
“真的,她穿的那个单鞋里,大姆脚趾老是那样一动一动地往外翘起来,就像,就像男人裤裆里的那东西一样不老实。”
“哈哈哈哈。”刘邦和他那帮兄弟全都被逗笑了。
刘邦道:“那我非得见识一下这个小娘们不可。”
这一晚,刘邦知道童铬要去赌场,他也就没有回丰邑去,悄悄地跟在了童铬的后面。进得赌场,那童铬径直往后面走去,刘邦不便进去,只得在外面的台子上装成赌博押黑红宝。
黑红宝的赌法自古皆有,那就是桌面上画着黑红两种色彩,赌客们可以押红也可以押黑,庄家就只能开出红黑两种结果,押错的被庄家收去,押对的庄家会以一赔五。
试了儿把,刘邦看出了门道,便对他的小兄弟说道:
“你用十个钱押黑,我就押红,我们两老是反过来押。”
这回就对了,他们一个赔钱,另一个即能赚取五倍的钱,这一下子就多得了四倍的盈利。
原来,这家赌场以众家的押宝为准,并加以心理猜测而下的庄,总体上都是贏的,像刘邦这样两人联手的押法,还真没有见过,几把下去,刘邦贏了不少的钱。
还想再押,却见童铬走了出来,刘邦连忙退出赌桌,暗暗地跟上了童铬。
童铬走了街道,又拐进一条巷子里,走进了一户人家,想来是这家人等他前来,连大门都没有关上。
刘邦带着那个见了女人直咽口水的兄弟,悄悄潜进了大门。
看来这不是一家大户人家,连个看门的都没有,一进的房子。童铬走到门厅,轻轻敲了几下,在里面传出了一个低低的女声:“来了吗?门没插呢。”
童铬进得门去又掩上了门,好像还将门闩插上了。
“今晚县爷不会来吧?”是那个女的在问。
“要是他来,我敢来吗?不会的,我看见他到了家里,现在正被他家的那个黄脸婆缠着呢。”
“那就好,我这里酒菜都准备好了,妾身陪你喝一壶。”
“你陪我喝一壶?我还要你陪我一晚上呢!”
两个己搂在了一起,还嘻嘻哈哈地笑着。
那里面点着灯,刘邦不免心中好奇地贴着窗户往里面看上一眼,见那个女的是一张瓜子脸,脸上红扑扑的,发髻半垂,云鬂淡扫,的确是个美人坯子,只是比一般的美人还要风骚,那骚情还不时地流露在外,那所有的男人都会生出非分之想。
不用说是里面的童铬,偷瞧着的刘邦也几乎有些乱了心神了。正当刘邦发呆的时候,只听那个女的说道:
“童兄弟,钱也存得差不多了,你什么时候让县爷陪你到郡守那里去一趟呢,我还等你当了官有个靠山呢!”
“你现在不是也有靠山么,县令可是个大官呢。”
“哼,靠他?这事儿要是让他的大婆子知道了,还不知道闹成什么样子哩,小女子指望的是你呀,童兄弟。”
“你就不怕我将来也找一个雌老虎?”
“你敢?你要是没良心,我就找把杀猪刀捅了你,看看你的心是黑的还是红的。”
“跟你说笑哩,我怎么舍得你呢······”
“哼,你们男人啊,难说!”
“我是决不会······”说这句话的时候,好像童铬已经把这女子搂在了怀里。
“大门还没有关吧?童兄弟,你去把门关上。”这女子挣开了怀抱。刘邦听到,知道童铬马上要出来了,就领着那个兄弟飞快溜出了大门。
事后,刘邦从众兄弟那里了解并自己分析出这样一个大体的情况:开赌场的老板是童铬的一位表兄,童铬到那里去拿钱,每拿到钱后就放到这个叫霁月的女子这里来存着。这个妓女被县令看中,接她出来之后,县令便为她置了这所房产,供她居住。县令养了这个情妇,开始也常来光顾,但县令的老婆却是一位大官的女儿,在家里说一不二,县令很是怕她。而她的老婆又经常逼着县令回家去睡,所以县令不敢与霁月常相交往。这些情况被童铬发现之后,便宜反而被童铬占了。这女子不但成了童铬的情妇,而且帮着童铬经常在县令面前进言,说童铬的好话。现在童铬想当这个县的县丞,就利用赌馆盈利筹备贿银,放在这个女子那里存起来,一朝要用,便用此钱去贿赂上官。但是这个女子是否会利用此法将童铬的银子侵吞了,或是这个女子想最终嫁给童铬,这些情况就很难说得清楚了。
了解到了这些情况之后,刘邦有了主意,他将计划告诉了萧何。萧何当然用不着刘邦更多提醒,他根据刘邦的侦察,在某一个晚上借巡察为名,带着县令来到了大街上。
县令见萧何把他领到这条小巷路口时,心里有些慌张,以为萧何是来揭他的秘密的,他想掉头回去,却被萧何拖入巷中。到得这小院的大门口,县令更是心惊,想快些走过去。萧何这时顾不得什么,硬是把县官扯进了院内。
在县令惊奇地以为萧何识破了他的隐私之时,更大的吃惊让县令目瞪口呆,他在门外听到了自己的情妇与童铬调情的浪里浪气的声音。
“这个坏娘们,是我养的她,她竟然再去找一个小白脸!”气得县令想一脚踢进门去。萧何赶紧拉住县令,将他扯了出来。
萧何道:“大人,不可鲁莽,您心里有数就是了。”
从此,县令再也不信任童铬了,不仅不信任,而且处处都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恨不得把童铬早早除去而后快。而萧何呢,又重新获得了县令的宠幸。
由于刘邦为萧何办成了这样一件大事,萧何也全力推荐刘邦,让他当上了泗水亭的亭长。
而刘邦的那十缗钱,就全部用在“调查费用”上面去了。
一亭之长,虽然小得可怜,但毕竟也是一个小吏了,有那么一个亭驿可以去办公,还配有两个属下,一个出去查案断讼,另一个在亭驿洒扫庭院,而他,则可以抽出空暇来与县里那班吏役喝茶饮酒,在乡里过一过“体察民情”的官瘾。
有了这个头衔,乡里人看他就不一样了,而王媪与武妇对他的态度也就更好了。
其实在此时,武妇曾私下里对曹女说过了这样的段话:
“这个刘邦是个可托之人,看他那样子,当上个亭长像模像样的,说不定还能升官哩,就是个升,这个人也靠得住。你又不是黄花闺女,得在这里找个依靠,而咱这个店也少不得有人关照,你如果没啥意见,就多接近接近他,将来他能立你为正室当然好,就是个偏室,生下个孩子,也是个依靠!”
在曹女点头同意之下,武妇在一个傍晚把刘邦请了来,专门在后室曹女的房里摆下了一个简单的宴席,说一是感谢他主持正义,救曹女于受辱之时;二是拜托今后还要他多多照顾孤儿弱女。刘邦当然看出了其中的玄机,哪有不允应之理,当场大拍胸脯,说将来有他刘邦出头之日,也绝不会亏待她们两个女人。
开始是武妇亲自把盏,殷勤劝酒,到了后来,武妇推说孩子要睡觉了,让曹女招待刘亭长多喝几杯,就溜走房去,还将房门带上了。
刘邦在那些寡妇们的训练之下,成了赏花惜玉的高手,他本来就对曹女垂涎三尺,只是摆出了救花护道的姿态,装出正人君子的模样命已,这次对方投怀送抱,岂有不接纳的道理。他乘着曹女敬酒之机,一把就将曹女搂住,那曹女也就顺势坐到了他的大腿上。
两人本无顾忌,当下便畅开心情,竟是这个将酒含在嘴里。送进了那个口中,那个又咬住了一块肉片,定要这个去咬那另一半。还没等酒醉饭饱,刘邦早已按捺不住色心,一把抱起了曹女,将她按倒在了床上。
刘邦迫不及待地撕开了曹女的衣衫,一个晶莹如玉的身体便展现在他的面前,刘邦看那身子,比起王媪、武妇来更胜一筹,闪亮的肌肤里透着青春与鼓胀,微张的小嘴也像是正等着男人去亲近。性急的刘邦恨不得立即与那身子融为一体。而那曹女也是心里愿意,就曲意奉承,使出百般柔性,勾背缠腿,像一株凌霄藤一样,一定要绕住这根乔木。于是,两人便颠鸾倒凤,撕咬在了一起。
不知过了几时,云雨方歇,那曹女道:“贱妾从今夜始,已是刘郎的人了,愿君不可忘却今宵,永远疼惜。”
刘邦信誓旦旦地回答:“只要我刘邦有发迹的一天,一定与你富贵同亨,永不相忘。”
不久,那曹女竟然肚子争气,替刘邦产下一子。虽然曹女娇小玲珑,这个儿子却生得肥头大耳,胖壮有加,于是刘邦就叫他为刘肥。
自从有了刘肥之后,刘邦有心想明媒正娶曹女,只是没敢同父母去说。正当这时,却插进了吕公当面提亲一事。那吕公是个大户,又有县令为其后台,一心想向上攀龙附凤的刘邦自然不会拒绝这门亲事,这样,曹女便成了连名分也没有的外室。
刘邦本来就觉得有些对不起曹女,现在又潜逃在外,不知何时能归故里,不仅不能给曹女名分,连见上一面都是困难。他是个怜花惜玉的人,因此经常沉思独想,心中叹息,不知这个曹女与肥儿现在过得怎么样了?
七
刘邦等人在芒砀山中的密林之中躲避官捕已有八九个月了,在这八九个月中,他手下的人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这都是因为时势愈来愈恶劣。一则是秦里朝苛政猛于虎,劳役无穷尽,逃役避税的人都惟有逃难一途;另则是不堪忍受的民众已开始走向反抗,起义军与秦王朝军队的战争时有发土,为避战乱的百姓也都逃向了山中。
这时刘邦的周围,已经有了一二百人的壮丁了。
就在这当儿,不时在外打探消息的樊哙忽一日来报,说萧何与曹参叫他马上出山,到县城里去拱卫县城。
一个在逃囚犯,怎么下子就变成了可以保卫县城的守卫呢?皆是因为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他在山中的这几个月,外面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原来秦廷曾命令阳城、阳夏一带官员组织千人到北方的渔阳去戍边。结果人数不足,只凑起九百余人。这支队伍由陈胜与吴广两人为正副屯长,并配有两个廷尉管带。到得大泽乡时,恰逢阴雨连绵,行期耽搁,于是这两人干脆揭竿造反,扯起了义旗。
陈胜起兵蕲州,传檄四方,东南各郡县响应者甚众,往往都是闻讯后城内起乱,杀掉守令,响应义军。蕲县在南,沛县在北,两地相距不过二百余里。因此县令十分恐惧,一怕城池为陈胜所攻,二怕城中姓生变,夺城以响应义军。
县令的心思,不如乘义兵末到,就贡献城池,向陈胜投降。他招来了萧何、曹参,向他们问计。
萧何大叫不可。
萧何说道:“君为秦官,怎能降盗?现在陈胜等人是否能得势尚在两可之间,如果陈胜兵败,令公岂不成了秦廷叛逆,身首异处?还是先看一看再说。现在主要是应当加固城防,保卫城池。”
县令摇头说道:“城中本无兵卒,如何守城?”
曹参言道:“我闻刘邦等人,在芒砀山中,己聚集百余人众,令公可以招集他来守城,他原是本县小吏,想来只要释免他逃亡之罪,一定会听从令公安抚。再放出狱内囚犯,一并由他组织,可暂保沛县无忧。”
县令于是同意了,派人去招抚刘邦。
岂料萧何、曹参刚走,那个童铬便凑到了县令身边,对县令说道:“令公,切切不可,你这样做,要引狼入室了。”
“这是何说?”
“那萧何、曹参,本与刘邦是一伙的。让他们掌握城池,还有您令公的地位嘛?要是他们挟令公而号百姓,又连如何?再说,刘邦己是秦廷要犯,你招来委以重任,万一让秦廷得知,县令岂不同样脱不了干系?”
虽然县令不喜欢童铬,但童铬这几句话却是说得很中肯的。慌了手脚的县令这时已没了主意,他左听左有理,右听右有理,便急切地问道:“那要怎么做才好?”
童铬本来恨萧何入骨,乘机挑唆道:“还不如照令公先前的想法,抓起萧何、曹参一伙,不令他们捣乱,然后举城投降陈胜,可保令公无忧。”
于是,县令听从了他的主张,命人去抓萧何与曹参。
在官吏之中,还是萧何的朋友居多,得到这个消息后,马上有人通知了萧、曹。两人一听大事不好,立即逃出了沛城。
再说刘邦得到樊哙奏报之后,事不宜迟,急忙召集这百余人壮丁,立即奔赴沛城,准备接受县令的招安。
哪知刚走到离城不足二十里之地,就遇到了萧何与曹参所带的三五人,一见萧何等人的模样,衣冠不整,气喘吁吁,便急问何故?“我们到这里来堵你,就是情况出了意外,不能再到县里去了,县令听了童铬的话,连我们都要抓要杀!”萧何说道。
曹参也道:“我们还是再躲到山里去吧!恐怕县令派的兵要追来了。”
那刘邦是个敢作敢为的人,说道:“有什么好怕的?干脆,咱们一不做二不休,攻下县城,杀掉县官,由咱们来坐江山。”
萧何心还犹豫:“这怕是不妥吧!料想县令已有防备,万一攻不下沛城怎么办?我等家眷还在城里呢。”
刘邦道:“不怕,车到山前必有路,到时再说。不然,你和我再返回芒砀山中,躲到何时为止,那算是出路吗?”
无论是县令还是萧何、曹参等人,大都是每临大事难以决断,不知所从的。偏偏这个刘邦,却是唯恐天下不乱,愈到那紧急的关头便是愈生胆气之辈。
于是,一行人都听从刘邦的主意,来到了沛县城下。
果然,县令听说萧何、曹参等人已经出城,便知道情势危急,急令关闭城门,并调集手中仅有的一些兵卒上城戍守。
刘邦心想,若是攻城,这点子人马远远不够,便问萧何道:“萧功曹有何破城办法?”
“城内听从县令的人并不多,与我们相厚的人也都不少,不如先投书函,令城中起乱,杀了县令。只是城门关着,无法投书。”
“这有何难,你修书一封,用箭射上去就可以了。我再用大话吓一吓他们,县令必然胆寒。”
萧何听了,立即草成书信一封,递与刘邦观看,那信上如此写着
天下苦秦久矣!今沛县父老,虽为沛令守域,然诸侯并起,必且屠沛。为诸君父老计,不若共诛沛令,改择子弟可立者以应诸侯,则家室可存矣!不然,父老俱屠无益也。
刘邦说了声“写得好”,便叫人将书信射到了城头。
然后,刘邦又对着城头喊道:“城上人听着,我等俱是本县百姓,都希望沛县能保无恙,家小平安。现在陈胜起兵于蕲,就凭城内几个守兵,真能保得城池不破嘛?不如照信中所说,杀了县令,由我们自己组织兵民守城,或许能走出一条生路来。”
却说县令本是外地来做官者,哪抵得萧何、曹参等人都是坐地户,加上平日里萧何等人交友广宽,大半商贾诸老与吏官都与他们相厚,因此,商量之下父老竟然赞成。更有像夏侯婴、任敖等一班衙吏听到刘邦已兵临城下,竟然带头冲进了县署,乱刀将县令砍杀,然后打开城门,迎接刘邦等人入城。
只是诛杀了县官,城内一切秩序依然井然,并未骚乱。于是刘邦等人进入县署。并召集城中诸老与有头面的商贾,共商大计。
商议之下,众人欲推刘邦治沛。刘邦言道:“天下方乱,群雄并起,刘邦只是泗水亭一小吏尔,何德何能,敢担一县之重任?我非敢自爱,只恐德薄能鲜,未能保全父老子弟,还请另择一贤能之人,方足以图此大事。”
城中诸老与商贾见刘邦推托,一时没了主意。
那萧何、曹参等人,不过俱是文吏之流,而夏侯婴、任敖之类,也只是个捕快、狱卒,都没有这方面的胆气与经验,众人相互看了看,一时间沉默不语。
当然,像萧何、曹参这样的能吏聪明人,还有一些小九九打在心黾。你想这个民众推举的县官是好当的嘛?枪打出头鸟,无论是陈胜或秦廷兵马来攻,这个县令都没有好果子吃,还是不伸这个头为好。
于是,萧何、曹参都谦让再三,并一致推举刘邦为首领,他们再三再四自愿为辅,帮助刘邦治沛。
这时诸老也同声说道:
“我们平素闻得刘季生来奇异,不仅左股有七十二颗黑痣,此次应役途中还曾力斩白蛇,这必有大贵之兆,且我等问过卜筮,莫若刘季为最吉,请你不必再推辞了!”(诸老不称刘邦的名,而称其字刘季,是爱称。)
那刘邦本来就不是真心推辞,他是个心中有异谋大志之人,早就想做一番事业,这下机会在即,岂能放手。所以就此说道:“既然蒙父老乡亲信任,刘季也就勉为其难,暂占此位,待将来有贤能之人再作辞让吧。”
就这样,刘邦就坐上了县公之位,人们从此就称他为沛公。这一年,刘邦已经三十八岁了。
那个被杀的县令,还是吕公不忘与他的交情,将他收敛,埋葬于城外一个山坡之上。
这时,是秦二世元年九月,刘邦选了个初吉日,祠黄帝,祭蚩尤,杀牲畜进行了一番祭拜,又制成赤旗赤帜,张挂于城中。因为根据他斩蛇时的传说,那个老妇人说赤帝之子杀了白帝之子,那么他当然就是赤帝的传人,故而一切皆赤实属必然。
那些随他起事的人都各有升迁:萧何被任命为丞,如了萧何原来的心愿,县丞之职等于他只在刘邦之下,其余人之上。曹参为中涓,樊哙为舍人,夏侯婴为太仆,任敖为门客。同时立即在全县招募民勇壮士,组成了一支三千人的队伍。
还要说的是那个名叫雍齿的流氓头子,虽然被刘邦惩治过一次,并当场认了错,喊刘邦为大哥,其实心里却时时想要报复。可是,刘邦真没有给他什么机会,他刚想报复,刘邦就当上了亭长:后来当了逃犯,总以为刘邦没有翻本的机会了,哪知一下子竟变成了县令,成了一县的主宰。幸好他还没有同刘邦闹翻脸,就连忙带着他的一些兄弟到县衙里来拜见“大哥”,并表示要效忠沛公之意。你想刘邦正在用人之际,这个雍齿也已表示臣服,就不再计较,任命他统领一支数百人的军队,那雍齿也就成为一员战将了。
刘邦一静下心来,就想起了那个风骚女人霁月,就在一个月夜里避开众人,到那条小巷里去找。谁知道那个童铬并没有在这次事变中被杀,而是听到风声抢先逃跑了,在他逃跑的时候,还不忘将这个霁月也带了走。
刘邦只能暗叹可惜。
回到县衙后,他与萧何商量,说要他的一帮兄弟朋友去寻访那个童铬,只要抓到他,就将他处死。萧何还以为刘邦是为他报仇,岂不知刘季是想要那个骚娘们。
沛县西北,有胡陵、方与两县,刘邦制赤旗赤帜,其实野心已现,他不仅是为了保卫沛县,而是起义去夺天下,所以一切停当之后,命令樊哙与夏侯婴各率一军,去攻两县。而这两县其实也同沛县一样,都已开始了卫城的准备。
因此待樊哙、夏侯婴兵临城下,他们都坚闭城门,不战不降,以图自保。樊哙、夏侯婴正欲攻城,忽得沛公传令,要他们收兵,两人问及传令之人。才得知刘邦的继母去世了。继母过世,儿子若还要在外面兴兵,是为不孝,刘邦只得暂且令二人返守丰乡,自己筹办丧事。
自然吕雉与一对儿女都是披麻戴孝,尾随棺后。那个曹女之子刘肥,只能是像那些其余乡邻一样,混随在大众堆里,送他的老祖母一程了。
刘邦一时只得将兵事搁起。
刘邦息兵之日,已是陈胜起义一年有余,而这时,又有两位枭雄,起兵于故楚会稽郡境内,他们是叔侄两人,叔叔叫项梁,侄儿叫项羽。秦朝虽立朝未久,却已到了风雨飘摇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