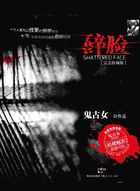坐落在雅典市中心的阿沙肯法院是一幢用灰色岩石建成的大型建筑,占了学院大街至斯特雷达的街区广场。法院里有30间审判庭,其中21号、30号和33号三间专用于刑事案件的审判。
33号审判庭的阿纳斯塔西娅·萨维拉斯谋杀案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审判庭长300英尺,宽40英尺,座位分成三个区,每区相隔5英尺,九张木凳一排。审判庭前部有一张6英尺高的桃木隔板,后面是高高的审判台,台上有三张法官坐的高背座椅。
台前的小高平台是证人席,配有一个固定的放证词的小台架。审判庭靠墙的另一端是陪审团席,早已坐满了10名陪审员。被告席前是律师的席位。
这起谋杀案格外引人注目的原因不仅在于案件的本身,而且在于担任被告律师的乔特斯是全世界公认的最杰出的刑事律师之一。乔特斯只为谋杀案出庭辩护,他的成功记录令人赞不绝口。据说请他辩护的费用要以百万计算。乔特斯看上去瘦削憔悴,皱巴巴的脸上闪烁着一双警犬般的、忧郁的大眼睛。他的衣着极不讲究,外表很难使人信任他。但是在他不修边幅的举止背后深藏着一种敏锐、聪颖的智慧。
新闻界极力推测乔特斯为何同意为这个女人辩护。他根本就不可能赢得这场官司。还有人打赌说这场官司将是乔特斯的第一次失败。
比得·迪莫尼得斯是本案的公诉人,他曾与乔特斯交过锋———尽管他不服输———他确实敬佩乔特斯的才能。对于这次交手,他信心十足。如果要举个典型的开庭后旋即结案的案例,那么阿纳斯塔西娅一案将是他最成功的例证。
案情本身很简单:阿纳斯塔西娅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嫁给了一个名叫乔治·萨维拉斯的富有男人。乔治比她大三十多岁,她暗中一直和一个名叫约瑟夫·帕帕斯的年轻司机相好。根据证词,她丈夫曾威胁要和她离婚并改写遗嘱。在谋杀发生的那天晚上,她支开了所有的仆人,亲手为丈夫准备晚餐。乔治正患感冒,进餐时一直咳嗽不止。他的妻子便把止咳药递给他,他喝了一口后就倒地身亡了。
确实是一个显而易结的案子。
33号庭一大早便座无虚席。阿纳斯塔西娅在被告席上坐下,她身着朴素的黑色衬衫和裙子,没戴任何首饰,只是淡淡地化了一点妆,显得楚楚动人。
公诉人彼得·迪莫尼得斯正在发言。
“女士们,先生们。有时,一起谋杀案的审判要拖到三至五个月。但我想这一次,你们大可不必担心本案会耽搁你们那么长的时间。当你们听完本案的事实陈述,我相信你们会毫无疑问地赞同唯一的审判结果———一级谋杀。陈述将证实被告蓄意谋杀了她的丈夫,因为她丈夫在发现了她和家中的司机有不正当关系时,威胁说要和她离婚。我们会证明被告具有动机、时机和实施她血腥杀人计划的工具。谢谢。”他回到了座位上。
首席法官转向乔特斯说道:“被告的辩护律师准备好开场陈述了吗?”乔特斯缓缓地站起来。“是的,法官阁下。”他迟疑地挪到陪审席前,眯着眼睛,像是喃喃自语地说,“我活了这么长时间,我知道任何人都无法掩盖自己本性中的罪孽,迟早会暴露出来。有一位诗人曾说过,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我相信这话是真的。我希望你们,女士们,先生们,看一看被告人的眼睛,根本就无法找到她心头居然有谋害他人的念头。”乔特斯怔了一会儿,像是在想如何再说下去,然而却又一言未发地拖着脚步回到了座位上。
比得·迪莫尼得斯突然感到一种胜利的喜悦。上帝啊,这是我一生中所听到的最惨白无力的开场白!这老头已经输了。
“公诉人准备好请第一证人出庭了吗?”
“准备好了,法官阁下,我想请罗莎·丽克奥格丝出庭。”
听众席上站起一位矮胖的中年妇女,她迈着坚定的步伐,仪态从容地走到法庭前面,宣誓出庭。
“丽克奥格丝女士,你的职业?”
“我是管家……”她哽咽着说,“我曾是萨维拉斯先生的管家。”
“是萨维拉斯先生吗?”
“是的,先生。”
“那么你能告诉我们你受雇于萨维拉斯先生多久了吗?”
“25年了。”
“噢,那么久。你喜欢你的雇主吗?”
“他是个圣人。”
“你是在萨维拉斯先生的第一桩婚姻中就被雇用的吗?”
“是的,先生。他在墓地埋葬他妻子时,我和他在一起。”
“可以这么说,他俩的感情很深,是吗?”
“他俩发疯似的相爱。”
比得·迪莫尼得斯瞟了乔特斯一眼,等他对这些问题加以反对。但乔特斯静静地坐着,显然已经走了神。
比得·迪莫尼得斯继续问下去。“萨维拉斯和第二任妻子阿纳斯塔西娅结婚期间,你仍然受雇于他吗?”
“是的,我当然是的。”她脱口而出。
“依你看这是不是一桩幸福的婚姻?”他又看了拿破仑·乔特斯一眼,乔特斯仍然没有反应。
“幸福?不,先生,他们拼命吵架。”
“你看见过他们吵架吗?”
“谁都会看到的。他们在房子里到处吵,那可是一幢很大的房子。”
“我猜他们只是动嘴,没有动手吧?也就是说萨维拉斯先生从未打过他的妻子?”
“噢,当然动过手。不过不是你想象的那样,而是夫人动手打了先生。萨维拉斯几年来一直忍气吞声,可怜的他已经很虚弱了。”
“你真的看见过她打她的丈夫吗?”
“不止一次了。”证人扭头望了阿纳斯塔西娅一眼,话音冷酷,但夹着快慰。
“丽克奥格丝女士,萨维拉斯先生死的那天晚上,哪一位仆人当班?”
“没有人。”
比得·迪莫尼得斯说话时故意带着惊愕。“你是说在整个房子里,那么大一所房子居然一个用人也没有?萨维拉斯先生没有雇位厨师,或者是女仆……男仆?”
“他当然雇了这些人。但夫人命令所有的用人在那天晚上都回去休息。她说要亲自为先生准备晚餐,说是要过第二个蜜月。”说最后一句话时,罗莎哼了一声。
“于是萨维拉斯夫人把所有的人都支开了?”
这一次是首席法官用眼神示意拿破仑·乔特斯,等他反驳,但辩护律师只是若有所思地坐在那儿。
首席法官面对迪莫尼得斯说:“公诉人必须中止诱导证人。”
“对不起,法官阁下,我重新提问。”
迪莫尼得斯走近萨维拉斯夫人。“你是说平时总有用人当班,而那天晚上,萨维拉斯夫人却命令所有人都离开以便她能单独和她丈夫在一起,是吗?”
“是的,先生,而且可怜的先生正患重感冒。”
“萨维拉斯夫人常给她丈夫做饭吗?”
丽克奥格丝嗤之以鼻地回答:“她?不,先生。家务事她从不沾边。”
拿破仑·乔特斯还是坐在那儿纹丝未动,倒像个旁听者。
“谢谢,丽克奥格丝女士,你提供的证词很有用。”
比得·迪莫尼得斯转身面对乔特斯,竭力掩饰着内心的得意之情。看得出来,丽克奥格丝的证词已对陪审团起了作用。他们将鄙夷的目光投向被告。让我们来瞧瞧老家伙有何招术说服陪审团。“该您向证人提问了。”
拿破仑·乔特斯微微抬起目光。“什么?噢,我没有问题。”
首席法官惊愕地望着他。“乔特斯先生……你不想问问证人吗?”
拿破仑·乔特斯站起身。“不了,法官阁下,看来她是个非常诚实的人。”说完便坐了下去。
比得·迪莫尼得斯不敢相信自己的运气竟如此之好。我的上帝,他思忖着,这个老家伙居然无力反击。他完了。迪莫尼得斯已经在品尝胜利的滋味了。
首席法官欠了欠身对公诉人说:“你可以传唤下一个证人了。”
“约瑟夫·帕帕斯出庭。”
一个高大、漂亮、一头黑发的年轻人从听众席间站了起来,走向证人席,宣了誓。
比得·迪莫尼得斯发问道:“帕帕斯先生,你能告诉法庭你的职业吗?”
“我是司机。”
“你现在有工作吗?”
“没有。”
“但不久前你还是有工作的。在乔治·萨维拉斯死之前,你受雇于他,是吗?”
“不错。”
“你在他家干了多久?”
“一年多。”
“工作愉快吗?”
约瑟夫看了看乔特斯,等他来为自己解围,但得到的却是沉默。
“这工作愉快吗,帕帕斯先生?”
“我想还可以。”
“你的薪水很高吧?”
“是的。”
“那么你难道不觉得这份工作不只是还可以吧?我的意思是,难道没有其他的事情令你愉快吗?你难道没有经常上萨维拉斯夫人的床吗?”
约瑟夫望着拿破仑·乔特斯,向他求助,但乔特斯仍然没有反应。
“我……是的,先生,大概有过。”
迪莫尼得斯狠狠地奚落道:“大概有过?你已经宣了誓。你究竟有没有和她私通,是还是否?”
帕帕斯局促不安。“我们私通过。”
“她的丈夫雇用了你,付给你丰厚的薪金,还让你住在他的家里?”
“是的,先生。”
“你难道不觉得可耻吗?一面拿着萨维拉斯的钱,一面又占有他的老婆?”
“我们之间不仅仅是私通。”
比得·迪莫尼得斯小心翼翼地设下了陷阱。“不仅仅是私通?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不明白。”
“我是说———我和阿纳斯塔西娅准备结婚。”
法庭里一阵惊讶的私语。陪审团的人一齐将目光投向被告。
“结婚是你的主意还是萨维拉斯夫人的?”
“这,我们两人都是这么想的。”
“谁先提出来的?”
“我记得好像是她先提出来的。”他朝阿纳斯塔西娅看了一眼,她报之以毫不畏惧的目光。
“坦率地说,帕帕斯先生,我被搞糊涂了。你怎么能同她结婚呢?她已经有了丈夫,不是吗?你想等到他老死以后吗?或者搞一个致命的事故?你脑子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这个问题火药味太浓了,公诉人和三位法官同时注视着拿破仑·乔特斯,以为他会怒气冲冲地表示反对。但是辩护律师却在漫不经心地写写画画,根本没在意。阿纳斯塔西娅开始用焦虑的目光看着他。
比得·迪莫尼得斯紧紧抓住这个机会。“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帕帕斯先生。”
约瑟夫·帕帕斯不安地挪动着身体。“我确实不知道。”
迪莫尼得斯说话犹如鞭击,响亮有力。“那还是让我确切地告诉你吧。阿纳斯塔西娅计划谋杀她的丈夫,以便去掉绊脚石。她知道她丈夫要和她离婚,而且要从遗嘱中把她的名字划掉,那样,她就会一无所有了。她……”
“我反对!”说这话的不是拿破仑·乔特斯,而是首席法官,“你是在要求证人作推测。”法官望了望拿破仑·乔特斯,对他的沉默颇感吃惊。这位老人此刻正靠在长椅上闭目养神。
“对不起,法官阁下。”他知道已经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他转过身对乔特斯说:“轮到你了。”
拿破仑·乔特斯站起身来。“谢谢,迪莫尼得斯先生,我没有问题。”
三位法官面面相觑,不解其意。其中一位开口说道:“乔特斯先生,你是否知道这是你询问对方证人的唯一机会?”
乔特斯眨巴着双眼。“我知道,尊敬的法官阁下。”
“对于他的证词,你没有任何问题要问吗?”
乔特斯的手在空中挥舞了一下,含糊地说道:“没有,尊敬的法官阁下。”
那位法官叹了一口气。“好吧,公诉人,可以传下一个证人出庭了。”
下一位证人叫米哈利斯·哈托里德斯,六十多岁,身体仍然很强壮。
他宣誓完毕入席后,公诉人问道:“请告诉法庭你的职业。”
“好的,先生,我经营一家旅馆。”
“你能说出这家旅馆的名字吗?”
“阿哥斯。”
“旅馆在哪儿?”
“在库弗。”
“哈托里德斯先生,本法庭中有没有谁住过你的旅馆?”
哈托里德斯的目光扫视一周后说:“有,他和她。”
“请在记录上写明证人手指着约瑟夫·帕帕斯和阿纳斯塔西娅。”他接着问证人,“他们在你的旅馆里住过不止一次吧?”
“是的,先生,他们至少住过六七次。”
“他俩在那里过夜,同住一个房间,对吗?”
“对,先生,他们通常来度周末。”
“谢谢,哈托里德斯先生。”他望了望拿破仑·乔特斯,“该你了。”
“没有问题。”
首席法官侧身和另外两位法官耳语了一阵。
首席法官看着拿破仑·乔特斯。“你没有问题要问这位证人吗,乔特斯先生?”
“没有,尊敬的法官阁下,我相信他的证词。那家旅馆不错,我自己也去过。”
首席法官凝视着拿破仑·乔特斯良久,然后把目光转向公诉人。“公诉人,可以传下一个证人了。”
“公诉人想请瓦西利斯·弗兰格斯医生出庭。”
一个气质不凡的高个男人起身走到证人席,宣誓后入席。
“弗兰格斯医生,你能否告诉法庭你是哪科医生?”
“我是全科医生。”
“是不是相当于家庭医生。”
“那只是名称不同而已,是的。”
“你行医多久了?”
“快三十年了。”
“你有政府颁发的执照吗?”
“当然有。”
“医生,乔治·萨维拉斯是你的病人吗?”
“是的,他是我的病人。”
“多久了?”
“十年多一点。”
“你是否为他治疗某一种特殊的病?”
“呃,他第一次来找我的时候,他患了高血压。”
“你就为他治了这个病吗?”
“是的。”
“你后来见过他吗?”
“见过,他常来我这儿,有时是支气管炎,有时是肝脏失调,都不严重。”
“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
“去年12月。”
“就是在他死前不久?”
“是的。”
“他是到你的诊所看病的吗,医生?”
“不是,是我到他家去的。”
“你通常都是到病人家中出诊吗?”
“不经常。”
“但你对这个病人例外?”
“是的。”
“为什么?”
医生犹豫了一下。“这么说吧,他的身体状况不允许他来我的诊所。”
“他身体怎么呢?”
“他软组织撕裂,几根肋骨青肿,还有脑震荡。”
“是事故造成的吗?”
医生又犹豫了一下。“不是,他告诉我是他妻子打的。”
法庭里一阵骚动。
首席法官愠怒地说道:“乔特斯先生,你不反对把道听途说之词写在记录上吗?”
拿破仑·乔特斯温和地说:“噢,谢谢,尊敬的法官阁下,我反对。”
但是,局面已经对他不利了,陪审团成员都将敌意的目光投向了被告。
“谢谢你,医生,我的问题问完了。”迪莫尼得斯沾沾自喜地转向乔特斯,“该你了。”
“我没有问题。”
接下来是一连串的证人:一位女仆证明说,她曾几次看到萨维拉斯夫人去过司机的住所……一位男仆证明,萨维拉斯先生威胁过他的妻子要跟她离婚并要改写遗嘱……邻居们也听到过他们两人的大声吵闹。
拿破仑·乔特斯还是没对任何一个证人提问。
阿纳斯塔西娅恰似一条无力挣扎的网中之鱼。
比得·迪莫尼得斯已经感到胜利在望了,他仿佛看到了报纸头版头条新闻的标题。这次审判将成为历史上最迅速的一次。这起案件甚至今天就可以了结,伟大的拿破仑·乔特斯被打败了。
“我想请尼科·曼塔基斯到证人席上来。”
曼塔基斯是一个清瘦、一脸诚挚的年轻人,他说话缓慢而谨慎。
“曼塔基斯先生,你能告诉法庭你的职业吗?”
“可以,先生,我在保育室工作。”
“你照看孩子?”
“唉,不是,先生,不是你所说的那种保育室。我们那儿是各种树木花草,各种植物。”
“噢,原来是这样,那么你是培养植物的专家啰?”
“我想应该是的。我从事这份工作已经很久了。”
“我猜想你做的工作就是让那些即将出售的植物保持健康,是吗?”
“是的,先生。我们精心培育植物。哪怕有一点小病的植物也不能卖给顾客。大部分顾客都是我的老主顾。”
“就是说,去你那儿的都是同样的顾客?”
“是的,先生,”他话音里带着自豪感,“我们提供的服务是优质的。”
“请告诉我,曼塔基斯先生,萨维拉斯夫人也是你的老主顾吗?”
“是的,她非常喜欢植物和花草。”
首席法官不耐烦了。“迪莫尼得斯先生,法庭觉得你这些问题与本案无关。你是否问点别的,或者……”
“法官阁下,如果法庭能让我问完,证人的证词与本案关系极大。”
首席法官看了看拿破仑·乔特斯。“乔特斯先生,你对这些提问是否有异议?”
拿破仑·乔特斯抬起头,眨着眼睛。“你说什么?没有异议,法官阁下。”
首席法官沮丧地盯着乔特斯看了一会儿,然后对比得·迪莫尼得斯说:“好吧,你可以继续。”
“曼塔基斯先生,萨维拉斯夫人是否在12月的某一天到你那儿去,告诉你她的植物有问题?”
“是的,先生,她说过。”
“事实上,她是不是说因为虫害,她的植物被毁了?”
“是的,先生。”
“那她有没有问你要什么杀虫药呢?”
“要过,先生。”
“你能告诉法庭是什么药吗?”
“我卖给她一些锑。”
“你能向法庭准确地描绘一下那东西吗?”
“那是剧毒的,就像砒霜一样。”
法庭里顿时骚动起来。
首席法官用小木槌猛地一敲。“如果再有喧闹,我就要命令法警清场了。”他转身对比得·迪莫尼得斯说,“你可以继续问下去了。”
“你说你卖过锑给她?”
“是的,先生。”
“你认为这药能致命吗?你刚才把它比做砒霜。”
“是的,先生,是致命的,没错。”
“而且你有记录在案,因为法律规定购买有毒物品必须登记,对吗?”
“对,先生。”
“那么,那些记录你带来了吗?”
“带来了。”他递给迪莫尼得斯一本账簿。
公诉人走到法官席前面。“尊敬的法官阁下,我希望能把此物证标为‘物证A’。”他转身对证人说,“我没有问题了。”他朝拿破仑·乔特斯望了一眼。
拿破仑·乔特斯抬眼摇摇头。“没有问题。”
比得·迪莫尼得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该是亮出杀手锏的时候了。“我想请大家看看物证B。”他转过身来,向后面走去,对站在门旁的法警说,“能请你现在把它拿进来吗?”
法警急步走出门去,不一会儿便捧回一个托盘。盘子里是一瓶咳嗽糖浆。瓶里的糖浆明显地少了一些。法警将托盘交给了公诉人,人们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迪莫尼得斯将它放到陪审席前的一张桌子上。
“女士们,先生们,你们看到的是本谋杀案的凶器。就是它置萨维拉斯先生于死地的。这就是萨维拉斯夫人在她丈夫死去的那天晚上给他服用的咳嗽糖浆,里面放了锑。可以看出,被害人喝了一些药水———20分钟后便死了。”
拿破仑·乔特斯站起身来以微弱的声音说道:“我反对,公诉人无法认定死者服用的就是这个瓶子里的药。”
比得·迪莫尼得斯乘势而入。“我当然非常尊重你,我富有学识的同行,但萨维拉斯夫人已经承认在她丈夫死去的那个晚上,由于她丈夫剧烈地咳嗽,她亲自让他喝了这个瓶子里的糖浆。这个瓶此后一直存放在警察局,直至几分钟前才拿到法庭上来。验尸官已证实萨维拉斯死于锑中毒,这瓶糖浆中恰恰含有锑。”他用挑衅的目光盯着拿破仑·乔特斯。
拿破仑·乔特斯败下阵来,摇摇头说道:“这么说来我想是毫无问题的。”
比得·迪莫尼得斯以得胜者的口气说:“丝毫没有问题,谢谢您,乔特斯先生。公诉方停止对本案继续提出证据。”
首席法官掉头对拿破仑·乔特斯说:“辩护方是否准备辩论总结?”
拿破仑·乔特斯起身说道:“好的,法官阁下。”他呆站了许久,然后从容地往前走了几步,站到辩护席前,抓耳挠腮,一副不知从何说起的样子。他终于开腔了,可说话时还在搜寻词句,结结巴巴。
“我想你们中有人会问我为什么对证人不加盘问。唉,实话实说吧,我认为迪莫尼得斯干得非常出色,因此我无须再多问。”
这个笨蛋在为我辩护呢,比得·迪莫尼得斯暗自欢喜。
拿破仑·乔特斯扭头凝视着那瓶咳嗽糖浆,良久,才转身对陪审团说:“所有的证人看起来都很诚实。但是,他们未能证明什么,难道不是吗?我的意思是……”他摇了摇头。“是啊,把这些证人的证词总结一下,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年轻貌美的姑娘嫁给一位老人,而这位老人不可能使她得到性生活的满足。”他朝约瑟夫·帕帕斯点点头,“所以她找了一位能满足她的年轻男子。可是这些我们从报纸上也能读到,不是吗?他们私通已不是秘密,全世界都知道了。世界上每一份低级庸俗的报纸都有报道。当然,你我对她的行为不会持赞赏态度的。可是女士们,先生们,阿纳斯塔西娅并不是因为犯有通奸罪而在此受审的。她并不是因为她具有和其他任何女人一样正常的性要求才上这个法庭的。她是来接受涉嫌谋杀的审讯的。”
他的目光紧紧地盯着药瓶,似乎着了魔。
让这个老家伙胡言乱语好了,比得·迪莫尼得斯心想。他望了望墙上的钟,12点差5分。法官们总是在正午休庭。这个老笨蛋的总结是说不完的。他聪明一点儿的话,本应该等到重新开庭时再作总结。我为什么总是要怕他呢?比得·迪莫尼得斯心里也觉得奇怪。
拿破仑·乔特斯还在杂乱无章地继续说着。“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证据,可以吗?萨维拉斯夫人的植物患了虫害,她喜爱这些花草,要拯救它们。她去找了曼塔基斯先生。这位植物专家建议她使用锑。她听从了专家的意见。你们不会把这看成是谋杀吧?我当然不这么认为。下面是管家的证词,她说萨维拉斯夫人赶走了所有的仆人以便亲自做饭,和她丈夫共同享用蜜月式的晚餐。我认为实情是管家本人可能对萨维拉斯先生有些爱慕之情。只有对男人有相当深的感情,才有可能心甘情愿地为他工作25个年头。她憎恨阿纳斯塔西娅,你们从她的证词中难道看不出来吗?”乔特斯轻轻地咳了一声,清了清嗓子,“所以,让我们假设被告在内心深处非常爱她的丈夫,她在尽最大的努力改善婚姻生活,使之维持下去。女人如何向男人表示自己的爱呢?要我说,最常用的主要办法之一就是为他做饭。这难道不是表示爱情的一种方式吗?我认为是的。”他又转身看了看药瓶,“当一个男人生病时,无论是生病还是不生病,她去照顾这个男人不也是爱的一种方式吗?”
墙上的钟指向了11点59分。
“女士们,先生们,本案开始时,我就请大家看一看这位女子的面孔。这不是一张充满杀机的面孔,那双眼睛也不是杀手的眼睛。”
比得·迪莫尼得斯看到陪审员个个以从未见到过的敌意目光看着被告。陪审员们都已听从他的摆布。
“法律条文白纸黑字,非常清楚。女士们,先生们,尊敬的法官会告诉你们,为了宣判被告有罪,必须出具确凿的证据,容不得有丝毫的疑点。”
拿破仑·乔特斯又咳了起来。他从衣袋中掏出一块手帕捂在嘴上,然后走到放在陪审席前的那瓶糖浆面前。
“到现在为止,公诉人还没有任何证据能说明问题,不是吗?除了萨维拉斯夫人给她丈夫服药的这个瓶子,什么也没有,而事实上,公诉方的起诉毫无根据。”刚说到这里,他又是一阵咳嗽,便不由自主地拿起那瓶咳嗽糖浆,拧开盖子,放到嘴边,“咕咚”喝了一大口。法庭上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接着是一片恐惧的唏嘘声。
法庭里乱成一片。
首席法官惊叫道:“乔特斯先生……”
拿破仑·乔特斯又喝了一口。“法官阁下,公诉人的起诉是对正义的愚弄,乔治·萨维拉斯并非死于这位女子之手。辩护方就案情所作陈述完毕。”
钟敲响了12点。一位法警快步走到首席法官面前耳语了几句。
首席法官连敲着小木槌说道:“肃静!肃静!现在休庭。陪审团退席作出判决。两点钟重新开庭。”
比得·迪莫尼得斯呆若木鸡地站立在那儿。有人施了调包计!但不可能。证据每时每刻都处于监护之下。难道验尸的法医出错了吗?迪莫尼得斯转身和他的助手交谈了几句,等他四下寻找拿破仑·乔特斯时,乔特斯早已不见踪影。
两点钟重新开庭,陪审团鱼贯而入,在席上就座。仍不见拿破仑·乔特斯的影子。
那个杂种已经死了,比得·迪莫尼得斯心里想。
就在此时,拿破仑·乔特斯推门而入。他看上去神采奕奕。他走向自己的座位时,所有的人都将目光投向了他。
首席法官问道:“陪审团的女士们,先生们,你们作出判决了吗?”
陪审团团长站了起来。“我们已经作出判决,法官阁下,我们认为被告无罪。”
刹时,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比得·迪莫尼得斯面色惨白。这个杂种又一次让我丢尽脸面,他心里咒骂着。他抬头瞥了一眼,拿破仑·乔特斯正冲着他龇牙咧嘴地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