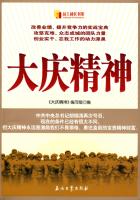我住在这巷子里,夜阑更深听到有鸽子叫,然而自我醒来,天色仍旧漫漫地亮了。这天气转眼间已将是如此分明,但是暗夜的潮气仍旧在,一片片打湿了院子。外面有人声,是俚俗的乡音,简洁而近似轻佻。并且狗也在隔壁的院落中狂吠,凡有行人路经,一个都没有放过。我听得外面的步履加快,连带叱责都于仓促中遗落。那狗的叫声果然使人生厌。然而没有它,早晨只是寂静的,不至于欢腾起来。家家户户的灯光在太阳未出时是亮同白昼,及至晨间,只是一点点垂落在壁间。早起的人一个接一个地起来,在院子里洗漱,接下来便是安排一天的生计。秋天是景色如此鲜亮的一个光景,这时辰里,农时占据主导,代替了所有的人事。我无法观察所有的人,因为早饭未过,一天里的忙碌便开始了。倘若有一件事做,我仍旧会关门闭户,像身在家庭里,人却隐居了似的。这期间有人过来翻看我读的书籍,瞧我在写了什么,我也是尽量如常,且并不答言。这只是一个特别世界里的分工,倘要解释,也只是一句无奈的话。而如果我不做文章,照样会参与到其他人的忙碌中。日子仿佛也可以是这样的闲散,在两类人看来,便有这样的不同。而今我身心与职业俱离散,反见了职业之外的事,有一种格外的亲。
这巷子并不长,走一个来回,不过是半个小时的事。然而我在这里静静的,因为路上遇到的人都不识。唯路边人家有红枣出墙来,半空里悬挂,却每一颗都似曾见过的。在这里我若与人言,说自己早些年便走出,而今是返回了,也丝毫不为过。回头望时,有一条砖砌的胡同,记录了寻常世界里的多少光阴。当我觉察到了这光阴的悠久,而旁边仍旧有摩托车辆载了居民从宅子里出来,这情景,便与任何别处,全无丝毫不同。可早晨有冷气,人像从清水里拎出来似的,那天空,在人抬头望时,眨眼间也如水洗过的一般。
这样的日子,原来别有一种情致。因为是这样勤谨踏实的人家,任何事情做得井井有条,没有半点含糊过的。其时我以一种特殊身份居住在这里,日子久了,倒仿佛从来没有离开过一般。而这样的岁月里,乡思却又分外浓重,好比相见的是儿时伙伴,便不由得会念及家里人。
我是在这里时发现了生活的另一种规律。如果不是这样的日常,我总会找出千般理由,认为还有一种规律比这里的更高。当我这样想时,其实也明白一个最为基本的事实:高下之分在生活的界限里是不存在的。可如我们这般聪明的人,总是会将目下与书里讲述的人事连接,好比说:书上一日,世上已千年。知道了这些,觉得社会沧桑更替,人事日非,便是再也寻常不过。有时午间饭吃过,日光高照在床前,眼里显现的人与事物都那般那般近,那般那般可亲,我就觉得岁月迢迢有层次,端然间万虑皆消;而且我能够在这里写了许多字,并且终日里得闲便忙碌于农事,仿佛儿时旧梦重温,已经回到乡下那长长的日子。产生了这种感觉时又想自己的行为是可笑的,却连院子里孩童四处喧嚷听在耳中都觉得烦了。人世间就是这样的琐碎与平淡。下午时间又到大街上走,遍眼皆是熙熙攘攘的人众,购物访亲的都齐聚在了一处,从这个头望过去,可以看到了那个头。原来这里的狭小,反叫人觉得没有了压力。而街口的古树和镶了字的门楼是沿袭了岁月一天天过来的,它们用心见证了一切,又用树身的斑痕和门楼上的锈色将这些记录了下来。
有时我们站在客观的立场品评人事,觉得世界本色如常。但我们要去谈论身边的事物与人,却觉得这里成了一个例外。譬如我这里写到的这一条巷子,几乎就是中国小城镇的微缩版本。它的入口处站立的居民,是我们在民间电影里习见的人群。他们的着装也是普通的,没有什么特色。他们口中的方言倒是带着独特的韵味,甚至在某一个音节上有着奇妙的回旋,并且有些字句,与我理解的会有出入。但如此种种,都使我意气感激。我跟踪了他们的行踪,看着那些人自门户里出来,在自家院门外嗑着葵花,说些家长里短。有一户人家要娶亲了,就在巷子里搭了高高的篷布,这一处,因为是阔敞的,所以也还没有使人感觉拘谨。而忙碌于婚事的人们偶尔会抬了头,诧异地望着来去的不熟识的行人。娶亲的这家院子,却陷在了一个低处,看得出,是一所几十年的老房子了,为了亲事已经装修一新。下午三点多钟光景,摆了宴席的桌椅都还立在当街,阳光浓烈地照着,那街上行人,俱都是满脸的喜气。
这一回,我看着那些人,连自己也是喜悦无尽。然后便径直回了。等到我离开婚礼的场所已远,身在小巷的深处,连同看天,也觉着了逼仄,心身里却突然发现了岁月的荒疏。我盯着屋里人看,她的举止动作都相宜,民间话里如是说:宜于家室。我便在心里渐渐安定。那荒疏的岁月终究聚拢了,形成一个怪异的气场,把我的二十几年全部笼罩其中。我还去了附近的小学校,是在巷子的更深处。却又因为是假期,看不到一个人。而附近的尘土扬起,像时间上行。我在心里默念,如是再三。我是为这秋季祝福。此外我还为这秋季里的人与事都祝福。下午五点多钟,世界里晃晃荡荡一阵惊动,这深巷里已经有人在准备晚餐了,炊烟暮霭里,我就一心一意写我的文字。天地安宁,我再不会无端里惊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