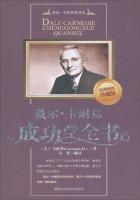一
女孩杨葵喜欢在晴朗的夜晚向窗外的那一轮或圆或缺的明月倾诉她的心事儿。
二
今晚上的她——
您是知道的,亲爱的明月。从我的幼年时候起,我的爸爸妈妈都是一名环卫工人。您是知道的,小时候的我从不缺玩具,我的爸爸妈妈会捡回来各式各样的虽然清洗过了还是破旧的但是仍然可以玩耍的被我喜欢上的小玩具。小时候,因为爸爸妈妈,我不讨厌垃圾,甚至觉得垃圾里也会出现宝,除了我的小玩具,还有我的爱不释手的课外书;即便它们已经缺了皮面或者缺了页面,还是我的珍藏现今的儿童插图版的《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西游记》和《水浒传》。
前些日子,厚厚的雨云铺满整个天空。我看不见您,也看不见太阳。其实我曾经告诉过您,从我拥有了这粉红色的背包起,遇到的每一个下雨天,我都会在出门前把本来背在后背上的背包转移至我的前胸。您应该记得,我是因为不希望我爱惜的这粉红色的背包被雨打湿;您应该记得,这被我爱惜的粉红色的背包仅仅是因为我的妈妈从垃圾桶里把它捡回来,然后用针线手巧地在洗干净的它的窟窿上修补了一只翩翩起舞的紫红色蝴蝶。我的家人——我的所爱的人给我的任何东西,我都会好好地爱惜着:如我的放背包里的弟弟用省下来生活费买下来的送给我当生日礼物的暖水壶;如我的放屋檐下的爸爸拿来别人废弃了的而经过用心地修理粉饰近乎崭新的自行车。
三
现在,我开始要向您倾诉的,是发生在那些下雨天看不见您的日子里的事儿。
您也许不知道,那场幅广而持续的大雨把低洼的城镇浸没在迅猛提升的江河水里。“我们的学生会必须义不容辞地响应学校号召的捐款,我们的每一位学生会成员必须以身作则捐出至少一百元的捐款!”我们的学生会会长就在那场大雨造成洪涝灾害的那个上午召开了临时会议,并随后激情高昂地向会议上的我们这么说道。
您不是不知道,到现在,我也没有向爸爸妈妈多要一元的零用钱。您不是不知道,爸爸妈妈手上攥着的每一元都是从日晒雨淋里赚来的,所以我怎么可能忍心地多要爸爸妈妈哪怕一元的零用钱。同时您也知道的,我的每一个月的零用钱不是刚好一百元吗?但您不知道的是,就在那个上午的前一天,我给我的公交卡充值了七十元——我的每个月坐公交车的用费。您想,那个上午我的身上只有三十元。
那个上午放学后,雨一样不停地下着,只不过时而的变大时而的变小。我从公交车走下来时,雨忽然从小变大了,我急忙躲入公交亭。在亭下,与我一起躲雨的行人有多少,我没有挤出丁点的心思数数。我把我的全部心思想着,该如何集齐那缺少的七十元?我告诉您,我想过马上找份日薪的兼职,然而再想一想我觉得压根来不及,因为学生会的捐款活动就在下午进行,何况爸爸妈妈从来是反对我去兼职。他们会说,您也听我说过的,葵儿,你只要专心地读书!
我还要告诉您,我还想过马上找好朋友借钱,然而又再想一想我便打消了向好朋友借钱的念头。您应该也听我说过,我爸爸妈妈对我说的,葵儿啊,冷,冷在风里;穷,穷在债里!
就想来想去继而就一筹莫展,但雨逐渐变小了,我也准备打开雨伞回家了。在那撑开伞的那一刹那间,您不会想到的,或许您会想到而我不会想到的,爸爸妈妈脚踏着笨重的环卫三轮车忽地进入我的不经意瞭望大马路对面的街道上的视线里。我的爸爸妈妈奋力地脚踏着三轮车的样子,我的爸爸妈妈穿着橙色底黄色条纹的厚雨衣奋力地脚踏着三轮车的样子,我一一清晰地望见了。
为什么我要烦恼那缺少的七十元?我要告诉您,我那时是激灵般地这么想的。难道三十元不是捐款,一百元才是捐款?难道捐款只讲究多少不讲究心意?我还要告诉您,我那时简直想把手上的伞柄紧紧地握在拳心里,那虽然是瞬间的感觉但简直就像手上紧紧地握着一个盾牌,然后用这盾牌无畏地想要去抵抗会长的提出的“至少一百元”的尖锐要求。嘿,当然了,那只是我看来的尖锐的要求。
四
您听到这里,我一直望着您,现在的您好像带着微笑地在问我,葵儿,你的胆大的抵抗结果怎么样了?
我的胆大的抵抗结果先被阻塞了,怎么跟您说呢,其实可以简洁起来一句不长不短的话:我赶在捐款活动开始前,我去找了会长,会长他的名字叫萧晨,我在好不容易找到他的面前把我的想法毫不保留地倾泻出来,然而后来的,我却听到他跟我说对不起,他不会改变向我们成员提出来的“至少一百元”的决定。
您想听那详细的经过吗?嗯,我一直望着您,我知道了,我的任何的倾诉您都乐意倾听。他,我要说了,那详细的经过,他听了我的想法后,最初是没有任何表情的反应只是把他的脚步停住。可他身边的那位倾慕着他挽着他臂弯的女伴——我当然知道她,她是我们的副会长,叫江婷婷;她与会长同年级,与我高一年级。若不是我从他们的身后跑近他们,我想她不会收回那句对会长说的娇嗔的话的。您想听她的那句娇嗔的话吗?嗯,我一直望着您,我知道了,我的任何的倾诉您都乐意倾听。晨晨,我要说了,她的娇嗔,晨晨,你好坏啦,我约你中午到优佳大百货的一楼咖啡厅,你不但又一次爽了我约了,还害我毁掉了我的裙子啦,不过下次我再约你,你准时赴约,我就不生你的气了。
她,我跟您说,她也听见我的要求,然后一张口一个劲儿地驳斥我根本无心无意拿穷来当借口,还讥讽我当今世道哪有可能像我那样拿不出一百元的穷学生,可是她面向会长时总是变得柔情似水、笑靥盈盈,甚至会长听她帮口的话到了有点不耐烦地甩开她的缠着的手,她“哎呀”微微一声后仍然用她白皙的手重新挽住会长的臂弯。那爱情,我在她身上见识到它的魔力:可以使一个女孩无不掩饰地表现出判若两人。
哦!我对您感到抱歉了,我说着说着有点偏离了,但也许我也是一个女孩子,也许我还是一个像她一样地想追求心的悸动的普通女孩子,所以我才比较容易忽视她对我的驳斥和讥讽。那时候,我真正想见到的是会长的反应。一开始,他听了我的想法没有表情的反应,我倒期待他的开口说话,可当他开了口说话,他的第一句话说的却是我最不想听见的“对不起”。
您听到了“对不起”,您应该与我一样立刻气愤会长的“对不起”以及会长继续说下去的话:“我不会改变向你们下达了的‘至少一百元’的决定。如果你真的没有一百元,我现在可以借给你一百元。”正是由于我的气愤,他向着我开口说的话,其实也只有这两句。而我正是由于气愤,在转身跑开之前,足足说了两句话回击他:“我谢谢你了,如果我要借钱,我只会向朋友借!还有我的身上是没有一百元,但我有三十元,如果我要借钱,我只会借七十元不会借一百元!”
您是知道我的,我怎么可能真的向朋友借钱。所以当时我想着要革命,地点学生会,时间半小时后进行的捐款活动,目的当着所有人的面把我的三十元投进捐款箱内。您听了我的革命,您一定为我的革命捏一把汗。我当时心儿喊着革命,其实在接下来的半小时内,我的心儿是揣着革命怦怦地跳着。是的,我当时是害怕着的,但我当时可以肯定自己没有一点儿的退缩,而且预先把钱包里的三十元拿出来放到掌心里紧紧地捏着,等候着会长上台宣布捐款活动的开始。可您不会想到的是,我的革命因会长提前夭折了。
您听清楚了吗,我的革命不是成功不成功,不是失败不失败,而是在我紧张地准备发起前夭折了。当时会长款款地走上台往台下看,可我随即感觉到他的目光是看着台下的我,他的话是对着台下的我说:“我仔细想过了,我虽然是你们的学生会会长,但我不过是同你们一样的学校里的其中一名普通学生,我没有权利非要决定你们捐款至少一百元,所以你们想捐多少就捐多少。当然同时因为,我相信你们对于不幸发生水灾的地区人们都会有一颗怜悯之心。”
五
他,从那时起,我好像重新认识了。他,好像不再是高高在上的会长,他叫萧晨,是一个带着温暖的男孩;特别他的微笑,我从那时起才发现,既温柔又好看。莫怪江婷婷会迷恋他;莫怪除了江婷婷之外,有不少的女孩们因他心里种下了一颗暗恋的种子。而我从他身边走过除了重新认识他、发现他的微笑,还心湖如荡漾般地捐出我的三十元。后来在将要离开会场时,我不自禁地回眸他一眼。您可要知道,那是我第一次主动向男孩子回眸,那一刹那,他那微微低着头清点捐款数的专注的背影又让我心满感激。当晚,我带着对他的感激,以及我的身无分文的真心,我打着雨伞来到我的小前院的西面墙角下。
您现在看到的,我的西面墙角下的一带小花基的黑色泥土上正有向日葵的幼苗沐浴在您为天地洒下来的柔和光芒里静静地生长着。那一晚上,我打着雨伞用小铲子把其中的一株向日葵幼苗移植在可口可乐瓶子制作成的小花盆上。那一晚上,那小盆栽带着我对他的感激,以及我的身无分文的真心,被我暂时放置在我的卧室的书桌上的粉红色背包的旁边上。
那一晚上的前些时候——近黄昏的时候,收工回来的爸爸妈妈告诉我,他们在优佳大百货的门口街边上的一个垃圾桶里捡到了一条完好的连衣裙。看着他们每一次从垃圾里捡到了“好宝贝”的高兴笑容,我也高兴地期待他们把装着“好宝贝”的百宝箱似的布料袋子打开来。我不止一次这样跟您说过,而这种因垃圾的高兴,我想在这世界上我家不是独一无二的,无国界的您应该轻易地见得到。
唔,您不用问我那条连衣裙是怎么样子的,因为我就要告诉您。那条连衣裙不仅爸爸妈妈说的完好,还十分特别的美丽。远远看上去,它整体纯白,但只要您向它渐渐靠近,它便是栀子花的美丽的化身。它的每片巴掌大小的丝缎就是一朵绽放着的栀子花,如此纯白而美丽的栀子花连结成一条如此纯白而美丽的连衣裙子。然而它还是被曾经拥有它的人扔掉了,然而它的上面不过是沾了咖啡迹,然而我的妈妈既然捡到它,我的妈妈就发挥了她的耐力把它彻底洗了干净。
唔,您不用问我有没有把那小盆栽送给萧晨,因为我就要告诉您。第二天我没有贸然跑近他,您要知道他的身边不止江婷婷那样的女孩子围着他,所以在课间休息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只能躲在柱后或树后远远地等候着他。等候着他一个人的时候,其实那简直好比草丛中寻找一片四叶草还要难,不过终于让我等到了。我悄悄跟着他,他似乎在逃离着什么,最后他逃到了校园的一个最幽静角落的竹林里。
“会长!”我鼓足了气走近他,当时他背向着我。
“你们可不可以让我清静一下?”
“对不起!”
“是你?你等一下!”在我真的以为烦扰到他正准备转身离开时,他也向我转身过来。于是我跟他无意间地四目相对,而在我想立马躲开他的视线真的转身离开时,他却立马把我叫住了,然后问我:“你是找我?”
“是的。”
“什么事?”
我向前几步,究竟几步,我忘了,反正来到他的跟前递上我的小盆栽。
“会长,送给你的。”
“我破坏了你的革命,你还送东西给我?”
他微笑着那么说道,我不禁愣了一愣。
“你怎么会知道的?”
“因为你说了两个如果。它是什么植物?”
他从容地回答我,从容地接过我手上的小盆栽。而我反倒有点拘谨了。
“它,它是向日葵,的幼苗。”
“我还是第一次收到向日葵幼苗的礼物。”
“会长,你不喜欢?”
“我很喜欢,谢谢你!还有我必须邀请你在今个星期六到我家来。”
“不必了,这小盆栽不用钱,我家前院的花基上就种着向日葵!”我起初以为他邀请我到他家是为了答谢我送给他的小盆栽。
“你送给我礼物,我当然要邀请你参加我的生日会。”
“会长,星期六是你的生日?”我怎么会想得到四天后就是他的生日。
“嗯!”
“会长,我——”
“哎,即将生日的人邀请你参加他的生日,难道你想要拒绝?”
“我不是拒绝,我是不明白。因为连同昨天,我跟会长你只说过两次话,即便我今天送给了你小盆栽,你也不必要真的邀请我参加你的生日会!”
“当然要!”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我欣赏你。”
我也怎么会想得到他会说欣赏我,那种心的冲击我一时负荷不来。
“我还是第一次听见会长你在开玩笑。”
“你不相信?”
“我是不相信。如果让我相信,你就说出原因!”
“好吧,原因是,你昨天的两个如果和现在我手上的小盆栽。”
“就这么简单的原因。”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
“什么原因?”
“我现在不说,等你到了我家后你自然会知道最后的原因。”
您知道吗,他又向我微笑起来了,但我总觉得他的这一下微笑里夹杂着一丝狡黠。
“看来我不去你的生日会也不行!”
“嗯!看来你挺喜欢穿裤子的。”
“你怎么会知道?”
“因为你每次到学生会开会都会穿裤子。”
“你会注意我?”
“你看起来是一个很恬静的女孩子,我只是不敢靠近你。”
您听见了吗,而且他说这句话时,他的神情还是认真的,我不由自主地有点害羞了。
“我自己倒不觉得。”
“你——”
“怎么了,会长?”
“你可不可以在我的生日会上穿裙子?”
“为什么?到你的生日会上的女孩子一定要穿裙子?”
“当然不是一定要穿裙子,只是我希望你为了我穿裙子。”
您听见了会想知道,他用如此煽情的话跟我说,我的心防是不是已经动摇了?我告诉您吧,我是动摇了。
“那,那我就穿裙子来吧。”
“嗯!”
而在我亲口答应他时,他竟然露出了灿烂的笑容。我想,当时换成您也会跟我一样觉得不可思议吧。
六
四天后,我遵守了自己的诺言和履行了我跟他的约定,我穿着裙子参加他的生日会。在这四天内的每一个晚上,我现在告诉您,我是多么想与您见面,可是尽管天不下雨了,风却是像被谁下达了命令似的相当地安静起来,不允于吹散遮盖着您的云层。在这四天内的每一个晚上,我现在告诉您,我是多么想把新的心事于您倾听,可是看不见您的光容,我又不知从何向您倾诉。我现在轻轻告诉您,在这四天的第一个晚上,我忽然发现自己的心里像我刚才说的那些女孩子一样种下了一颗暗恋的种子。那从未有过的感觉让我期待着他的生日会,让我放学回家后无时无刻地想跑去小前院触摸晾在衣架上的栀子花裙子究竟干了没有。那从未有过的感觉,您听了不要笑话我的叨唠,因为我真的从未有过那样的感觉。
也许由感觉的作用下,穿着栀子花裙子的我却迟迟徘徊在他家的楼下,直到他忽然出现在我的身后并牵住我的手带着我走入通往他家的电梯。在明亮的电梯里,他依然牵着我的手。他不说话,我也不说话,我们似乎都等着对方说话。我不敢挣开他的手,其实我的心底里不想挣开他的手,我不敢抬头正视他,其实我不想让他看见我在他牵我手的一刻羞红的脸。而他虽然看起来毫不发现了的样子,但我隐约觉得他还是发现了,因为他牵着我的手,我手上的热度,因为他牵着我的手,我手上的搏动。那是最不容易看得到的却是最容易触摸着到的,他牵着我的手,他只是装着若无其事。
您听我说到这里,是不是觉得他正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想捉弄我一番?他果然如此,就在我们刚走出电梯口,就在我毫不来得及防备之下,他忽然停下来,带着他温柔而好看的微笑对我说,“杨葵,你很美!”
我顿时难抑心跳加快,我随即不由自主地咬住自己的下唇,我是害怕我剧烈跳动着的心脏会从嘴里蹦出来。
“你怎么了?是哪里不舒服吗?”
他目不转睛看着我,我的心动然的样子,在他看来倒像是我哪里不舒服了忍着疼痛。
您是不是觉得那一刻的我有点逊?您总会了解我,我也觉得那一刻的我不是逊,只不过是一时难以控制的真情流露。可不随即,我就恢复以往遇事迅速泰然自若起来的样子:“我哪能不舒服!我还没有吃你的生日蛋糕呢!”
“好啊,我就欢迎你吃我的生日蛋糕!”
难道他只邀请我到他家为他过生日?我听了他的话不得不胡思乱想。真的,他真的只邀请我到他家为他过生日!当他为我打开他家的门,当我看见他的华美的客厅里除了我与他空无一人,我就更加胡思乱想了。
“杨葵,来吧。”
杨葵!到那时,我才发现到他已经知道了我的名字。“会长,你知道我叫什么名字?”
“我知道你的名字有何不妥?”
“你怎么会知道的?”
“知道一个人的名字并不难,何况是你!”
“为什么?”
“你等一下就知道了。”
那时,他牵着我穿过客厅走上二楼的楼梯。
“为什么我等一下就知道了?”
“你真多为什么耶!”
他莞尔一笑,我有点不好意思了。“你又不回答我。”
“你放心,你走完这段楼梯就真的知道了。”
那时,他牵着我从二楼走上三楼的楼梯。同时,我才注意到他的家在一栋公寓楼的一座单位里竟然拥有自己独立的楼层。我随即诧异放慢脚步,甚至想挣开他的手,其实那时我隐隐约约听到了从上面传下来的音乐声和说笑声。
听到了三楼的音乐声和说笑声,我多多少少替自己感到尴尬,您笑话我吧,谁叫我那般自以为是。
从去三楼的楼梯上为什么只听到隐隐约约的音乐声和说话声,在我看见了楼梯口我才知道,在楼梯口原来有一扇印花的立地玻璃门。当我们一起来到楼梯口,他放开牵着我的手是要为我打开那扇玻璃门。
七
门后是一个看一眼都会喜欢上的玻璃室,地面上铺着绒绒的绿色地毯,透过四围的墙和天顶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外面的景色,还有挨近着玻璃墙的与相同间距竖立着的若干条细圆杆子,上面的天平挂钩一边挂着散发着柔和光线的琉璃灯一边挂着开着淡蓝色小花的吊兰。他的生日会在这天台的玻璃室里进行着,他所邀请的人在丰盛的自助餐桌之间交谈着、欢笑着。接下来,您会与我一样想也想不到的,就在我为这玻璃室充满好奇与欢喜地想要走向前展望外面夜景时,我忽然听见一把好像我弟弟小刚的声音在喊“姐姐”。
我就循声看过去,弟弟杨刚居然真的出现在我的视线里。
“小刚!”
“姐姐,你来了。”
“小刚,你怎么会知道我来?还有你怎么会在这里?”
“是萧晓的哥哥告诉我的,当然还是萧晓的哥哥邀请我来的。”
萧晓的哥哥!我一听了以我灵敏的脑筋,我怎么会不马上知晓是谁。您,我会慢慢告诉您。
萧晓是我弟弟的同学,在我烦恼“至少一百元”的那一天,我才认识他。所以那一天我认识他的前后经过,我记忆犹新。
记得,我在公交亭想到了应对“至少一百元”的办法后,便打着雨伞跑出公交亭,然后追着爸爸妈妈踏着三轮车的身影跑回家。
“爸爸,妈妈,我回来了!”我一打开小前院的街门便朝着厅堂喊。
厅堂连通了我家的小前院和小后院。而爸爸妈妈每回的下班回到了家都会第一时间把他们的环卫三轮车安稳地停放在小后院的铁皮棚下。
“你怎么知道我们回来了?”爸爸随后来到我的面前,但他不是为了我的呼唤走来,而是他把他的三轮车停放好后,他就会来到小前院投入他的副业——在屋檐下,给来往的过路人修补自行车来赚取额外的微薄的收入。
“我在公交站台看见你们,”我说,“我就追着你们的环卫车跑回家来了。”
“傻傻的。”爸爸笑了笑说,“下雨路面都会滑,你以后别追着跑了。”
“我知道了爸爸。”我认真地回应爸爸一声后跑向小后院。“妈妈!”
“葵儿,回来了?”
“嗯,我回来了,妈妈。”我跑到妈妈的身边还没稳住脚便问,“妈妈,你买了什么菜了?”
今年的爸爸妈妈在环卫所的清扫路段的抽签中,他们抽到了中山路——市区内的一条繁华的商业街——的头尾。爸爸清扫的街头,中山路的优佳大百货矗立着;妈妈清扫的街尾,有一个大型的菜市场。
“买了一条大头鱼。”在铁皮棚的切菜台前,妈妈一边忙着收拾手上的这条鲜活的大头鱼,一边对跑到她身边来的我说。
“清蒸吗,妈妈?”
“葵儿,妈妈想下次才给你清蒸。现在,妈妈想用这条鱼的鱼身给你弟弟煮汤。”
您知道,我的弟弟只比我小两岁,今年就到他参加高考。
“好啊,妈妈。”所以一听到妈妈的那条大头鱼的鱼身即将成为弟弟补充营养的鱼汤,我当仁不让。
“就剩两天了,我希望小刚营养满满地去高考。”妈妈的言语洋溢着对备考住宿学校的弟弟的牵挂。
“妈妈,你放心。上一次我给弟弟送汤时,他高兴地跟我说,他对高考很有信心!”
您知道,从小我就跟弟弟无话不谈。
“那就好。”妈妈听我说了高兴了,因为她信任女儿我所说的话,因为她知道她的女儿和儿子从小到大感情好,因为她晓得女儿我从来不说谎。
“妈妈,那大头鱼的鱼头鱼尾呢?”
妈妈很会精打细算,她不会只要鱼身不要鱼头鱼尾。
“我还买了豆腐干。”妈妈说。
“豆腐干!”
“我准备用大头鱼的鱼头鱼尾给你烧一味你喜欢吃的大头鱼豆腐干。”
“好呀,妈妈!那我帮你摘点青葱。”只要是妈妈亲手做的大头鱼豆腐干,我是一点也不会计较究竟是鱼身还是鱼头鱼尾。
“不用你摘葱了,葵儿。你去做你的课业吧。”我的妈妈,您看的到,她从不偏心。
“妈妈,我的课业不急交,何况摘点青葱又花不了什么时间。”我说着取下无论晴天还是下雨都被我们挂在铁皮棚下的铁架子上的那把长柄雨伞,然后把它撑开来走向我家的小菜园。您见到小前院的小花基就见到小后院的小菜园,它虽然不过是铁皮棚正对面的墙脚上的一个挨着一个的圆形瓦盆里的黑泥土上的种着的青葱儿、芫荽儿和枸杞儿。我记得,我打着雨伞采摘青葱时,我是满心愉悦的。为了什么?也不过是妈妈即将烧煮的美味的大头鱼豆腐干,以及雨落瓦顶上的、棚顶上的发出像音乐的声音。
吃完午饭后,我没有午休,我带上我的粉红色背包(出门前,雨不停下,我便把背包放前胸)和弟弟的大头鱼鱼汤(弟弟的鱼汤用一个提式的暖壶装着,而与暖壶同装在一个纸皮袋里的是喝汤用的匙碗)坐公交车前往弟弟的学校。
“姐姐,你有没有被雨淋湿了?”弟弟已经在学校门口等候着我。您不知道当时正下着能够溅起水花的大雨,弟弟打着单薄的雨伞立在那场大雨中,我反而应该比他更关心他有没有被雨淋湿了。
“小刚,你才是有没有被雨淋湿了?天都下大雨了,你为什么不暂时躲进门卫室里?”弟弟的学校门口不是没有门卫室,他那么地傻里傻气地立在雨中等着我,我怎么可能不心疼弟弟。
您猜弟弟怎么对我说的。他说:“姐姐,天都下大雨了,你还不是坚持要给我送鱼汤来。”
我点点头,我心暖烘烘地简直无话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