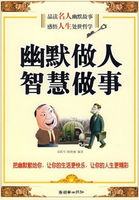小店沉思
这是一个不起眼的小饭店,要不是它坐落在解放门东马路旁的黄金地段,就是他们经营的三鲜锅烙再有风味,我敢断定,也很少会有人光临。
刚入冬的一个黄昏,我和一起来齐齐哈尔市参加全省党政干部基础科考试的老沈,穿过下班的自行车人流,快步来到这家锅烙店门口。透过镶着霓虹管灯的玻璃窗子,我看到这个往日冷清的小店,非常热闹。往常光秃秃的窗户台上,堆满了各式各样的手提包。这时,老沈拉开门,我随后进去。可能是职业的缘故,对这种热闹的场面,我非常想看个究竟不可。
这是一个两张八仙桌拼起来的由十多个人组成的小宴会。奇怪的是,这么多的饮酒者中,只有一个穿警服四十岁上下的男警察,其余十多人都是长相漂亮的少女。一张张白净的脸上,镶了一双双水灵灵的大眼睛,一个个苗条的身段,穿了一身身入时的衣服。我们在一个角落里坐了下来,又不自觉地打量着这些姑娘们,我仿佛头一次发现了人间的美。
我一边羡慕着她们,一边和老沈猜着:“她们是业余戏校的,还是体校的……”
从人们嘈杂的话语中,我们隐隐约约地听有人说:“她们是刚从省城汇演归来……”
听了这些话,我越发感到这个小店不配招待这些贵客。反过来,不是这些贵客,使这个平常的小店增添了光彩,也不会又招来这么多的顾客。
再看看这个小店,服务员没有一个让人看了能增加食欲的,身上穿的白衣服,沾满了油垢。小店经理,是一个四十岁上下的胖女人,两只眼睛犹如火柴杆划的两道缝,走起路来还深一脚浅一脚的。
锅烙端上来了,我们一边吃着,一边观察着。只听她们向那个年长的男民警敬酒声,一浪高过一浪“哥们儿长、哥们儿短”的,话语越来越粗鲁。我听着,听着,觉得这语言和这相貌不大相称。不一会儿,她们吃完了,一阵风似的走了。
“这么多的漂亮姑娘白瞎了……”胖经理一边端起她们用筷子弄碎的一碗锅烙,一边冲着我们说了句。顿时,我俩全糊涂了。
后来,才知道,这是市郊一个青年管教所的演出队,在去省里演出后,回来到这共进晚餐。
顷刻,在我脑海里,就像晴天响了一个炸雷。我默默地离开了小店,留给我的只有叹息,沉思。
我的勤奋斋
刚到而立之年,就能有个十多平方米的书斋,而在周围的许多人中,我的藏书也数得着,就这一点,有多少人羡慕我。
记得著名漫画家华君武有一幅漫画,画上有个人在墙上画书橱,题字是:“买书不读书,不如画个大书橱。”每当有人夸我书多时,我总怕人说我买书装饰房间,然后,我赶紧解释说:这么多书没有一本学好的。
上小学的时候,我学着认识几个字,能看懂几本儿童读物了。一天,我看到娘夹鞋样的旧书,竟是一本故事书。我生怕不懂事的弟弟妹妹给我撕了,就跟大一点的孩子去供销社,找售货员软磨硬泡,要回个肥皂包装箱,用花花绿绿的香烟盒糊上,再安上一把小锁,这就是我最初的书箱。
上初中时,我对文学发生了兴趣,更迷上了诗歌。生不逢时,正赶上十年动乱,偶尔来了几本工农兵诗选之类,我如饥似渴,见书就买。
我早就盼着能有一个名副其实的书斋。上高中时,全家六口人挤在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小屋里,炕上睡不下,我就在地下用砖支起了一个床。到了晚上,我和爸爸的矛盾不可调和,我想多看一会儿书,爸爸劳累了一天,喝上点儿酒,恨不得马上闭灯,没办法我只好让步了。只有爸爸出差或回来晚时,家里才是我的天下。为解决这个矛盾,妈妈也很为难。
成家后,我做的第一件家具就是书柜。这书柜和大衣柜差不多大,可放六层书。当时虽然住在小土屋里,学习的劲头可没减。
前几年,我住进了两屋一厨的楼房。我把阳面大屋摆上两个大书柜了。
我看完了《光明日报》上的几篇《我的书斋》征文后,我觉得就目前的学习条件来说,应该知足了。这个书斋,比大作家刘绍棠的蝈笼斋和科普作家叶永烈家阳台书斋强多了,虽不敢称万卷户,叫千卷户总算可以吧!
去年我拢了一下,总共买了一百五十多本书,照这样速度下去,30年后离万卷户差不远了吧?然而,最使我忧心的是:什么时候才能坐下来系统地读本书呢?
辛辛苦苦把书买来,翻了几下编上号、按上章就算完事,真说不出有几本书是从头看到完的。
总不应该像有个作者说的那样:“不能以藏书颇富骄人,而不自惭于思想和知识的贫乏。”
为了自勉,我给书斋起名——勤奋斋。
藕荷色的……
真正认识这个颜色,还得拜你为师。那天,我们并肩走在马路上,你主动跟我说,你喜欢藕荷色,我故作镇静地看了看你身上穿的连衣裙说:“那你今天怎么穿上了紫色的裙子。”你用纤细的手捂住涂了变色口红的嘴嫣然一笑,马上给我纠正:
“我这叫藕荷色……”
我也说不清这个颜色有什么象征意义,总的来讲,穿这个颜色的人太少了。
看得出,这是一个高傲的颜色。从中,也看出了你的性格。
你穿着这藕荷色的连衣裙,来到太阳岛绿阴下,撑起了湖蓝色的阳伞,我为你摄下了这个珍贵的镜头。
石坝上,到处可见到一对对甜甜蜜蜜的情侣。要不是时间拉开的距离,要不是空间不合理的位置,我们会比他们甜蜜。
草坪上,留下你的倩影,大街上,飘着你送行的歌声。
餐桌上,你陪我咽下几口辣酒,月台上,握住就不想松开你的手。
感情可以脱缰,理智却不能撒手,洪水再大,堤坝却不能低头。
女孩子有女孩子的向往,男子汉有男子汉的追求。
爱情未必就是婚姻的伴侣,爱情未必就是自私和占有。
我把卧室刷成藕荷色,一百个人问我,我有一千个理由。
你把信写得朦朦胧胧,好像我们初相识,欲说还觉羞。
宴席上,我喝过许多种酒,还头回品尝这分别的酒,是苦是甜,是辣是酸?日子越久,味越醇厚。
春天来了,白色消失,绿色将遍及北大荒的原野,我仿佛看到,从远方飘来一片美丽的藕荷色。
双阳河忆旧
夏日,北大荒像一位丰满的少女,打扮得令人注目,我却无心欣赏。到跃进农场采访,我特意来看望草甸子上静静流淌的双阳河。我就像见到一位老朋友一样,默默地注视着河水,14年前的情景,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那年冬天,我们全班四十多人,告别了母校——九三中学,分别被两辆汽车送到这儿来。
当时,我们心里还挺高兴,觉得这跃进农场离局里又不远,可没想到,汽车走过了场部,驶过了双阳河大桥,开上了山冈,拐了两个弯,又跑了足有半个小时,才到我去的连队。满天小雪,天却不冷,加上刚刚出校门的好奇心,没有什么异常感觉。
第二天一早睁眼,看到窗外白茫茫一片,心里不觉一颤。还得起早上工,这时我一下子想起了在家时的暖和的被窝。
这段时间,我虽然刨过粪,扬过场,给我印象最深的,要数修双阳河水利工程。
修水利的动员大会,在一个背风的路旁沙坑举行。当时一个团领导作动员,据说要在双阳河边种水稻。也不知是谁出的馊主意,那小小的双阳河水,怎能供上这么大一片水田。现在想起来那件劳民伤财的举动,真是荒唐。也说不清到底花了多少钱,耗费了多少人工,伤过多少人。
寒冬腊月,习惯上正是农场的猫冬时节。不知是谁瞎指挥,把忙乎了一夏天的人们都赶了出来。无奈,一个个在野外修水利工程的人,穿得浑身都圆了。我穿着爸爸的黑旧棉袄,腰里扎着一根麻绳,脚登一双从知青卖破烂的麻袋里捡来的翻毛皮大头鞋。每天往返二十多里地,迎着刺骨的寒风,在雪地上走着,艰难地走着,一步一个脚印。
也是在这里,我第一次当上了连队的宣传报道员。田间排原来的报道员,是个北京女知青,她听我同学说我的作文写得好,她就自动退出了报道组。在这个报道组里,我首先写了16字令三首《战双阳》。这篇稿被《黑龙江文艺》社退回后,被连队报道组发现了,硬给抄到连部的板报上。后来,在春节联欢会上,队里小学校一帮小学生又朗诵了这三首词。在队部食堂里,人们把目光转向我时,我的脸一下子红了。我感到爱好文学的欣慰,这也是我的作品第一次被社会承认。
当时,市场上买不到灯泡,队里一个比我晚几天参加工作的青年王美宫,知道我爱看书,就特地为我找个拖拉机上的小灯泡,放在我的床头上,加上个变压器,我高兴了就看一会儿书。尽管这灯光微弱,却使我看到了光明,使我从复杂的人际关系中,看到了光亮,自立,是人生的出路。
双阳河还在默默流淌,不知她一路曲折流向何方,只要是向前,迟早会汇入海洋。
我思念你双阳河,你给我美好的幻想,是你教我如何生活,教我展开想像的翅膀。
人生归宿
人,作为社会发展至今天的高级动物,从呱呱坠地,就开始了人生的匆匆旅行,都是在匆匆奔向自己不可避免的终点——死亡。
死亡,是人生不可避免的归宿。有史以来,人类已有无数个生命走向这一归宿。更多的是代代相传的生者,对死亡闻之骇然,谈之色变,因为无人知晓自己将如何死,或者说何时死。对死亡的恐惧激发起人们对永生的追求。从尼罗河畔威严的金字塔象征着法老对他的臣民的永恒的统治到中央之国的秦皇汉武,寻访仙方秘术以期永寿,都表现了对生命的永恒性的关注。
科学尽管还无法使人永生,但至少可以使人长寿,由此,保住青春、延长生命又成了人们孜孜以求的目标,各种长寿药物常常供不应求,气功、瑜珈术在世界各地拥有振臂一呼而应者云集的魔力。人类用延寿的方法同死亡对峙。然而,人寿无论多长,毕竟还是有一个终点,人的生命总是一个过程。人是宇宙之子,他同万物一样,有生必有死,人也确是万物之灵,具有其他生物所没有的理性,当人们意识到,既然永生不能企求,长寿总有终点,死亡不能避开,因此最好的办法,还是运用理智的方法来重新对死亡加以审视,让每个人面临它时,会有一个坦然而又相对科学与人道的态度。
其实,人一出世,就是在向死亡迈进,只是进程不同罢了。一次,我来到佳木斯市东郊殡仪馆,为一朋友的老母送殡。三个小时的排队时间,我好像悟出了许多人生的真谛。
殡仪馆院内,成百上千的送行者,在这里焦急地等待着,就像为远行的亲人送行。这里,是城市的另一种出口,它不像火车站,也不像客运站,不售返程票。
看着抬进去的一具尸体,等候的人们,在仰望二十多米高的烟囱,一阵黑烟过后,一阵白烟直冲云霄。用不了半个小时,就送走了一位逝者。
看得出这里也是人生的一站,是从生到死的终点站,可又是一个起点,是驶向另一个世界的起点。
今天,人类的智慧虽然已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但人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却仍然无时不在困扰着人类。据记载:古往今来,在地球上已经存在过的800亿人都毫不例外地走向了它,而且即使在科学技术相当发达的今天,或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也无法使生命永存。
在人生的航道上,每个人都可以坐在自己的生命之舟上,各自用不同的方法驾驶它,然而,他们的去处都只能是死亡这一神秘的终点。对待死,不同世界观的人有不同的认识。毛泽东同志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写道:“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曾说:“死是两种境界之一,或是灵魂与肉体俱灭,死者对于任何事物都无知觉,死就如同平时沉睡无梦的睡眠,一定是一个奇妙的境界;或者如世俗所说,死亡就是灵魂从一处移居到另一处,如是此,人可到另一个世界中去会以往所有死去的人,那也是一种莫大的幸福。”苏格拉底的假设,尽管能让人对死产生一种乐观的态度,但几千年来,毕竟没有人能够对此加以证实,因为死去的人不可能再来向人作出死亡是怎么一回事的说明,而活着的人又不可能有死亡的经历。
殡仪馆是一个城市的出口,以每天十几个人的速度奔向黄泉路上。无论是谁,领袖和伟人也毫不例外。如此人们都应该淡泊人生,什么职务、级别、职称等等都不在话下,什么嫉妒和被嫉妒,一切鸡毛蒜皮的事都没有必要去计较。
有人曾说过:“一个人只有真正冷静地思考过死亡的问题,才可能真正地成熟。”这话的正确与否也许难作评价,但未经审视的人生是没有价值的这一点,也许是不应该有异议的。
每到殡仪馆送行一次,我的心灵就会得到一次超凡脱俗的净化。莎士比亚说:“人可以通过两种途径来超越死亡,一是留下子孙,一是留下著作。”文天祥所谓:“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即要用一生对人类和社会的贡献来使人心满意足地去迎接死神。
我的生日
正巧,我过34岁生日这天,赶上在哈尔滨市参加一个会议。会议的最后一天,认认真真地进行着最后一项主要议程——会餐。
晚宴开始了,风趣的主持人致了祝酒词。与会人员一边品尝着佳肴,一边窃窃私语。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后,我似乎在寻找一种温馨的气氛——生日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