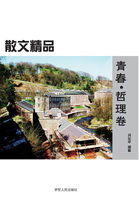最终,孟古青还是住到了延禧宫,宁楚格隔一段时间便会偷偷去瞧瞧孟古青,给她送些吃食,起初两个月,孟古青与彩蝶都不愿见她,她只得把东西放在门口,默默离去。
后来,彩蝶也肯出来拿东西了,还会跟她说声多谢,宁楚格略感欣喜,她总觉得多付出一点,心里的愧疚便少一点。终究,她不能确定到底是不是孟古青害了她的孩子,可她却实实在在的害的孟古青到这样的境地。
到最后,她的肚子越来越大,离生产的日子越来越近,可她还是会按时来看孟古青,孟古青也怕她挺着大肚子在门外冻坏了,因而便请她进来小坐。
如此一来,宁楚格便来的更频繁了,每次来,孟古青都是在礼佛,宁楚格就坐在一旁陪她一会儿,偶尔说些话,大多数时候都是默默相对的!
直到那一日,宁楚格又来看孟古青,她喜滋滋的带了自己做的梅花糕来给孟古青。
宁楚格笑言:“姐姐一直不喜欢梅花的味道,可是我确实最喜欢的,可从前姐姐一直肯纵容着我···不过,难得的是,姐姐虽不爱梅花,却能喜欢我做的梅花糕,一到了冬天就嚷着要吃呢!姐姐可还记得?”
孟古青的眼睛深的像一口古井,那样的平静,似乎再也起不了一丝波澜,平静道:“那好像都是上辈子的事儿了!”
宁楚格的笑容僵在唇边,低下头,愧疚道:“抱歉!都是我···”
孟古青摆摆手,淡淡道:“往事不要再提了,都是我的命罢了!不怪你···不怪你···”
宁楚格眼眶含泪,恳切道:“姐姐,我今儿带了梅花糕来,我自己做的,姐姐好歹尝尝!”
孟古青微笑道:“多谢你的心意,只是何苦,你都是有身子的人了,这样劳累也不利孩子。”
宁楚格笑道:“无妨,能为姐姐尽点心,我心里便舒坦!”说罢递了一块梅花糕到孟古青面前。
瞬时,两人不约而同的愣住了,这画面像极了焚宫那一日,不同的是,那日是在永寿宫,而如今是在延禧宫后殿的静室;那日宁楚格递来的是福临与荣惠大婚的喜饼,而如今是梅花糕······
孟古青怔怔的瞧着那梅花糕,并未伸手去接,宁楚格的手微微一颤,立马缩回,旋即湿了眼眶。
气氛有一瞬间的凝滞,宁楚格过了半响,才缓缓抬起头,哽咽道:“姐姐!对不起!”说罢,便把那梅花糕塞进自己嘴里,大口嚼了起来,流泪道:“真的对不起,对不起!”
孟古青轻轻拾了一块梅花糕,咬了一口,浅浅笑道:“味道极好!这些年过去了,你的手艺却一点儿没变!”
宁楚格脸颊还挂着泪水,偷偷瞥了眼孟古青,低声道:“多谢你还肯吃我做的东西···”
孟古青怅然道:“当初那些事儿,证据确凿,莫说是你看不清,便是我自己都想不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都无法替我自己辩白,又怎么能怨你?你恨我害了你的孩子,便来害我,原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这些年啊,我早就不是当初的我了,还有什么看不透呢?终究,我也没有被那场火烧死,你也不算害了我性命,至于这容颜,呵~对我而言又有何用?在永寿宫里与在这里又有什么分别?我反倒觉得如今更自在些!”
宁楚格咬了咬下唇,终于抬起头,定定的瞧着孟古青,问道:“有一件事,我一直不明白,今儿既说起了,我实在是想问个明白!”
孟古青点点头,淡然道:“问吧!”
宁楚格道:“既然你什么都知道,那···那日,为何要说是你自己放的火?你为何不说出我来?”
孟古青怔怔的瞧着地下的火盆,微微一笑,淡淡道:“我早就不想活了,只是没有死的决心罢了!你那把火倒是成全了我,不过,可惜,终究还是没有死!在这宫里,能活着已是不易了,你也不过是个苦命人,我又何苦拖上你?何况,你还有孩子,说到底,孩子是无辜的,我这一世,已经对不起一个孩子了,我不想再造孽了···”
宁楚格奇道:“对不起一个孩子?”
孟古青回过神来,眼里含了热泪,定定的望着宁楚格,叹道:“是啊!大阿哥牛钮···那个孩子,当初才那么一点点大,那么可爱···”
宁楚格一惊,声音禁不住大了起来,“大阿哥的死真的跟你有关?”
孟古青紧紧的攥住桌角,出神道:“那是顺治八年,我与福临刚刚大婚,巴尔庶妃是一早就伺候福临的,我大婚的时候,她的肚子已经很大了。那个时候的我太过骄傲,我要求福临只能爱我一个人,我讨厌巴尔·伊丹,她居然抢先怀上了福临的孩子,对那时的我而言,无异于奇耻大辱,我容不下她,更容不下她的孩子!可福临似乎很喜欢那个孩子,福临很欣喜,说第一次体会了当阿玛的感觉,还亲自给他起名叫牛钮,还说等牛钮满一周岁,就封巴尔·伊丹为妃!这一切,在我眼里,都是那么的刺眼。那时的我,可是母仪天下的皇后啊,有什么事是我办不到的呢?福临忙于朝政,也很信任我,要我好好照顾牛钮,可我···可我却被那可笑的妒火冲昏了头脑,我吩咐阿哥所的嬷嬷们不许善待牛钮,那个时候也是这样的天气,冷的刺骨,小小的牛钮从一生下来就病体孱弱,又不曾得到善待,很快便感染了风寒。福临急的把太医院所有的太医都叫去会诊,可即便如此,还是没能挽救牛钮的性命。那个可怜的孩子,终于在出生后三个月夭折了···”
宁楚格惊的说不出话来,怔怔的望着她。
孟古青续道:“那个时候,巴尔·伊丹很痛苦,整日整夜的哭,福临也很伤心,躲在养心殿里不肯出来,整整半个月都没来过后宫。我知道,巴尔·伊丹一直疑心是我害了牛钮,可是那时的我如日中天,她又没有证据,即便有证据,也不能拿我如何,她只得忍气吞声!”
宁楚格皱眉道:“那时候,我应当已经在你宫里伺候了,可我为何一点儿也不知这件事?”
孟古青淡淡道:“你刚来我宫里,我虽很喜欢你,但与你相识毕竟才不过三个月,这样的事儿,我又如何能信得过你?除了我自己以为,也只有彩蝶知道罢了!”
宁楚格有些失落的点点头,“可牛钮,终归只是个孩子,你如何能下的了手?”
孟古青流下泪来,叹道:“当初的我,是那么的愚蠢,原本,我只是气巴尔·伊丹怀了孩子,想折磨折磨她的孩子,只是不想让那个孩子舒坦的过日子,并不想害死他!可他,终究是因为我而死的!我承认,我骄傲,我自负,我脾气暴躁,我对下人也并不好。可无论如何,我从未有害人之心,除了对牛钮···所以,我这一生,最最对不住的便是牛钮,他是唯一一个,我起过歹心害过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