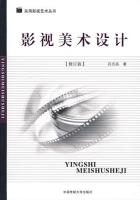把乡愁框得更紧
小时候,我们看到照相机的机会不多,只有在大年初一拍团圆照时,才会看到照相馆师傅和助手扛着大大的木头相机和三脚架,来到镇上一个斋堂前的广场集合。那里比较清静,而且地方够大,装得下我们阮家几十口人。
穿着新衣的小孩兴奋地四处狂奔,被大人抓回来后,动也不能动,一站老半天。师傅用一块大黑布把头蒙住,凑在木箱后调调弄弄,又把头伸出来叮咛我们不能转头、不能闭眼;同样的程序重复好几遍,才会郑重其事地按下快门,以免浪费昂贵的底片。总之,拍照在童年印象中是磨人的苦差事,可也隐隐约约地明白,那是一种神秘的仪式。
那时最轻便的相机就属120片幅,拍出来的照片是6cm×6cm的,四四方方,大小跟小孩玩的纸牌差不多,不用放大,光是印样就可看得清楚。风流倜傥、受过日本教育、在镇公所当民政课长的四叔就有这么一台奢侈品。虽然他只拍自己的小孩,很少将镜头转向我们,可我最喜欢盯着他摆弄机器,觉得真是神奇啊!把他最爱的人、最在意的东西摄入那神奇的盒子里,就能变成一张张永远都在的影像。
他像拼图那样,把所有照片贴在一个很大很大的相框里,挂在最醒目的地方。那个大相框让人百看不厌,每次到他家,我都会再瞧瞧年轻时的四叔、四婶,看看含着奶嘴在地上爬的堂兄、堂弟,感叹长大后的他们真是讨人厌多了!摄影把时间停格的魔力,我还真是从四叔那里最早感受到的。
直到现在,我都记得四叔的那部相机是日本出产的YashicaD。离开家乡多年后,我成了职业摄影人,有天在台北一家二手店看到一部同款的老相机,立刻凑钱买了下来,真希望它就是四叔的那一部,被老人家淘汰换新后,辗转流到了我的手里。可惜,用过才知道,那部相机在光线充足时还不错,拍较暗的景物,解像力就差了。
常用35mm相机捕捉画面的我,每隔一阵子就喜欢用120相机来调剂一下。将双眼镜头的相机捧在胸前,垂头望着毛玻璃取景,整个人自然而然就会谦逊起来,静心享受等待的滋味。使用这种相机,好像跟童年、故乡有了联系。
《正方形乡愁》出版在即,前一阵子我刚好为了下一个展览在暗房里放了好几天照片。看着一张张影像逐渐浮出,感触极深。相较于长方形的外放,这些四四方方的构图显得格外内敛,仿佛将乡愁框得更紧了。